
【学术档案】蒋学模(1918.3—2008.7)浙江慈溪人,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经济学会原名誉会长。2004年获上海市第一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在近70年的学术生涯中,共出版学术专著30余部,主编政治经济学教材和著作10余部、文学和经济学译著10余部。其中包括连续再版13次、印刷达2000万册高等学校通用教材《政治经济学教材》。他还是《基度山伯爵》中文版初译者。
回顾自己的人生,蒋学模是心满意足的。他曾经说:“人的一生能经历如此波澜壮阔的历史巨变,是难能可贵的,特别是,当历史演变的脚步同个人追求的价值目标相一致的时候,其欣慰与满足,更是不能用言语来表达的了。”作为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之一,出生于1918年的蒋学模目睹了旧中国的满目疮痍,等来了新中国的成立,见证着中国如何一步步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而他也把自己的学术生命,全部融解于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波澜壮阔的时代变革中,“为这理想的大厦添上了一砖一瓦”。
与老一辈的经济学家一样,蒋学模最初也是出于“朴素的无产阶级热情”,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能守旧,不怕守旧。”正如他的座右铭,从传统中走来,他终生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并不拘泥于传统,而是根据中国的实践经验不断创新,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时代养料——首版于1980年,面世以来不断修正,再版13次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便是最好的例证。这本教材累计发行达2000万册,创造了社会科学教育普及成果之最,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数代大学生必读的教科书,直到今天仍在使用。
为“人人都有工做,人人都有饭吃”而走向政治经济学
蒋学模曾说:“走上以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作为毕生的选择,不是偶然的,这同我所处的时代条件有关。”
1918年,蒋学模出生于浙江慈溪。6岁时,随父来到上海。他的父亲是一个普通的银行职员。这份工作固然让他家不愁温饱,但成长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积弱积贫的现实让年幼的他感到异常苦闷,期盼着“中国这头睡狮早早醒来,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
同时,他还有另一个烦恼,那就是害怕家人失业。一次,他的父亲算错了一笔账,虽然只是几分钱的事,但还是受到了银行的警告处分。这也引发了家人的恐慌,因为万一父亲因此失了业,他们兄弟姊妹3人都得失学。虽然最后是虚惊一场,但家里还常常有失业的亲戚和同乡来访,请求为他们介绍工作。身边亲人们的际遇,也让他期望着能有那么一天,“中国人人都不愁失业,人人都有工做,人人都有饭吃”。
儿时的两个苦恼和愿望,最终演变成了四个问题:中国往何处去?中国的出路在哪儿?个人往何处去?个人的出路在哪儿?为蒋学模答疑解惑的途径,是读书。首先引起他兴趣的是孙本文的《社会学ABC》,让当时只是中学生的他惊奇地发现,“原来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是有人专门把它当作一门学科的对象来研究。”后来,一本波格丹诺夫关于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的书,更让他豁然开朗:“原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现在世界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都是要发展到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而在未来社会里,将不再有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
从此,他更是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但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能找到的只有河上肇的《〈资本论〉入门》和里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等寥寥几本书。后来在四川大学经济学系,老师在课堂上讲资产阶级经济学,他自己却私下硬啃1938年在重庆出版的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第1卷。
1941年,大学毕业后的蒋学模先是在香港的《财政评论》社当编译,但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他几经流离颠沛,回到重庆进入财政部的财政研究委员会当编译。但国民党政府的研究机构官僚气息浓重,每天上班就是喝茶、抽烟、看报纸、聊天,初出校门不久的他,“在那样的气氛中,简直感到要窒息了。”
所幸不久后,复旦大学的《文摘》社递来“橄榄枝”,蒋学模毫不犹豫地辞去财政部的工作,成为该社的编辑。从1945年进入《文摘》社到1949年《文摘》社解散,除了每月承担两期《文摘》约10万字的翻译任务外,他还翻译了多部文学古典名著、长篇小说、人物传记和历史著作,完成的译作总计9部约230万字,平均每年46万字。其中,使他一举成名的《基度山恩仇记》的翻译工作,便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上世纪80年代,该书改名为《基度山伯爵》重新出版时,一时间洛阳纸贵。今天,市场关注度最高的仍是他的译本。
在儿子蒋维新看来,回过头来看父亲早年的这段经历,从事翻译工作可以说是当初动荡时局下的谋生之举,尽管父亲表现出了惊人的天赋,他简明轻快的文笔成就了《基度山恩仇记》,也让29岁的他因此“一炮而红”,但这只是他璀璨人生的一面——大学毕业后谋生的不易、抗战时期的颠沛流离、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动荡,都让他深深感到,儿时的愿望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愈发严峻迫切,这也使得他并没有继续走上翻译家的道路,而是选择了政治经济学作为他的终身事业。
正如《基度山恩仇记》的结尾写道:“人类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这四个字里面的:‘等待’和‘希望’。”终于,蒋学模等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他毫不犹豫地投身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为之奋斗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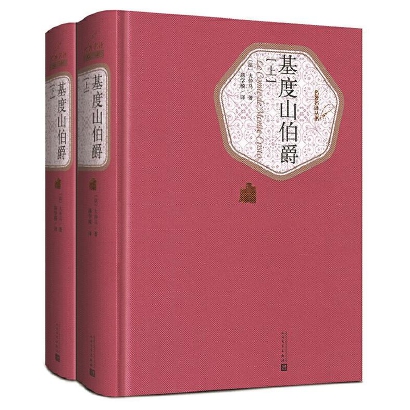
◆《基度山伯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
“他很早就红极一时、名声远播”
上海解放后,蒋学模进入复旦大学经济学系任教。他先是开了两门新课“苏联经济建设”和“东南欧经济”,不久便转而教授政治经济学。解放初期,我国的政治经济学几乎是亦步亦趋地学习苏联。1950年,党中央建立中国人民大学,邀请苏联专家来讲课,并要求全国各地的高教局选派高校青年教师来学习,蒋学模便是其中之一。
在人大的两年,蒋学模认为最大的收获就是“有整整两年的时间来读原著”——尽管在解放前,他已经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产生极大兴趣,但完全是出于“零敲碎打”的自学,也从未接触过马、恩、列、斯的原著。这期间,通过阅读原著,尤其是仔细研读《资本论》,使他“初步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奠定了学术的根基。
学习的同时,蒋学模也笔耕不辍。两年光阴的另一项收获,是1952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讲话》。回到复旦后,他还与同事们一起编写了供大学本科使用的《政治经济学讲义》。由于这两本书是国内第一次撰写包括有社会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读物,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1955年,蒋学模更是因此受邀进京和王惠德、陈道一起编写了《政治经济学常识》,以配合当时全国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热潮,该书一年之内印行了280万册。只是这段时间,苏联教科书的观点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中还是处于支配地位。
但“分歧”很快开始出现——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不同、中国工业化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途径与苏联的不同,以及苏联教科书中关于变革生产关系时只讲物质前提不讲上层建筑的问题……这些都使得无法将苏联的理论“生搬硬套”到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去。基于这样的矛盾,编写一部“国产”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成为当时学者的努力方向。
于是,这一时期全国各地掀起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的高潮。编写教材期间,“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记录”成为各地编书组的理论指导,也让时为上海编书组成员的蒋学模“如获珍宝”。在晚年的回忆中,他写道:“我当时觉得,毛泽东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注入了辩证法,注入了革命精神,注入了主观能动性。”
当时,13个省市编写了14个版本的教科书,1960年到中央党校讨论,会后有两本教材公开出版,蒋学模与姚耐、雍文远等主编的上海版教材是其中之一。后来华东局组织的教材评比会中,这一版教材被推选为范本。有学者曾评价,“这本教材的出版是当年政治经济学建设中的一件大事,是解放以来我国自创全新系统以崭新面貌正式出版的第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至此才打破了苏联教科书一统天下的沉闷局面。”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突出成就,让蒋学模两次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958年毛主席在上海接见教育、卫生、艺术界人士,谈家桢、蒋学模、孙怀仁、章靳以等六位教授受到接见。蒋学模当时40岁,时为副教授,与谈家桢等资深教授一起与毛主席面对面进行了交谈。1964年7月17日,毛主席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接见高、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代表,蒋学模位列首排。可以说,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政治经济学大师,他“很早就红极一时、名声远播”(周秉腾语)。
但很快,“文革”开始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热潮和体系构建工作基本被打断。蒋学模的学术之路,也因此耽搁了10年。
“他一直站在他们那一代人的前面”
改革开放后,包括蒋学模在内的老一辈经济学家们面前,一段崭新的历史徐徐揭开序幕。尽管“改革”已成为社会共识,但很长的时间里,怎么改?改到什么样子?这场没有脚本的改革里,他和当时其他人一样,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1979年,我们党拨乱反正,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政治经济学新教材的编写工作被提上日程。蒋学模再次被委以重任。这年夏天,接到了高教部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的编书任务后,他立即组织复旦的政治经济学教师编写教材。
当时,身为主编的蒋学模已经62岁。为了完成《教材》的统稿任务,开不动“夜车”的他一改年轻时的工作规律,开起了早车。每天凌晨4点左右起床工作,泡一杯茶,书桌上放一些干点心,这样一直工作到中午12点。经过一个月左右紧张的统稿工作,1980年7月,第1版《政治经济学教材》终于横空出世。此后,为了及时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新观点、新经验,教材每两年就要作一次较大的修订,从1980年到2005年,一共出了13版。
思想大解放的氛围中,蒋学模把过去长期郁结在心头的问题大胆提了出来,对以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看似“真理”性质的判断提出了质疑。1978年,他发表了两篇颇具争议性的文章,引发学界广泛讨论:其一是关于“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他指出苏联教科书将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作为一个经济规律来表述,是不符合实际的;其二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发生经济危机”,对长期在社会主义各国流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无危机不断增长”的传统观点发起了挑战。
对此,有学者批评他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念歪了,自由化了”,甚至将他的思想歪解为“资本主义无贫困,社会主义有危机”。蒋学模却不以为然,并且提出,“在理论研究工作中应该提倡实事求是的好学风,避免对社会主义‘肯定一切’和对资本主义‘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
类似的这种对政治经济学传统观念的“拨乱反正”,在蒋学模那里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在他看来,“不破不立”,“对‘左’的指导思想下形成的传统观点不破除,就不能接受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的邓小平理论和党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或许,正是这种与时俱进的开放心态,让他得以“站在他们那一代人的前面”,很快跟上了日新月异的新形势——
早在1978年,蒋学模就接受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观点。1992年,在党的十四大和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发表后,曾经把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特征奉为真理的他,在看到私有制经济在增加就业、社会产品供应、国家税收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后,也逐渐想通并接受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断。随后不久,他还进一步撰文探讨了我国的国有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如何与市场经济相容,回应实践提出的新问题。
提出“市场经济”后,“劳动力是否是商品”一度成为当时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蒋学模撰文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应该承认劳动力的商品性。当时,同为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的一位关系非常要好的同学看到后,立刻回信“质问”:“你今天说我们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也是商品,我们社会是什么性质?”甚至还开玩笑地说,“如果你坚持这个观点,朋友情谊也要‘一刀两断’。”
回溯这段历史,思想解放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也恰恰印证了那句话,“改革没有完成时,改革只有进行时”。正如蒋学模所说,“改革实践不断向传统的理论观点提出挑战,要求经济理论界根据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提出新的理论观点以适用和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
多年来,这些思想修正和理论创新全部反映在了《政治经济学教材》的一次次修订中,每一版的改动都吸收了最前沿的学术动态和理论共识。复旦大学资深教授伍伯麟就认为,“蒋先生的教材修改,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进程,及时地将实践证明是科学正确的经验转换为教材建设的鲜活素材”。这部教材的编写工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演进的一个缩影。

◆《政治经济学教材(第13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深入浅出”本身就是重要的治学过程
蒋学模曾经说,有两本书代表了他的一生,那便是《基度山伯爵》与《政治经济学教材》,这两本广为流传的著作,也是数代人的共同记忆。无论是《基度山伯爵》还是《政治经济学教材》,为什么“蒋学模版”总能从诸多版本中脱颖而出,被首推为经典并广泛普及?
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的威力就在于能够武装大众”,蒋学模正是把握了经济学理论研究使命的精髓,其明快流畅的文笔和严密的逻辑结构,总是能把深奥的经济理论讲得浅显易懂、引人入胜。他经常告诫学生,做学问不能“深入深出”、“浅入深出”,那是自我清高和卖弄风骚;而是要“深入浅出”,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治学过程。在对所研究问题有深刻认识的基础上,还必须做到“浅出”,以明白易懂的方式传播给大众。能否“浅出”,实际上是对学者所研究问题有否真正掌握的检验。
这种“深入浅出”的治学智慧不仅落于笔尖,也反映在他的教学风格上。“蒋先生讲课条理清晰,口才非常好,也很幽默。”许多学生的回忆里,他的课总是座无虚席,外系的学生也来旁听,迟来的学生只能站在后面过道上;当年他开一次讲座,蜂拥而至的人群像现在的明星开演唱会。有学生至今对他的一场讲座记忆犹新,讲座的内容是关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商品经济,蒋学模在开头提到了当时被列为“禁曲”的《乡恋》。“老师的思想很开放,李谷一的这首歌因缠绵悱恻被批判为‘靡靡之音’,他却觉得没什么问题。”
“开放”,这也是学生们提及最多的老师身上的特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晖明谈到,1977年到1978年,上海几家大型图书馆的经济学科领域藏书都少得可怜,外文图书更是非常少,蒋学模就组织青年教师去北京图书馆查阅,并安排相关的资金复印材料。上世纪80年代初,蒋学模是当时少数代表中国经济学家参加国际会议的学者,一回校就组织向全系师生作考察报告,将所见所闻分享给大家。“老师很喜欢与年轻人对话交流,也很善于接受新的学术成果。在教材的修订过程中,也充分尊重和听取年轻人的意见,宽容地吸纳了西方经济学的一些范式和内容。”张晖明这样说。
晚年的自传中,蒋学模将自己的治学之道总结为“不能守旧、不怕守旧”。对于自己的理论研究工作,他也曾这样自我剖析道:“像我这样年龄的理论工作者,受高度集权模式的影响较大,一般把我归为‘保守派’之列,但我自信还不是顽固派。不是先知先觉,但还不是死硬派,是随着时代脉搏前进的人。”他还说,“但我又绝非‘风’派,我讲课或写文章中的观点,总要自己想通了才写,自己没有想通,人云亦云,这样的文风是没有的。”
这不免令人回忆起上世纪8 0年代,两位经济学家蒋学模和于光远之间的一段著名对话: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于光远戏称自己是“死不悔改”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蒋学模随后回应,宁愿把自己称作“是一个不断改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
“用今天比较时兴的表达语言就是‘与时俱进’。”张晖明这样理解老师的“不断改悔”,“以问题为导向,思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时期如何保持活力,能够联系中国改革的实践,做到不断丰富发展,这是他一直在做的事情。”

作者:本报记者 陈瑜
编辑:陈瑜
责任编辑:杨逸淇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