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我到哥伦比亚大学读学位,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我从国内的一个大学讲师一夜间变成了学生,开启了人生的一个新历程。我这里要说的是赴美时随身带的一样物品和与此物品有关的一个人的故事。
这件物品其实就是一本英文原著,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Otto Jespersen)所著的《语法哲学》。我随身只带了这本英文原著是因为我跟此书有特别的情缘。一是因为叶斯柏森是我非常敬仰的一位语言学家,二是因为我是《语法哲学》中文版的译者之一。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感觉,对英语真正有研究的人往往不是英美人,而是英美国家之外的学者。因为外国语言学家往往有对比的视野,对另一门语言有更深的理解和更敏锐的洞察力。
叶氏是位多产作家,一生写过近500部著述,涉及普通语言学、语法学、语音学、语言史、符号系统、语言哲学、外语教学和世界语。他编写的7卷本《现代英语语法》是他最宏大的一部著作,其规模和深度都超过我喜欢的另一部由四位英国学者Randolph Quirk, Sidney Greenbaum, Geoffrey Leech和Jan Svartvik写的《英语综合语法》(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由于他对英语语法学所做的杰出贡献,他被语言学界公认为英语语法的最高权威,同时也享有“语言学之父”的美誉。此外他还独创过一门世界语,先是叫“依德语”(Ido),后是叫“诺维亚语”(Novial)。《语法哲学》是叶氏的另一部代表作。我成为此书中译本译者之一的故事是这样的。

1970年代末正是改革开放、百废待兴的年代。中国的学术界也异常活跃,开始与西方学术界全方位接触。我本人在一年内先后两次去南京大学参加教育部主办的全国高校英语师资培训班,接受来自“英国文委”(British Council)的语言学家们的培训。当时中国的语言学界一方面在引进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的最新学说,一方面在介绍西方语言学史上各经典流派,同时大量引进西方学术界的著作。当时我在徐州师院(现叫江苏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我们学校中文系有位国内知名的语言学家廖序东先生。廖先生上世纪30年代问学于黎锦熙、许寿裳、罗根泽等多位大师,1941年7月从北师大毕业后即投身教育界,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汉语教学生涯。他与黄伯荣先生于1979年共同主编的《现代汉语》一书至今仍被国内许多高校的中文专业用作指定教材。他时任中文系主任,后来又担任了学校的副校长。廖先生对汲取西方语言学理论的精髓以资研究中国语言方面十分重视,经常组织他的研究生与我们外文系的青年教师进行交流和探讨,我们也从廖先生渊博的学问中获益甚多。
廖先生在和我的交谈中多次提到近百年来一直被看作是语言学史上经典文献的叶氏著《语法哲学》一书,他对此书的喜爱溢于言表。叶斯柏森是西方语言学史上介于传统和现代描写派之间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在《语法哲学》中运用新的方法分析探讨语言学、语法学上的重大问题,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语言理论。叶氏指出,语言理论应是概括语言事实的工具,而不是让语言事实去迁就语法的教条。这对一般语法理论的探索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呼出了现代描写语法的先声。《语法哲学》对上世纪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和吕叔湘等人都影响甚大。廖先生认为《语法哲学》是叶氏论述其语法理论和语法体系的代表作,是一部有划时代意义的语法著作,对汉语语法的研究和发展有深刻的影响。
当时我对叶氏其实也很熟悉。我特别尊崇他1922年写的《语言的本质、发展和起源》(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一书。此书也被学界认为是他学术成就最高的一本著作。他领先于时代,在此书中率先讨论了六七十年代成为热门话题的诸多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问题,如女性语言的问题和语言物质特性的理据问题。
源于我们对叶氏的共同兴趣,廖先生问我是否愿意协助他组织一个翻译班子,将《语法哲学》译成中文,让更多中国语言工作者从中获益。我欣然接受了廖先生的邀请。
随后我请了南京师范学院(后改为南京师范大学)的夏宁生老师和本系的司辉老师参加翻译、韩有毅老师担任校订,廖先生又请到他在苏州的好友张兆星老师和徐州师院中文系的王惟甦老师分别参加翻译和校订,于是一场翻译大战便揭开了序幕。我们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并不是专业方面的问题,而是叶氏对众多语言里的例子的旁征博引。他在书里并没有提供这些例句的英译,但是我们必须把这些例句都翻译成中文。1980年初国内的外国人还是不太多,特别是我们在徐州那样的城市很少有机会接触到说英文以外语言的外国人。我们当时想到的一个办法就是给相关语言所在国的驻华大使馆写信求助。有时也给国外高校的学者发函询问。
经过近两年的齐心合力,并在廖先生的指导和主持下,我们终于完成了翻译。译本先由徐州师院印刷,分寄给国内各高校的中文系,作为交流资料。多年后国内还有不少同行与我说起,他们曾看过我们的那个本子,有的还保存着那本书。
徐州师院的自印本印出后,廖先生随即与语文出版社联系正式出版此书,未几语文出版社便接受了。《语法哲学》于1988年正式出版,给我们多年的辛勤努力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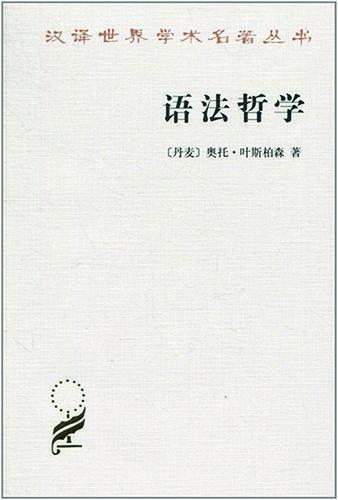
就在语文出版社将《语法哲学》付梓的前夕,我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前去攻读人类语言学专业。我来美国时由于行李箱的空间有限,不能带很多书,但是在我随身携带的书籍中就有中英文版各一本《语法哲学》。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语言学导师哈维·皮得金(Harvey Pitkin)教授对叶斯柏森也很推崇。他听说我参与了此书中文版的翻译很高兴。虽然他不懂中文,还是跟我索要了一本译本,但这足见叶氏在语言学界的地位。
我到了美国后,一直与廖先生保持联系。廖先生也告诉我《语法哲学》的译本出版后不久就已告罄。译作出版后,廖先生寄赠两册给中国语言学界的泰斗吕叔湘先生。吕先生1990年2月7日回信说:
收到您的信和两本《语法哲学》,谢谢。此书在五十年代曾由语言所请人翻译,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完稿,现在终于有了中文译本,实为好事。最近商务印书馆正在筹划续编《世界名著汉译丛书》100种,我间接托人表示此书可以入选,不知商务意思如何。
斗转星移,在吕先生写了上面那封信的16年后的2006夏天,我回徐州拜访廖先生的时候,廖先生说他已同商务印书馆联系,商务已同意再版此书。廖先生嘱我回美国后也同商务印书馆联系,再次确定。我回来后便同商务取得了联系,终于在2008年的7月得到确定,此书将由商务年内再版。我得到这个消息时正带一团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在南京大学培训中文,不禁欣喜若狂,准备在月内去徐州时告诉廖先生这个好消息,可是我到徐州后才得知,廖先生已于2006年的12月仙逝。我虽知廖先生年事已高,但听到他去世的消息仍是觉得突兀。我在再版后记里写道:“万分遗憾廖先生未能看到《语法哲学》的再版。廖先生为叶氏一书的翻译、审订、再版呕心沥血,倾注了近三十年的心血,是《语法哲学》中文版的第一功臣。在此书再版之际,我觉得我们纪念廖先生的最好办法就是把这一译本献给他老人家。”
叶斯柏森在《语法哲学》的序言中一开头就说此书基于他1910年至1911年在哥大的一个题为“英语语法导论”的系列讲座,我在翻译此书时对此并没有在意,译作完稿后一年我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读博,不禁对《语法哲学》产生了更多的亲切感,也觉得离叶斯柏森更近了一步。到了哥大后我便开始搜寻叶氏的足迹,近些时候又几经周折通过纽约大学的馆际借书服务处借到叶斯柏森的自传。叶斯柏森的自传是用丹麦语写的,1995年才被翻译成英语。有英文版的图书馆很少,所以我要通过任教的纽约大学去其他图书馆调这本书。
叶斯柏森生前来过美国两次。他的两次美国之行都给美国学术界带来很大的影响。他第一次来美国是1904年8月应邀参加在圣路易斯举行的世博会美国文理大会(Congress of Arts and Sciences)版块,并做演讲。当时叶斯柏森是哥本哈根大学的教授。此次会议邀请了100位欧洲和100位美国的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参会。每门学科安排两场讲座,一场谈本学科的话题,一场谈本学科和其他学科交叉关系的话题。我觉得100多年前的这种研讨形式非常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跨界交流了。英文学科的两个话题落在哈佛大学基特里奇(Kittredge)教授和叶斯柏森身上。基特里奇教授谈英文本题的问题,叶斯柏森谈英文学科和其他学科的关系。大会主席在致辞时还专门提到叶斯柏森。他说:“欧洲有个不起眼的半岛,可是那儿的知识水平可是了得,我们这次从那儿请来一位人士讲我们自己的语言。”世博会结束后,叶斯柏森跟其他参会嘉宾前往华盛顿,受到美国总统(老)罗斯福的接见。华盛顿之行结束后,各位嘉宾又去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参加活动。完后欧洲的嘉宾都返回自己的国家,只有叶斯柏森留下几个星期,因为他很想体验一下美国大学的日常生活。此时哈佛大学有不少知名的语言学家。叶斯柏森找到知音,很快就跟他们结为好友。在哈佛待了几个星期后,叶斯柏森又应耶鲁大学两位语言学家之邀访问耶鲁,随后他又去纽约待了一个星期。在纽约的日程和起居都是哥大修辞学教授乔治 ·卡彭特(George Carpenter)安排的。通过卡彭特教授,叶斯柏森又结识了多位哥大的教授。纽约之行为他第二次访美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908年,也就是叶斯柏森首次访美的四年后,哥大校长尼古拉斯·莫里·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来访叶斯柏森任职的哥本哈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有一座巴特勒图书馆,是哥大标志性建筑。这座图书馆就是以尼古拉斯·莫里·巴特勒命名的。巴特勒校长在哥本哈根大学做了三场关于美国文化生活的讲座。在讲学期间他问哥本哈根大学的校长有无可能派一名教授去哥大讲学一个学期。当时美国跟欧洲各国的这种学术交流刚刚成为时尚。哥本哈根大学的校长很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学校的校务委员会一致通过派叶斯柏森于1909年的9月到1910年的1月去哥大讲学一个学期。叶氏在做行程计划时又收到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校长本杰明·惠勒(Benjamin Wheeler)的一封信。信上说他听说叶斯柏森秋季要去哥大讲学,问他有无可能夏天先来柏克莱讲学6个星期。因时间紧急,惠勒校长请他接信后电报作复。经和太太商量后,叶氏次日就发一个一字电报回复:Yes。他如此爽快地接受邀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惠勒校长本人也是同行,是著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在任校长前曾在哈佛大学和康内尔大学任语言学教授。叶氏也想跟他建立私人之交,以便日后的学术交流。6月3日他和太太还有11岁的儿子就“扬帆起航”,登上了远洋油船,开启第二次赴美的行程。叶教授到柏克莱后开了一门语音学课程并以世界语为题做了一系列的讲座。叶氏在回忆录里说他在柏克莱度过了即愉快又有学术收获的6个星期。
1909年的9月20日叶斯柏森在哥大走马上任到英语系任职。在随后的5个月里哥大完全把他看作是自己的教授,享受哥大教授所有的权利和福利,学生也不知道他是访问学者。他在哥大教的是博士生, 开的课程是“普通语音学”、“英语语法原则”、“历史英语句法研讨课”。我在看叶斯柏森的自传时,看到他说他的《语法哲学》一书就是他在哥大上的“英语语法原则”一课的基础上扩展开的时候,感到我自己跟叶教授的关系又亲近了许多。
哥大人类学系的佛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教授听说叶斯柏森在英语系开语言学的课程,就让他所有的学生都去注册。博厄斯是举世闻名的人类学家,在学界被称做“美国人类学之父”。博厄斯在做人类学田野调查时研究过很多美国印第安部落的土著语言,并在很多论著里谈到语言问题。我在出国前就看过他1940年写的《种族、语言与文化》(Race, Language, and Culture)一书,当时还以为他只是语言学家呢。说到博厄斯就不能不提一下我在哥大时的导师Myron Cohen,他的中文名字是孔迈隆。孔教授也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是我在哥大的导师之一。当时他是系里唯一研究中国的教授,所以我跟他的关系很近,也协助他做一些关于中国的研究。孔教授后来还担任过哥大人类学系的主任和哥大东亚研究所所长。我之所以在谈博厄斯教授的时候提到孔教授是因为孔教授用的办公室就是当年博厄斯的办公室。所以我每次去孔教授的办公室都有一种进入学术圣堂的敬畏感觉。
叶斯柏森在哥大教语言学课程时有个发现,77年后我来哥大也有同一发现,这就是哥大语言学专业的研究生大多不是美国人。学生大多是外国人也有好处,因为叶教授上课时经常援各种语言的例子。每到这时他就会让说这些语言的学生朗读这些例子。他们是本族人,发音当然是标准的。不过这些外国学生也有他们的短处。叶教授发现他们的语言水平普遍不如丹麦学生的语言水平。他上课时引法语或德语的例子时,学生大多不懂,得让他翻译。但学生们都很勤奋,从不缺席一堂课,给叶教授留下深刻的印象。
叶斯柏森所在的英语系在哥大的哲学楼。楼里当然就有哲学系。哥大哲学系当时最著名的一位教授就是杜威。杜威是大哲学家,常被称为“美国进步教育之父”、“改变美国教育和中国教育的人”。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正值杜威教授访华100周年,诞辰160周年。叶斯柏森在哥大的时候,杜威也在同一楼里。我尚未找到这两位学者交往的资料。不过我想这两位在各自领域里的领军人物没有交往是不大可能的,尤其是语言和哲学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叶氏的代表作不就叫做《语法哲学》吗?说到杜威,我跟他还有一个缘分呢。我当年在哥大的博士论文答辩就是在杜威原先的办公室进行的。我毕业后不久就去杜威和胡适、郭秉文、孟禄(Paul Monroe)等哥大学人于1926年在纽约创立的华美协进社工作了。
叶斯柏森在哥大讲学期间还应周边一些高校之邀,利用周末的时间去做语言学讲座。他去过哈佛讲语言中的逻辑,去过卫斯理学院(Wellesley College)给学生讲语音和句法。卫斯理学院是所女子文理学院,讲座那天来了300听众,令叶教授很是惊讶。
叶斯柏森在结束讲学之际,哥大为表彰他的功绩,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仪式是在校长办公室进行的,这是莫大的荣誉。叶教授在回忆录里谈到他在哥大5个月的生活时用了两个词,跟他形容在柏克莱的6周生活的两词一样:instructive (获益匪浅)和 enjoyable(欢乐愉快)。叶斯柏森回国后便再没来过美国。他于1920年60岁的时候出任哥本哈根大学的校长,达到他事业的巅峰。叶氏70岁生日时,美国语言学家、人类学家萨丕尔在丹麦著名报纸《明智人》上撰文祝寿,并对其成就及人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作者:何勇(联合国赴华项目负责人)
编辑:于颖
责任编辑:陈韶旭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