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的西方法学界,哈特与德沃金无疑是两位声誉卓著的大师。前者是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奠基人,后者是新自然法学的领军人。德沃金对哈特理论的批判所引发的论辩被公认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法哲学论战之一。一般认为,在论战中,德沃金的对手主要是哈特的拥护者们。哈特本人在有生之年几乎未曾亲自参与论辩,只是在其逝世后再版著作的“后记”中对德沃金的观点做出长篇回应。但事实上,哈特在晚年一直致力于对德沃金的理论进行回应和批判,只是德沃金对此几乎毫不知情。究竟为何会出现这样奇怪的情形?要回答这一问题,则不得不谈到两位顶尖法学家之间颇为令人唏嘘的交往,以及二人惺惺相惜却又带有某种瑜亮情结的隐秘纠葛。

赫伯特哈特 罗尼德沃金
一
早在1955年,哈特与德沃金便已存在联系。那时,哈特是牛津大学的法理学教授,正处于职业生涯中的“黄金岁月”。他致力于实现哲学与法律的对话,且其一生中最为著名的代表作《法律的概念》雏形也在此期间逐渐形成。德沃金则是哈佛大学的一名普通学生,正在牛津大学交换学习。哈特极为偶然地对这名来自美国的本科生产生了深刻印象。当时,哈特一边无聊地批改结业试卷,一边向身旁的助手抱怨阅卷令他虚度光阴。突然间,一个名叫“德沃金”的考生所提交的答卷令哈特眼前一亮。其精妙的回答,让他不得不给出极高的分数。然而,哈特心中也暗暗生出一丝焦虑。他从德沃金的答卷中,感受到这个学生很可能会对自己即将出版的《法律的概念》一书做出激烈批判。很多年后,哈特在一次学术演说中,公开坦承他当年看到德沃金答卷时的焦虑,并认为这种焦虑曾给自己造成了“智识与个人情感上的巨大困惑”。
1956年9月,哈特赴哈佛大学访学。其间,他特意找到德沃金,邀请他共进晚餐。用餐时,正处于求职迷茫期的德沃金向哈特咨询,自己应当从事学术研究还是实务工作。哈特却令人意外地提出他应当选择后者。提出这种建议的具体理由以及哈特当时的真实心态已无从考证。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德沃金听从了哈特的建议,先去美国最高法院担任法官助理,然后在纽约市一家大型律所担任律师。不过,德沃金始终无法在实务工作中获得成就感。几年后,他放弃了律所的高薪职位,决定重新“思考、争辩那些艰难的、重要的和值得的事情”。1962年,德沃金获得了生平第一份教职:耶鲁法学院副教授。
二
1968年,哈特即将退休。他认为应当亲自挑选教席的继任者。事实上,这一做法与牛津大学法学院的规定相悖。根据学院规定,任何教授不能够介入自身教席继任者的选任工作。而且,当时已经存在一位被法学院普遍看好的候选人,他就是哈特的好朋友与合作者托尼·奥诺里。也许是认为奥诺里过于广泛的兴趣会影响他对学术研究的专注度,哈特并没有将他视为合适的继任者。哈特对选任工作的不断干预,不仅令他与奥诺里的关系出现嫌隙,还使得法学院其他教授极为不满。
然而,哈特毫不顾忌他人的看法。他直接给正在耶鲁法学院工作的德沃金写信,问他有无兴趣接任自己的教席。接到哈特的来信,德沃金非常吃惊。因为此时的德沃金尚未发表太多作品,在学术圈几乎默默无闻。更令德沃金讶异的是,这么多年来,哈特竟然一直在关注他的研究。其中,德沃金一篇题为《法律是一种规则体系吗》的论文更是曾被哈特反复阅读与思考。
仅仅写信还不够,在不久之后赴纽约的公务出差中,哈特专门宴请德沃金。在会面前,哈特甚至感到紧张。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烦躁不安,例如,昨天晚上在牛津的火车上阅读德沃金评论我的规则模式的文章。我读得很晚,并为他观点而焦虑:我开始感到某种智识上的恐慌。”抵达纽约后,他仍然不断阅读德沃金的文章。他写道:“在形成那个想法之前我必须再读一遍德沃金论规则的论文……在1点钟与德沃金会面之前,重新思考一下他的论文。”当时哈特已是具有国际声誉的学术权威,而德沃金只是一名普通的青年学者。产生如此紧张的情绪,连哈特自己都无法理解。他暗暗感叹道,“对于一位六十岁高龄,而且在这个职位上已经待了十六年的牛津法理学教授来说,这样做真是有些无事自扰了。”
在与哈特见面后,德沃金决心接受前往牛津任职的邀请。促使德沃金做出这一决定的主要原因是,他希望今后能够跟哈特这位自己心中最为杰出的法哲学家经常进行交流。因为正是基于对哈特理论的批判,他才得以发展与完善自己的学说。哈特对德沃金的选择感到十分高兴。尽管他已认识到,德沃金可能会成为对他理论最有力的批评者,但他仍主动替这位在他看来极具天赋的法学家谋取牛津教职。为了维护牛津法理学首席教授席位的声望,他不惜让自己的学说面临被激烈批判的风险,并不惜将自己置于法学院同事的非议与流言中,毅然选择德沃金作为自己的继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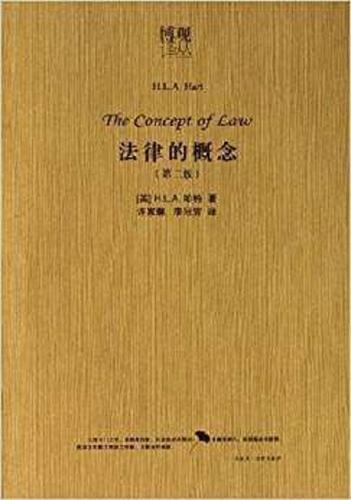
《法律的概念》及其第二版
三
在1968年夏天,哈特曾应德沃金夫妇之邀与他们一起度假。双方的友谊迅速升温。遗憾的是,这一美好的场景未能延续。
担任牛津大学法理学首席教授后,德沃金迅速取得巨大的名望。他的著作《认真对待权利》于1977年一经出版,立刻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与好评。该书对哈特倡导的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攻击,迅速引发双方支持者与反对者的一场大规模论战。哈特之所以被称为新分析实证主义的奠基人,就是因为他在借鉴现代语言哲学的基础上,创造了分析法学流派,并致力于提出一种能够包含所有类型的法律概念。哈特理论起源可归结为一个极为简单的观念,即法律是一个规则体系,它在结构上类似于象棋、足球之类的比赛规则,其中并不包含与道德相关的因素。
德沃金在《认真对待权利》一书中正是集中火力对哈特理论中的“规则模式”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进行批判。他继承了自己在哈佛的老师朗·富勒的自然法学派思想,认为法律需要藉由道德标准予以识别。在此基础上,德沃金指出,法律除了规则,还包括原则,而原则中不可避免地包含道德性因素。哈特的支持者们则批评德沃金眼中的“规则模式”过于主观,并不符合哈特对于法律定义的真正表述。除此之外,包括约瑟夫·拉兹、科尔曼在内的诸多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家,加入了反对德沃金的阵营中,这使得论战的规模与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与如火如荼的论战氛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在牛津大学法学院的德沃金与哈特两人几乎不曾直接交流过相关问题。事实上,此时二人的关系已经十分微妙而别扭。在牛津,德沃金尽管已获得事业上的巨大成功,但他始终感觉到不被接受与承认。旁人喜欢将他与哈特比较,而后者则被牛津大学法学院的众人像英雄一样崇拜。长期在牛津大学法学院工作的门房长甚至很喜欢跟别人讲,哈特才是真正的牛津绅士,德沃金不能与哈特相比较。
与之相对的是,哈特对德沃金的学术批判方式,感到越来越不舒服。他认为德沃金在引用自己观点时不够客观与诚实,某些用语也不够尊重。在哈特看来,对于自己这位推荐者,德沃金并未表现出足够的感激与认可,这使得哈特觉得自己非常不受尊重。但更深层次的心结是,哈特愈发意识到德沃金的批判给自己理论造成了巨大挑战,而自己在回应这种挑战时已经十分艰难与吃力。在这种纠结的心理状态下,他回绝了德沃金邀请他一同开设法理学课程的请求。
在往后的日子里,哈特与德沃金几乎不再碰面。可是,两人又忍不住想要了解对方的观点。于是,哈特的博士生维尔·卢瓦乔便充当起“传话筒”的角色。哈特在阅读完卢瓦乔论文时,通常会说:“我们必须看看德沃金教授对这一切是怎么想得。”而根据卢瓦乔的回忆,他与德沃金讨论论文的情形是这样的:“在我们讨论的过程中,德沃金教授问我:‘哈特教授对这一切是怎么想的?’我回答说:‘他似乎同意论证的思路。’德沃金教授边摇头边嘟哝着一些听不清楚的东西。第二天我收到哈特教授的来信,他想知道‘德沃金教授说了些什么’,我告诉了他,他轻声一笑。”
四
晚年的哈特将大部分精力暗暗用于回应德沃金的批评。当德沃金的经典著作《法律帝国》出版后,疾病缠身的哈特越发感觉到自身的力不从心。他在笔记本上痛苦地写道:“绝望地寻求工作的转机。”哈特曾试图主张他与德沃金的研究具有互补性,彼此无需推翻对方理论。然而德沃金在其著作中却明确表示,自己的理论与哈特的理论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二者不具有任何共容性。事实上,德沃金对哈特的努力与痛苦全然不知晓。直到其他同事告知他哈特一直在致力于反对他的理论时,德沃金才恍然大悟。他找到哈特想与他直接交流,但遭到了哈特冷淡的拒绝。这一反应也伤害到德沃金的自尊,从此他就再也不提这件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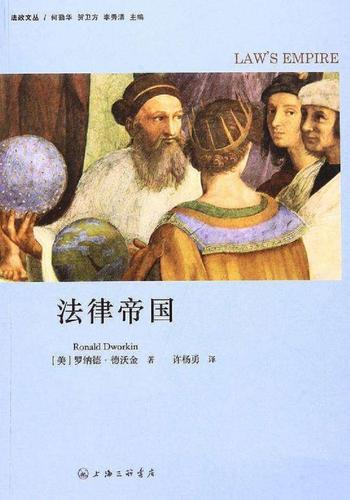
直到去世,哈特对德沃金的回应工作也没有全部完成。在几位崇拜者的努力下,哈特生前围绕德沃金理论所作的笔记被整理出来,并以“后记”形式刊登在哈特逝后出版的《法律的概念》(第二版)中。这一“后记”引发了学界的轩然大波,专门针对它的分析甚至形成了一本厚厚的论文集。德沃金对“后记”中哈特表现出的痛苦与愤怒大为震惊,黯然道:“他在写作这篇回应时,就如同从来没有和我见过面一样。我们本来可以就它进行交流的。”某种程度上,哈特亲手造就了这位使自己抑郁十余年的强劲对手。为回应德沃金的观点,哈特曾在《噩梦与美梦》一文中分别以“噩梦”与“美梦”来比喻自己和德沃金的法学思想。如其所言,对于彼此而言,这两位互相欣赏又互相看不惯,渴望了解又刻意保持冷淡的法学家又何尝不是对方的“噩梦”与“美梦”。
作者:何源(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编辑:于颖
责任编辑:任思蕴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