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第一流的学问”
——浅谈何炳棣先生治史的特点
(之四)
李伯重
《文汇学人》 2017.12.08

“大历史”史观
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说:经济史“只是通史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说明而把它从其余的部分分离出来”。克里吉(Eric Kerridge)则说:“只有整合的历史才能使我们穿越现时,看到那已逝去的我们不熟悉的世界,更重要的是运用这种对那个已逝世界的知识,与当今世界做出对比,从而加深我们对现实的认识,这才是历史学家最伟大、最崇高的目标。”经济史也不例外,“经济史是从通史或总体史中抽取出来的,而农业史、工业史、商业史等又是从经济史中抽取出来的。这种专门化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集中思考总体史的某一具体方面,以揭示整体的发展”。然而现实是,“现在各门专业壁垒高筑,互不理会,经济史也沾上了这种毛病”。这种“各门专业壁垒高筑,互不理会”的状况不止存在于经济史学,而且存在历史学各学科,而各学科之间的壁垒,更是高不可攀,深不可测。
何先生的研究不断转向,从英国史到中国史;在中国史中,从商业史到人口史,然后到社会史、文化史,最后到思想史。虽然从领域来说,每一次转向都是一次剧变,但这些转向背后都有一个逻辑,即把中国史作为一个整体,转向只是从不同的方面来研究这个整体。他研究的重点从经济到社会,从社会到文化,从文化到思想,足以覆盖历史的主要领域,把中国历史的各主要方面都纳入了他的视野。汪荣祖先生评论何先生晚年的研究说:“从黄土的特性发见华夏原始农耕的特性,又从此特性发展出村落定居农业以及家族制度和祖先崇拜,可见自仰韶一直到西周其间‘血缘链环’之形成,以及之后借宗法制度的推广以控制广土众民。秦汉大一统在政治形式上固然变成郡县,但在精神上仍然延续宗法,皇帝实乃超级之宗子。华夏文化中延绵不绝的‘宗法基因’之发现,为作者近年最重要的创获;窃以为以此基因为主旨,足可写一部崭新的中国通史。”
在《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中,诸葛亮有一句很精辟的话:“儒有小人、君子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这段话区分君子之儒和小人之儒的标准是有问题的,但是从治学的理念和胸襟来看,确实有通儒和小儒之分。通儒的代表是司马迁,他在《报任少卿书》中说:他终生追求的理想,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以无比坚毅的意志和伟大史家的才能,做到了这一点,成为中国史学之父。做第一流的学问,就是要成为这样的通儒。“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不论才气如何,向着这个方向努力,是史学家的使命。在这方面,何先生也树立了一个榜样。
* * *
最后,我回到“做第一流的学问”的话题上来。
何炳棣先生的研究多次转向,做出来的成果却都是第一流的。汪荣祖先生说:何炳棣先生“将其研究课题与特定的学术专业接轨,他的美洲作物论文发表在第一流的人类学学报上,他的早稻论文发表在第一流的经济史学报上。……探讨任何起源问题,都是头等的难题,作者自选最困难的题目攻坚,而且还涉及专业以外的许多专业,其艰苦与毅力可以想见,然未能想见的是英文书稿完成之后,无论出版过程的曲折以及出版后的纷争,真可说是‘赞美’与‘攻讦’齐飞,毁誉绵绵无尽期”。
作为开创者,何先生的许多成果在学术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当然,如韦伯所言,“一个人的研究无论怎么说,必定是极其不完美的。……我们每一位科学家都知道,一个人所取得的成就,在10年、20年或50年内就会过时。这就是科学的命运,当然,也是科学工作的真正意义所在。这种情况在其他所有的文化领域一般都是如此,但科学服从并投身于这种意义,却有着独特的含义。每一次科学的‘完成’都意味着新的问题,科学请求被人超越,请求相形见绌。任何希望投身于科学的人,都必须面对这一事实”。何先生的一些研究,今天看来有需要改进和发展的余地,但是没有他所做的工作作为起点,改进和发展也无从谈起。陈寅恪先生在著名的《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文中有言:“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由此而言,尽管何先生的一些研究会被超越,但是他的以学术为志业的人生追求,他在学术上的创新精神以及他的“大历史”史观,却永不会过时,值得后人敬仰和效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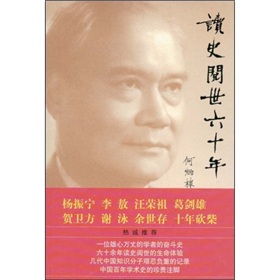
本文写作参考了何炳棣《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台版序言,汪荣祖《何炳棣:一个历史学家的历史》(刊于《读书》,2002年02期)及拙作《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追忆何炳棣先生》(刊于《中华读书报》2012年06月20日07版)
(作者为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
编辑:李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