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第一流的学问”
——浅谈何炳棣先生治史的特点
(之一)
李伯重
《文汇学人》 2017.12.08
和何先生交往,得到的一个深刻印象是他在内心中随时都充满激情,充满对学问真谛的追求的冲动。他总是想不断改进自己的研究,永无止境。这种追求完美的激情使得他经常不得安宁。英国作家勒卡雷说一个好作家在创作时“找不到可休息的场所,找不到伙伴和活动使自己得到安逸。任何局外人的判断也比不上他内心的正确判断……”这也是何先生的日常心态。这种激情,也使得他有一种战士的性格,在学术上经常和人“开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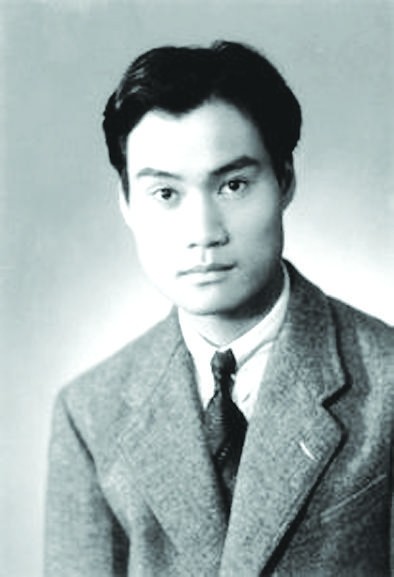
1988年,我去洛杉矶加州大学讲学。在此期间,曾专程去附近的尔湾加州大学拜访何炳棣先生。他和我畅谈,说做学问就要“做第一流的学问”。这句话给我深刻的印象,终身难忘。如今在追思何先生的学问时,深切感到他用他的一生,实践了他要“做第一流的学问”的信念。
对于何先生的学问,我没有资格做评论。但是对于他如何做学问,却有一些感受。在这里,我就凭我自己的理解,来谈谈他是如何做到“做第一流的学问”的。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够“做第一流的学问”,原因有四:他以学术为志业,他的创新精神,他对新事物的开放心态,以及他的“大历史”史观。
志业
1919年,韦伯在慕尼黑大学为青年学生们作了一个题为《以学术为业》的讲演。在这个激励了几代人的著名讲演中,韦伯说:任何人,如果无法把学术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他便同学术无缘了。……这个人便不会有科学的志向,他也不该再做下去了。因为无论什么事情,如果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做,那么对于人来说,都是不值得做的事情”。他接着指出:“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如果选择这条道路,就必须将其当作自己的天职,坚信“我只为我的天职而活着”。
何炳棣先生就是一位“只为我的天职而活着”的学者。在长达近80年的漫长学术生涯中,他对学术一直充满热情。我和他在一起时,他几乎没有多少别的话,从头到尾都只是谈学术。正是这种热情,使得他在几乎是孑然一身的高龄晚年,仍然元气十足,思维活跃不减当年,不断产生新见。
学术生涯是艰苦的。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由于学术研究非常艰苦,所以“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韦伯也说:“如果我们不曾绞尽脑汁,热切地渴望着答案,想法也不会来到脑子里。不管怎么说,研究者必须能够承受存在于一切科学工作中的风险。灵感会不会来呢?他有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工作者,却永远得不出自己的创见。”是的,做真正的学问,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
如果真正热爱学术,在学术之路上遇到困难就不会怨天尤人,自叹命苦;相反,他会把遇到困难视为走向成功路上的必然现象,即古人所云“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之意。正因如此,何炳棣先生在其治学生涯中从来就不畏艰难。他的青年时代在战乱中度过,治学条件十分艰难。到美国求学,虽然可以避开社会动荡而专心读书,但是毕业后找工作时又遇到种种挫折。及至得到了大学教职,方才比较稳定,但又遇到研究方面的问题。在1950年代的美国图书馆,中文文献颇为有限,特别是与何先生研究有关的文献,往往十分匮缺。何先生自己说:“1952年夏,才第一次有机会去美国东岸搜集清史资料。……同年秋冬代校方向温哥华(Vancouver)华商筹款购书的工作也初见成效。当时五千加币还能买不少书,第一批有伪满原版的《清实录》和商务印书馆影缩洋装本的五省通志(畿辅、山东、浙江、湖北、广东)。”中文文献不够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于是他用尽一切方法去寻找资料。到1966年,他当选为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他即利用这个身份,经常借开会之机,到台湾查阅资料。我国大陆著名史家王仲荦先生于1986年去世后,何先生购得王先生藏书,这批藏书对何先生晚年进行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其传递也成为史坛美谈。
和何先生交往,得到的一个深刻印象是他在内心中随时都充满激情,充满对学问真谛的追求的冲动。他总是想不断改进自己的研究,永无止境。这种追求完美的激情使得他经常不得安宁。英国作家勒卡雷(John le Carré,即David John Moore Conwell)说一个好作家在创作时“找不到可休息的场所,找不到伙伴和活动使自己得到安逸。任何局外人的判断也比不上他内心的正确判断。一旦作家从内心的紊乱中理出头绪,就应该按任何评论家想像不到的无情规范约束自己写作;当他沽名钓誉时,他就脱离了自我生活,脱离了对自己灵魂最深处世界的探索”。这也是何先生的日常心态。这种激情,也使得他有一种战士的性格,在学术上经常和人“开战”。大家公认他脾气暴躁,易与人发生冲突,批评人毫不留情面。但这实际上常常只是因为他用“第一流学问”为标准去衡量他人成果的缘故。他不仅对侪辈成果多有批评,而且对自己过去的工作也会表现出不满意。这种“好战”的个性,恰如韦伯所言:“在科学的领地,个性是只有那些全心服膺他的学科要求的人才具备的,不惟在如此。我们不知道有哪位伟大的艺术家,他除了献身于自己的工作,完全献身于自己的工作,还会做别的事情。”
如后所言,何先生一生,在中国史研究中不断更换领域。每次更换到一个新的领域,都需要足够的专业知识。何先生在80高龄时,由原先长期从事的明清经济史转入先秦思想史这样一个相去甚远的领域。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是匪夷所思,其难度之大难以想象。然而何先生将克服所遇到的困难化为战斗的乐趣,越做越高兴。虽然他旧学功底很好,但要做好这个“大转向”,当然也需要进行知识上的“补课”。为此,他又重新拿起少年时代读过的先秦经典,认真研读,并广泛阅览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这种精神确实值得我们敬佩。
编辑:李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