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加利亚画家帕斯金(JulesPascin)的《灰姑娘的马车》(1929年)藏美国盖蒂博物馆
戴望舒在《灰姑娘》中,介绍女主角得名的缘由时说:“当她做完了她的事,便置身于烟囱角边,坐在灰烬上,因此家里人都称她做‘煨灶猫’。”突发奇想用了“煨灶猫”这样的方言俚语,并在后文中屡屡出现,虽然并不忠实于原文,可经过这样的加工改造,却平添了活泼新鲜的意趣。
赵景深写过一篇《安徒生的玻璃鞋》(载1929年《文学周报》第七卷),讥讽百星大戏院在电影《玻璃鞋》上映前所刊登的广告,竟然大肆宣传原作《灰姑娘》是所谓“德国文学家的杰作,童话大家安徒生的名著”,非但张冠李戴搞错了作者,就连无缘无故卷入其中的安徒生也莫名其妙被篡改了国籍,“不知安徒生在泉下当作何感想,怕不左右做人难也”。然而仔细追究其原委,恐怕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戏院。以“玻璃鞋”之名译介这个故事的,始见于孙毓修主编的《童话》丛书第一集第十四编(商务印书馆,1912年)。但孙氏并未交代所依据的底本,很可能“是取材于故事读本,而不是取材于专书”(赵景深《孙毓修童话的来源》,载1928年《大江月刊》十一月号),
内容也多有删略改窜。在西方童话的译介工作方兴未艾之际,人们对其来历渊源确实多存隔膜。戏院方面未予细察,实属情有可原,倒也不必过分苛责。好在此后围绕这则童话的翻译和研究不断出现,读者们对灰姑娘日渐熟悉,再也不会闹出类似的笑话了。
佩罗版灰姑娘的翻译
灰姑娘的故事在欧洲流传久远,留存了各种在细节上多有出入的版本。近代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收录在法国作家佩罗编著的《鹅妈妈故事集》中。孙毓修编译的《玻璃鞋》有不少自出机杼的改编,已经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了,但就主要内容而言,与佩罗版灰姑娘故事最为相似。孙氏大胆尝试用白话来叙述,显得颇为与众不同,可惜态度极其敷衍随意,不少情节都因为前后失据而多有龃龉。所以没过多久,就招致周作人的严厉批评。周氏在《童话略论》(载1913年
《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卷第八册)中说:“《玻璃鞋》者,通称《灰娘》(Cinderella)。其事皆根于上古礼俗,颇耐探讨。今所通用,以法Perrault所述本为最佳。华译删易过多,致失其意。如瓜车鼠马,托之梦中,老婆亦突然而来,线索不接。执鞋求妇,不与失履相应,则后之适合为无因,殊病支离也。”未曾点名道姓的“华译”即孙氏译本,对其草率行事显然非常不满。除了情节多有疏漏,孙毓修还喜欢越俎代庖地发表意见。一提到王子举办舞会,他就按捺不住来了一通洋洋洒洒的议论,一方面指出“舞蹈之事,我们上古尧舜之时便已有了”,“诸君高兴起来手要乱动,脚要乱跳,人皆说你快活得手舞足蹈,即此便是舞蹈的见端”,另一方面又强调“现在说的跳舞,原是外国风俗,花样甚多,一言难尽。外国人盛行此事,一是寻些快活,二是做个男子和女子相交的礼节,或者从此定了婚的也是有的”,还不厌其烦地补充道“有专门学堂教人舞蹈之法,学过数年,方能合拍”。这些漫无边际的即兴品评,只会令读者感到枝蔓芜杂。因此张谷若回忆儿时翻览的《玻璃鞋》等童话,虽盛赞“这许多美丽故事的一切人物,都是我日思夜梦中的良友好伴”(《关于我自己(一)》,载1928年2月26日《申报》),可是对孙氏“喜欢附加案语”,“大发其议论”(《玻璃鞋》,载1926年12月23日《申报》),依然多有怨言。当然,尽管其编译多有疏漏,还是能引领风气之先。对此周作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童话,未经蒐集,今所有者,出于传译,有《大拇指》及《玻璃鞋》二种为佳,以其系纯正童话。”提到的这两部作品都来自孙毓修主编的《童话》丛书。在近代儿童文学尚处于筚路蓝缕的时候,他确实有导夫先路之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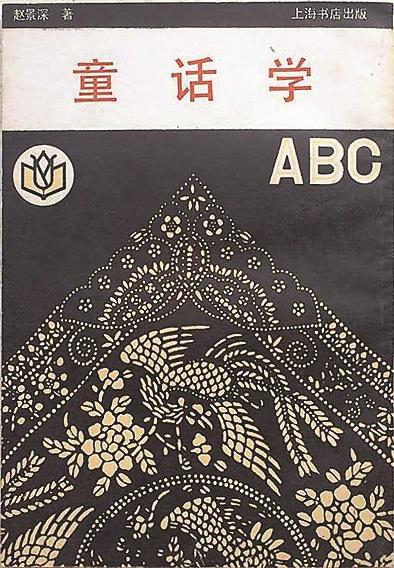
▲赵景深及《童话概要》《童话学ABC》

孙毓修的《玻璃鞋》并未如实呈现佩罗版的原貌,这个缺憾在十余年后终于由戴望舒来加以弥补。他完整地翻译了《鹅妈妈的故事》(开明书店,1928年),在《序引》里对这些作品赞不绝口,说它们“都是些流行于儿童口中的古传说,并不是贝洛尔的聪明的创作;他不过利用他轻倩动人的笔致把它们写成文学,替它们添了不少的神韵”。尽管只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但除了极个别地方略显生涩,其译笔还是相当流畅生动的。比如在《灰姑娘》中,介绍女主角得名的缘由时说:“当她做完了她的事,便置身于烟囱角边,坐在灰烬上,因此家里人都称她做‘煨灶猫’。那第二个女儿,没有像她大姊姊那样粗野,只称她做‘灰姑娘’。”突发奇想用了“煨灶猫”这样的方言俚语,并在后文中屡屡出现,虽然并不忠实于原文,可经过这样的加工改造,却平添了活泼新鲜的意趣。后来一些比较严谨的译本,将此处译为“家里人,尤其是继母带来的两个姐姐,总是讥笑她,说她像个灰人,喜欢开玩笑的二姐干脆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她‘灰姑娘’”(董天琦译《佩罗童话》,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就不免太过拘谨而缺乏神采。类似的例子在戴译本里还有不少,如提到那六个由壁虎变成的跟班:“他们的衣服用花边镶着,好像是一晌过着这种生活似的。”讲到大姐对灰姑娘的呵斥:“拿衫子借给一个像你这样的煨灶猫!我一定真个发疯了!”都令人感到绘声绘色,增添了作品的鲜活灵动。即便是些细枝末节,看来他也认真琢磨过。比如提及大姐的姓名,取法文谐音译作“杰浮德”,就很能引导读者循名而责实。可惜戴望舒去世后,其译本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在1955年改版重印,虽然补正了译文中的一些疏漏,但编辑大概是为了遵守所谓的“规范”,自作主张地把“一晌”改成“一向”,用“真是”替换“一定真个”,引人遐想的“杰浮德”更是成了平庸无奇的“夏洛特”,实在有点得不偿失。
戴译本在后来颇受欢迎,屡屡付梓重印,在流传推广的时候,这篇《灰姑娘》也格外受到青睐。开明书店拟定过一则戴译《鹅妈妈的故事》第六版的广告(载1935年1月18日《申报》),称佩罗凭借此书使得“他的童话作家的大名,便因此而成了不朽”,尤其标举“内中《灰姑娘》一篇,流入英国,便把本来流行于英国的民间故事《猫皮》毁灭无闻,由此可见本书之魔力了”。提到的那篇英国童话《猫皮》,内容与《灰姑娘》相仿,同样是妇孺皆知的作品。而出版方大肆渲染,认为《灰姑娘》已经反客为主,后来居上。以此篇作为佩罗童话的代表,足见其早已为读者所熟知。


▲戴望舒及其所译《鹅妈妈的故事》
韦丛芜稍后也翻译过佩罗(韦氏译作“贝罗”)的这部童话集(只有《小红帽》未译出),并取其中的《睡美人》作为书名(北新书局,1929)。长期在北京求学和工作的韦丛芜,其译文风格与一直在上海生活的戴望舒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比,从他为这篇所取的题名“灰妞儿”便可见一斑。同样讲述女主角遭受歧视,韦氏译作“她们通常都叫她灰丫头;但是较小的妹妹,不像她姊姊那么酷虐,叫她作灰妞儿”,“丫头”和“妞儿”无疑都源自他所熟悉的北方方言。然而在后文中,他提到大姐嘲笑灰姑娘是 “肮脏的煤丫头”,并说第二晚的舞会,“煤妮也去了”,不知为什么忽然改变了称呼。兴许是担心反复使用同一称谓容易使读者生厌,可是上下文全无交代,终究不免令人感到突兀。韦丛芜与其兄韦素园早年深得鲁迅的赏识,在其引导下组织未名社,接手编印《未名丛刊》,收入不少社员的翻译作品。其中一位社员李霁野回忆过鲁迅当年悉心给予指导的情景:“先生在看了译稿之后,在要斟酌修改的地方,总用小纸条夹记,当面和我们商量改定。”(《鲁迅先生与未名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鲁迅历来主张“硬译”,甚至为了“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鲁迅全集》第十卷《译文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想必是受到他的影响,韦丛芜也多采用直译。比如讲到灰姑娘盛装出席舞会时,“室内立刻便有一阵非常的寂静。他们停止了跳舞,停奏了提琴,一切的跳舞者都那般渴想着去审视这位不认识的宾客的奇美”;随着午夜来临,灰姑娘夺门而出,守卫的士兵向紧追不舍的王子汇报,“他们并没有看见人出去,除了一个年青的女子,穿的很坏,态度多像乡村女子,少像大家小姐”,遣词造句都有很明显的欧化倾向,与原文对照虽可谓萧规曹随,还是稍嫌诘屈聱牙。在全书卷首有一篇类似序言的《故事——新的和旧的》,韦丛芜在文中强调,“倘若要养成儿童读书的习惯,起初就应该给他好的书,可以快乐地欣赏,珍奇地收藏——书的内容要适合儿童的程度”,就本书的译笔而言,恐怕还没有完全达到这个标准。
潘树声在五十年代初翻译过不少苏联文学作品和科普读物,其中有一本《水晶鞋》(知识书店,1950年),包括了三篇童话。令人深感蹊跷的是,译者并未交代那篇最重要的故事的来历,不过内容情节与佩罗版极其相似,应该是某位俄语作家据此翻译而成的。虽说是根据俄文本转译,可有些细节还是很耐人寻味的,如讲到女主角的不幸时说:“她继母的大女儿称她为‘脏鬼’。但是她继母的小女儿却不像她姐姐那样没礼貌,所以她不叫她‘脏鬼’,而是唤她作‘卓鲁什卡’(意即叫化子)。”俄文本在翻译中做了必要的归化处理,在汉译时也相应表现出不同的面貌。尤其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佩罗原作中那位热心助人的仙女教母,在此书中居然被唤作“老妖婆”。而类似的情况并非仅见,稍后还有一种根据俄译本转译的佩罗版《灰姑娘》(尚佩秋译,曹靖华校,真理书店,1951年),同样语出不逊地称她为“会使魔法的老太婆”。沃尔夫冈·贝林格在勾勒巫术衍变时曾提道:“俄国等社会主义统治者们试图粉碎巫术、萨满教和宗教;同时,像这些帝国从前的统治者一样,他们宣称对其臣民的信仰有控制权。”(《巫师与猎巫:一部全球史》第六章《19世纪和20世纪的猎巫》,何美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是否因为这位仙女频频显示神通,才被俄译者们视为异类而遭受污名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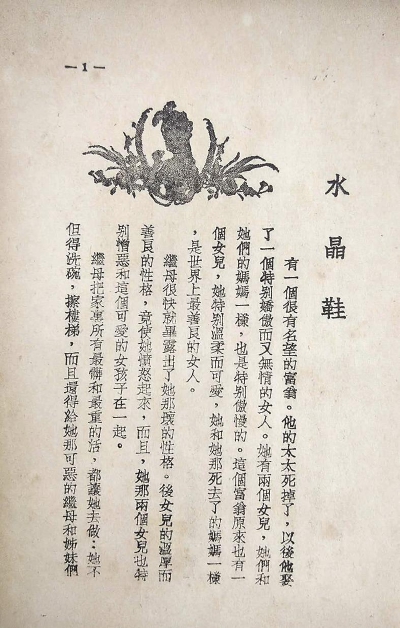
▲潘树声译《水晶鞋》

▲尚佩秋译、曹靖华《灰姑娘》
佩罗此书原名《附道德训诫的古代故事》,在每个故事后都会借题发挥,阐发一番微言大义。讲完《灰姑娘》时,他除了义正辞严地告诫读者,“女人天生丽质当然值得骄傲,刻意打扮的丑女只会惹人耻笑,要想获得幸福,心地善良必不可少,因为有时候它比任何条件都更重要”,还揭开一些令人困惑的谜团,“故事中的教母,其实是上帝的化身,他总是帮助那些受苦受难的人,那两位姐姐之所以没受到惩罚,是因为她们已经悔过自新”(据董天琦译《佩罗童话》)。但上述各位译者,都将这些说辞略去未译。佩罗苦口婆心的教导针对的原本是成年人,而戴译本收录于《世界少年文学丛刊》,韦译本“是专供儿童阅览的”(《故事——新的和旧的》),潘译本则被列入“新少年读物”丛书,既然预设的读者都是少年儿童,在翻译时有所取舍也就容易理解了。正如戴望舒在《序引》中所言:“这一种比较的沉闷而又不合现代的字句,我实在不愿意让那里面所包含的道德观念来束缚了小朋友们活泼的灵魂,竟自大胆地节去了。”顾均正在推荐这本《鹅母亲故事》时,曾介绍“每一个故事的结束都附着一段很短的道德的韵语,但在英国的翻译本子里,则大都是被略去的”(《世界童话名著介绍(七)》,载1926年《小说月报》第十七卷第八期),可见如此处理其实也不乏先例。
格林版灰姑娘的翻译
除了法国的佩罗版,灰姑娘故事还有一种脍炙人口的重要变型,见于德国格林兄弟编著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有些汉译本就转而以此为据。率先问世的是一篇题名古怪的《阿育博德露》(载1910年《东方杂志》第七卷第三期),通篇以文言译就,如述及女主角遭受姐姐们欺凌:“二女遂尽褫其身上之艳服,而与以敝衣,恶嘲毒骂,推之入厨。女不得不执此卑贱之役,未曙而起,汲水举火,劳苦不可名状。而二姊犹复时时苛扰,戏侮不止。及夕,女倦极欲睡,则不得榻,于是卧于灶次,横身炉灰之中,不免尘垢沾污,面目黧黑。二女遂呼之曰阿育博德露。”在“阿育博德露”下另有小字注文:“犹言灰中人也。”可以推知此处实为Aschenputtel的音译,意即灰姑娘。这位未署名的译者文笔简练雅饬,读来饶有文言小说的意味。如讲起灰姑娘受到刁难,不能参加舞会时的场景,“阿育博德露感伤怀抱,坐于墓树之下,高吟曰:‘嗟长榛之依依兮,安得赐我以锦衣。’其鸟友自树上闻之,遽奋翮翔去,从市中求得锦绣之衣,绚丽之履,攫而飞至,掷与女”;当王子误将两位姐姐带回宫时,“归途过阿育博德露所植之榛树下,上有一小鸽巢枝而歌曰:‘归去视金履,履小何不伦。使君自有妇,莫恤马前人。’”待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王子遂掖阿育博德路登骑,扬扬出门去。二人过榛树之下,则闻鸽歌曰:‘归去视金履,金履实宜人。王子多艳福,满载马头春。’”穿插在文中的几首歌谣,或拟楚辞,或仿乐府,浑然天成,颇具巧思,毋庸赘言经过仔细的推敲。《东方杂志》连载过数十篇同类作品,均冠以“时谐”的总题名,最后还结集成书(《说部丛书》第二集第九十二编,商务印书馆,1915年),影响也随之更为广泛深远。然而因为使用文言来翻译,也频频遭到诟病非议。赵景深指摘此书“是用文言写的,和儿童不很接近,并且没有标明那是儿童用书,实在是一件缺憾。况且童话的特点,就在于小儿说话一般的文章,现在他用古文腔调说起来,弄得一点生趣也没有了”(《教育童话家格林弟兄传略(四)》,载1922年5月27日《晨报副镌》)。顾均正则将此书与孙毓修主编的《童话》丛书互较长短,认为“这书是用文言译的,它包含的分量虽较《童话》第一集为多,但因其读者并不是儿童,所以对于儿童教育上的影响,倒远在《童话》第一集之下”(《格林故事集序》,载张昌祈译《雪婆婆》卷首,开明书店,1932年)。站在小读者的立场,文言译本确实有些不合时宜。
此后为了满足儿童的阅读需求,陆续出现了不少白话译本,如俞艺香译《灰娘》(春泥书店,1929年)、张昌祈译《雪婆婆》(开明书店,1932年)中的
《灰姑娘》、魏以新译《格林童话全集》(商务印书馆,1934年)中的《灰丫头》、张亦朋译《格林童话全集》(启明书局,1939年)中的《灰丫头》、丰华瞻译《格林姆童话全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52年)中的《灰姑娘》等。这些译本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俞艺香“本想从德文直译”,因条件所限只能据英译本转译(见《引言》);张亦朋所译号称“全集”,实际上只选了99篇,而且“系根据柯林司版的《格林兄弟童话集》的英译本译出”(见《小引》);丰华瞻的译本则“是由英文本译出的”,“另外参考苏联的选译本”(见《译者序》);魏以新的译本最为严谨,不仅依照“德国名著丛书版本译出,共二百一十篇”,积疑之处还承德国语言学家欧特曼教授襄助,“因其口授而完全译出”(见《译者的话》)。此外还有一篇乐群翻译的《灰姑娘》(载1935年《浙光》第一卷第一期),在标题下注明“原著德国裴立剌”,“裴立剌”想来是佩罗(Perrault)的另一种音译,却蹊跷地成了德国人,而从内容来看其实源自格林童话。恐怕是译者辗转稗贩,以讹传讹,正像赵景深所嘲讽过的“德国童话大家安徒生”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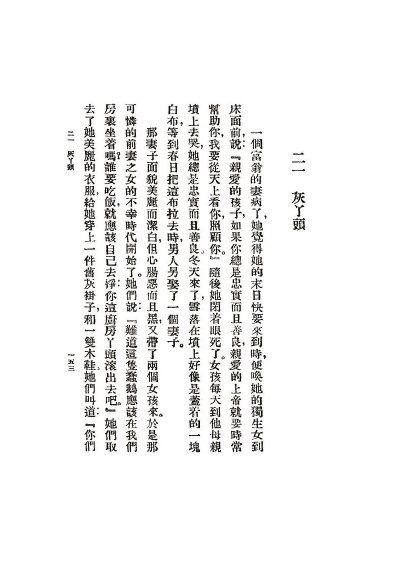
魏以新译《灰丫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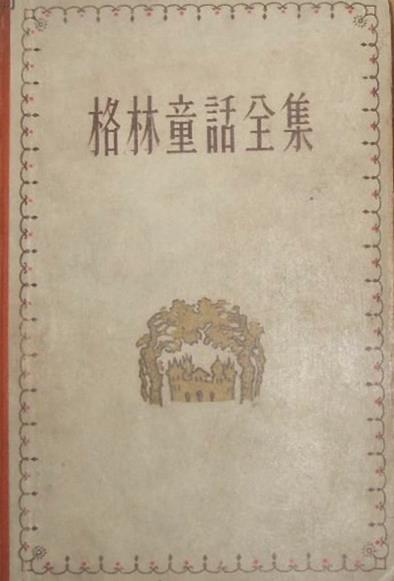
魏以新译《格林童话全集》修订版
魏以新的译文不仅平实晓畅,细节处理也更准确贴切。比如当继母把扁豆倒入灰堆,责令灰姑娘挑拣出来时,魏氏译作“女孩从后门出去到园里叫道:‘你们驯良的鸽子,你们斑鸠,一切天下的鸟儿,来帮我把好的拣到盆儿里,坏的吞到肚子里。’”张昌祈译为“灰姑娘有许多鸟朋友,她便跑进花园去唤道:‘我的小朋友们,来罢,你们的朋友灰姑娘在等候你们;用你们明亮的眼睛,尖锐的嘴巴,立刻把灰里的豌豆捡起。’”不仅把扁豆换成了豌豆,其余内容也多有损益。张亦朋译作“女孩从后门出去走到园里叫道:‘良善的鸽子,和天下一切的鸟儿,都来帮我拣,把好的拣到盆里,坏的吃到肚里。’”虽然严谨了许多,但也遗漏了原作里出现过的斑鸠。另如说起王子追赶灰姑娘,魏译本作“王子用了一条计,叫人把全楼梯都涂上沥青。女孩跳下去时,左脚的拖鞋黏在上面了”。张昌祈译作“王子因为决意要找出这最美丽的姑娘的住处,所以预先吩咐侍役们在宫前的石阶上厚厚的涂上一层胶质;灰姑娘跑过时,一只跳舞鞋竟被黏住”,用“胶质”就难免有些含糊其辞。而乐群的译文则径直作“灰姑娘因为逃得太快,所以她的一只小缎鞋脱落在地上”,绝口不提王子所设的计策,丢鞋居然成了灰姑娘在仓皇失措间的意外。
当然,其余各种译本也并非一无是处。比如讲到王子因误会而将两位姐姐带回宫时,魏译本作“那两个鸽子蹲在榛树上叫道:‘汝刻底谷克,汝刻底谷克,鞋子里面有血,鞋子太小了,真新娘坐在家里’”;等最终找到灰姑娘时,魏译本又作“那两个白鸽叫道:‘汝刻底谷克,汝刻底谷克,鞋子里没有血,鞋子不小,他引真新娘回家。’”反复出现的“汝刻底谷克”采取音译的方式,令读者徒费猜疑。而张亦朋将这一句译作“回过去看”,丰华瞻译为“回过头来瞧”,就明白显豁得多。魏以新在修订时也借鉴了各家译文,将这一句改为“回过头来看”,其余部分也多有润饰(见修订版《格林童话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正因为坚持不懈而精益求精,魏译本在日后才会得到读者们的普遍认可。
格林版灰姑娘在人物、情节等方面都有了不少新变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增添了不少血腥的场面。在佩罗版中,姐姐们费尽力气也未能穿上那只鞋,只能徒呼奈何而就此罢手;到了格林版中,两人为了攀上高枝,却不惜自残肢体,用刀切下脚趾或脚踵。故事结束时,佩罗版的灰姑娘以德报怨,在嫁给王子的同时,又顺带让两位贵族娶了姐姐们;格林版则以牙还牙,让两位姐姐受到严酷的惩罚,被鸽子啄瞎了眼睛。稍事覆核各种源自格林版的汉译本,不难发现有些译者会对原作情节加以删改或省略。张昌祈的译本在讲到姐姐们试穿鞋子时说:“姊姊拿了那只跳舞鞋,试了又试,总是穿不进去。轮到妹妹,她尽力拉扯,可是她的脚太大,结果也是穿不进。”简直就是移花接木,挪用了佩罗版中的情节。到了最后也只说:“王子就带着灰姑娘上马,直回宫中,从此永远在宫中快乐过活。”丝毫不提对两个姐姐有何惩处。乐群的译文尽管提到大女儿为了穿上鞋而割下大脚趾,可轮到二女儿时,就轻描淡写地说她“拿去试穿,亦是不与”。在结束时也仅称王子“预备举行一隆重热闹的婚礼,融洽相处,过他俩安乐的日子,这一场甜蜜的梦,在世间发扬光大,直到永远”,用皆大欢喜的方式来收场。张亦朋的译本虽说大体无误,但在结尾处只说“两个坏姊妹都被白鸽啄去了眼睛”,对照一下魏以新的译文——“新夫妇到教堂去时,大的在右,小的在左,鸽子把她们的眼睛各啄去了一只。以后她们出来时,大的在左,小的在右,鸽子又把她们的眼睛各啄去了一只”——还是省略了许多具体内容。这些程度不一的删略,一方面毫无疑问与各家大多根据英译本等转译有关,另一方面大概或多或少也含有译者刻意为之的因素。张昌祈译本前有顾均正的《格林故事集序》,开宗明义就指出:“在儿童文学中最流行,最适于低年生阅读的作品,应当推格林兄弟的《家庭故事集》。”张亦朋在介绍其翻译初衷时也说:“《格林童话全集》是世界各国儿童都知道和欢迎的一部读物,译者现在把它选译过来,介绍给中国的小朋友,想来也是一样欢迎的。”考虑到读者都是天真烂漫的幼童,并希望借助此书起到引导教育的作用,自然不宜过分渲染暴力血腥的场面。(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作者:杨焄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任思蕴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