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会催生一些看似奇怪的伙伴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催生的最奇怪的一对关系是:一方为美国中情局(CIA)前身、美国二战期间情报组织(OSS)的首领威廉·多诺万(William Donovan);另一方为一群德国犹太人马克思主义者,被多诺万邀请来帮助美国了解纳粹。
《纳粹德国密报:法兰克福学派的战时贡献》(Secret Reports on Nazi Germany: The Frankfurt School Contribution to the War Effort,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包含了二战期间诺伊曼(Franz Neumann)、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和基希海默尔(Otto Kirchheimer)等提交的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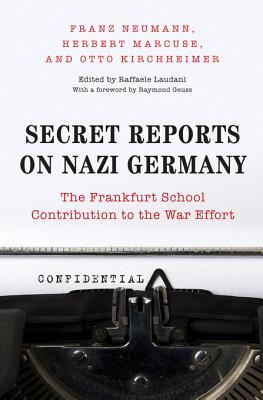
多诺万是经历过一战的经验丰富的老手。1941年,罗斯福总统钦点他建立美国首个专门的非军事情报机构。当时,很多外交政策机构的工作人员认为谍报工作既不体面也不重要。于是,多诺万只能广泛撒网,不仅招募外交官和专业间谍,也吸收了电影导演、犯罪集团成员、运动员和记者从事谍报工作。
在如此多元化的间谍队伍中,诺伊曼脱颖而出。诺伊曼是一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1933年纳粹上台后离开德国,几年后来到美国。1942年,诺伊曼因写作《巨兽》(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一书而成为声名卓著的纳粹问题专家。该作品阐释了纳粹主义是病态的垄断资本主义和残酷的极权主义的结合。
多诺万请诺伊曼领导OSS的研究分析部门,专门研究纳粹统治下的中欧。不久,诺伊曼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同事、哲学家马尔库塞和法学专家基希海默尔也加入进来。社会研究所成立于1923年,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起点,纳粹上台后迁往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法兰克福学派以马克思主义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为区别于传统的标志,强调文化、法律、政治和心理学等的重要作用。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往往不认同苏联和其他一些地方号称继承了马克思衣钵的过于死板的左翼思想。
尽管多诺万与诺伊曼团队之间有巨大的政治和文化鸿沟,但他信任这些激进分子并委以重任,着其提供应对纳粹的建议。正如另一个被指派给诺伊曼的年轻人赫茨(John Herz,后来是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人物)所言:“这就好像是黑格尔左派的精神世界突然短暂地降临在OSS的中欧研究分部。”
这种不同寻常的合作的结果是一系列精彩的报告,供美国政策制定者了解包括反犹主义、纳粹的政治经济、空袭对于平民士气的影响以及公诉战犯的最好方式。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术背景都是如此抽象的领域,如法学、哲学和政治学理论,但他们倒也不失为机敏而实际的政治分析家。他们的报告常不吝指出战时政策的限制,他们也忠告美国政府,存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困难以及精明的预言家甚至也可能局限于过去政治状况的严峻现实。

Franz Neumann
法兰克福学派的担忧
诺伊曼和他的团队似乎误解了一些事情。他们从未真正理解到纳粹反犹的程度,也并未视其为政治病态,而只是视为纳粹政权对某个群体试验其残酷策略的一种方式。诺伊曼的《巨兽》提出现代资本主义是纳粹主义的主要根源,认为德国民主的振兴依赖于对国家经济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修正,而没有预期到以自由民主重新校准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也没有预期到联邦德国等地战后出现的新发展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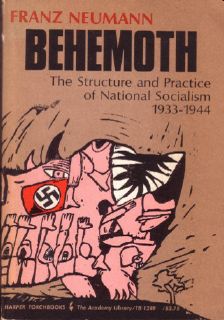
当然他们也有很多贡献。他们对纳粹最后几年中的政治和社会状况的评估大体上被认为是正确的。罗斯福同意了美国财长亨利·摩根索处置战后德国的计划——废除德国现代工业,丘吉尔在各种压力下也勉强同意了。而诺伊曼团队对该计划的批评可能在杜鲁门作出最终放弃该计划的决定中起了很大作用。基希海默尔在其中一份报告中颇有先见之明地指出,美国将来处置战犯时会在法律和消除纳粹在德国的影响力方面面临困境。基希海默尔和同伴们对纽伦堡审判感到失望,赫茨悲痛地将审判描述为“去纳粹化的惨败”,尽管如此,他们的OSS报告却为美国在德国的战后审判提供了大部分理论基础。最显著的是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给美国决策者资政的纲领性意见——同盟国必须停止以一战中认识德国的老眼光来看待纳粹德国。美国只有充分理解了已然偏离熟悉的历史轨道的现实,才能赢得和平并确立新的德国民主的基础。诺伊曼及其团队严厉批评美国决策者仍然将德国视为独裁统治下的“普鲁士”,认为这窜改了纳粹权力结构的实际情况。
法兰克福学派同时担心,同盟国将1945年的德国误认为1918年的德国,这种认知是无法帮助他们领会纳粹是怎样做到让普通德国人拒绝接受在一战结束时遭遇过的投降结果。法兰克福学派指出,纳粹激进分子的反犹主义是为了保证能将更广泛的民众牵扯到纳粹罪行中。当大部分德国人的双手都沾满鲜血,他们将别无选择,只能抵死反抗同盟国。即使一些来自德国的证据显示,战时士气低落,但纳粹依然采取一切手段以保证普通德国人能够坚持下去。
编译/黎文
刊《文汇报》2013.07.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