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勒高夫的作品常常会给读者带来这样的感受:中世纪离我们现在的世界似乎既很近又很远。站在年鉴学派的经典立场上,勒高夫认为,史学的本质在于把握时间和变化,而长时段的优势正在于能够将历史演进中的连续性与断裂性相结合。这正是他选择使用“长中世纪”(5—18世纪)的概念来囊括传统意义上的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代背后的考量。
法国中世纪史学者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大概是作品的中文译介最多的西方当代史家之一。根据我的统计,他的专著和编著中译至今已有12本之多。这种“勒高夫热”自然部分得益于其身为“年鉴学派”当代领军人物与20世纪60年代以降的“新史学”运动领袖的赫赫声名。但同样重要的是,勒高夫从来都乐于保持一种平易近人的学术写作姿态,这使中世纪研究之外的学者乃至非史学专业的普通读者都有兴趣阅读他的作品,而且不难从中获益。新近翻译出版的《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杨嘉彦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以下简称《分期》)让中国读者再次得以领略勒高夫轻快的文风,以及他在学术生涯的最后时光里依旧充沛的学术活力。这本小书的法语原版(Faut-il vraiment découper l’histoire en tranches? Paris: ditions du Seuil)出版于2014年1月,当时的勒高夫已是90岁高龄。3个月后,这位20世纪史学大家与世长辞。《分期》一书是勒高夫为我们留下的最后的史学思考。
囊括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长中世纪”
这部散论(essai)的主题是西方历史中的“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之间的关系。在勒高夫看来,这两个在传统叙事中泾渭分明的时代,更应该在同一个西方历史的大时段中加以理解,他称之为“长中世纪”(long moyen age)。勒高夫选择从“历史分期”这个大问题入手思考。中国读者对历史分期问题不会感到陌生。在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中国史学走向形成的过程中,古史分期问题一度扮演了核心角色。共和国“十七年”史学的“五朵金花”中,分期问题居首,而且与另外两朵金花(“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密切关联。比照中西分期问题可以发现,聚讼最多的都是对上古与现代之间的中间时段的性质与边界的理解:对中国史来说,是所谓的“封建时代”;对西洋史来说,则是“中世纪”。这不是偶然的。正如勒高夫所言:“新时期的一种观念总是反对前一时期的观念,后者总被认为是黑暗的阶段并理应让位于光明。”(《分期》,第34页)与常常被理想化的古典时代不同,中世纪构成了与“现代”相反相成的历史阴影与历史“他者”。勒高夫在《分期》中多次暗示我们,把文艺复兴视为现代的开端与把中世纪视为现代的对立,是伴随着现代西方的诞生而出现的同一种历史叙事的两面。《分期》一书本质上是勒高夫对这种经典历史阐释法的学术史批判。在对于这种西方历史的传统分期的形成史与修正史的辨析中,勒高夫阐发了他对“作为社会科学的史学研究”(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这也是著名的《年鉴》期刊1994年更名之后的副标题)的性质与前工业化时代的欧洲的历史进程的个人见解。
《分期》正文部分共分八章。第一章提纲挈领地概述了三种在前现代西方最有影响的历史分期方式。它们均具有十分强烈的基督教色彩。首先是以圣经旧约《但以理书》中的四兽异象为原型的统治帝国更替模式。第二种是以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第九卷为代表的、围绕着圣经历史建构并比照人生阶段的人类历史六时期模式。第三种分期模式以人类的救赎历史为主线,勒高夫以13世纪圣徒传集《黄金传说》为其代表(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于2016年的该作品中译本的译名为《金色传奇》)。在其中,亚当以来的人类历史被分割为“迷途”、“更新”、“和解”与“朝圣”四段。第二章梳理现代历史分期模式的发生史。彼得拉克在14世纪最先使用了区别于古代和当下的“中间时代”一词。德国新教史学家塞拉里乌斯在17世纪第一次用“古代—中世纪—现代”的三分法写作通史,以“中世纪”为主题的一卷以君士坦丁皇帝始,以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终。直到18世纪末,“中世纪”都是一个与黑暗和蒙昧相关的负面概念。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与中世纪文献学的兴起开始为“中世纪”洗刷污名。第三章从教学和学科建制的角度继续讨论现代史学。通过罗列欧洲各国大学中史学讲席的设置时间等方式,勒高夫勾勒了历史如何在16—19世纪期间逐步演化为自主的教育和研究对象。
第四、五章的主题是文艺复兴的学术史。勒高夫先是探讨了两位19世纪的史学家对作为一个独立历史时期的“文艺复兴”的“发明”。一位是勒高夫所钟爱的法国史家儒勒·米什莱(可进一步参考勒高夫的论文《米什莱的几个中世纪》,收录于《试谈另一个中世纪》,周莽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另一位是德语文化史家雅各布·布克哈特。米什莱在1840—1841年法兰西公学院的讲座中开创性地
使用“重生”的概念命名14—16世纪发生在意大利各个城邦与公国的文化勃兴。布克哈特的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则首次系统地提出了文艺复兴时代“人的发现”、“对世界的发现”与人文主义的兴起等经典命题。第五章主要评述了四位20世纪的文艺复兴阐释者:保罗·克利斯特勒、欧金尼奥·加林、欧文·潘诺夫斯基与让·德吕莫。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推进和深化了米什莱与布克哈特奠定的历史叙事。以返回古代(克利斯特勒特别强调这个“古代”包括基督教教父传统)和“重生”意识(潘诺夫斯基的学术主题)为特征的文艺复兴,完成了与中世纪的决裂(被加林阐释为对中世纪日益僵化的思想体系的摧毁),开启了西方的现代进程(德吕莫把地理大发现与宗教改革也视为广义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一部分)。在第六章,勒高夫对“文艺复兴现代开端说”的另一面,即“中世纪黑暗说”,进行了全面驳斥。传统叙事认定为文艺复兴开创的正面价值,如对古典学问的复兴、革新与当代意识的出现,人本与理性精神、审美与艺术的发展,中世纪都不缺少。而中世纪被人诟病的阴暗面,如宗教战争与对巫术的迫害,在15世纪之后依旧延续、甚至加剧。
第七章是《分期》全书的核心。勒高夫最终“图穷匕见”,正式提出了“长中世纪”的说法。用他自己的话说:“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社会、文化领域中,在16世纪,甚至直到18世纪中叶之前,都不曾有过能证明将中世纪与一个新的、不同的时代即文艺复兴相分离的根本改变。”(《分期》,第93页)勒高夫所枚举的各项例证可大致概括如下。新大陆在15世纪末被欧洲“发现”,但直到18世纪,美洲才在西方世界成为具有影响力的经济与政治实体。欧洲的远洋航海技术在12—13世纪就已经有所发展,但直到18世纪中叶以后才实现大突破。在盛期中世纪时奠定的欧洲农业经济格局直到17世纪之后才逐渐因为商业资本的介入而发生重大改变。欧洲的社会生活,包括收成与饥荒、饮食、金属工具、服装时尚与仪礼规范,在11—18世纪期间都呈现出强烈的延续性。16世纪的宗教战争与17世纪的英荷共和革命并没有彻底颠覆传统欧洲的君主继承制与以王朝关系为基础的国际格局。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对中世纪“封建”经济的真正胜利发生在18世纪后期。直到启蒙运动,基督教对欧洲思想界的绝对宰制才真正终结。总而言之,在勒高夫看来,欧洲历史的现代转折并非文艺复兴,而是发生在18世纪下半叶的诸多变革:瓦特与蒸汽机、狄德罗与《百科全书》、斯密与《国富论》、美国与法国的大西洋革命。不过,勒高夫也公正地概述了佛朗哥·卡蒂尼等学者持有的“1492年变革说”,后者把15、16世纪之交视为欧洲史上承上启下的决定性时代。
在作为全书结语的第八章,勒高夫回到了历史分期问题,并对于历史科学本身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站在年鉴学派的经典立场上,勒高夫认为,史学的本质在于把握时间和变化,而长时段(longue durée)的优势正在于能够将历史演进中的连续性与断裂性相结合。这正是他选择使用“长中世纪”(5—18世纪)的概念来囊括传统意义上的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代背后的考量。历史分期或许无法有效地把握全球格局的历史变迁,但对于有限的文明区域(如欧洲),它依旧是可能、必要而且有益的史学工作。
总体而言,《分期》是一本阅读体验非常好的书。勒高夫以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把历史叙述、学术史与个人观点出色地结合在了一起,可以说是“大师小书”的典范。不过,从专业读者的角度来看,《分期》的有些部分,特别是反对“黑暗中世纪说”的第六章,近乎教科书式的事实罗列略显乏味。但这种普及读物的写法应该是勒高夫刻意为之。从1959年进入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第六部(也就是后来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到1969年担任《年鉴》期刊(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主编、1972年接替费尔南·布罗代尔出任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勒高夫40岁出头就奠定了自己在学界的地位。而在学术象牙塔之外,向大众文化推介中世纪同样是勒高夫终身倾力的志业。1968年,勒高夫在极度繁忙的学术工作之余选择接手了流行广播节目“周一说历史”(Les lundis de l’histoire)的主持工作,向大众普及史学界的最新进展。节目反响颇佳。他也是通俗历史读物与通史写作的高手,已有的中译作品包括《中世纪文明》(徐家玲译,格致出版社2011年版)、《给我的孩子讲欧洲》(王佳玘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与《给我的孩子讲中世纪》(林泉喜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勒高夫属于法语中称之为historien engagé的那种热衷于在学术专业与现实世界之间建立关联的历史学家。在1983年,他受法国政府之邀,利用自己对时间体验的学术敏感(中世纪不同人群的时间感受是勒高夫学术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参与了巴黎大众交通系统的设计工作。21世纪初,配合扩张中的“欧盟”的文化认同建设,勒高夫为由他自己主编的书系“欧洲的形成”(The Making of Europe)撰写了以“作为现实与表征的欧洲形成于中世纪”为主题的通俗读物,同时以五种欧洲语言出版。英文书名为《欧洲的诞生》(The Birth of Europe);法文书名则和《分期》一样是一个问句《欧洲诞生于中世纪吗?》(L’Europe est-elle née au Moyen Age?)。这本书得到了一些欧洲政要的公开称赞。一位评论家称,这部书让勒高夫成为了“欧盟”的“宫廷史家”。
不过,大概出于对文意的直白晓畅的追求,勒高夫在《分期》中的一些局部论断似有可商榷之处。以第一章为例。勒高夫认为奥古斯丁的人类历史六阶段分期模式是一种悲观的世界衰落理论,“直到18世纪都在阻碍着进步理念的诞生”(《分期》,第5—6页)。但正如20世纪的奥裔学者盖尔哈特·拉德纳关于早期基督教中的改革理念的经典研究所指出的(Gerhart Ladner, The Idea of Reform: Its Impact on Christian Thought and Action in the Age of the Fathe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奥古斯丁的历史六阶段论其实体现了一种积极的历史意识:人类的历史命运并非重返伊甸园中的纯真幼年,而是在革新中进步(reformatio ad melius)。再如,勒高夫暗示,以人类救赎为线索进行历史分期的做法是13世纪的创新。但这种史观和分期方式显然可以上溯到新约中的保罗神学,即认为人类先后经历了“前律法”(ante legem)、“律法”(sub lege)与“神恩”(sub gratia)三个历史阶段。不过,《分期》中类似的可商榷之处并不影响全书的立论。

▲法国史家儒勒·米什莱(1798—1874)开创性地使用“重生”的概念命名14—16世纪发生在意大利各个城邦与公国的文化勃兴。
传统分期“晚期中世纪”
在批判“中世纪黑暗说”时,勒高夫所引征的主要是盛期中世纪,特别是 “12世纪文艺复兴”与13世纪经院哲学的文化与社会成就。这与他个人的学术研究重心有关。他的早期著作《中世纪知识分子》(张弘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的主题是职业知识人在12世纪的出现与在13世纪的体制化[就是这部著作打动了布罗代尔,使他决定把这位未能完成教职论文(these d’etat)的年轻人召入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工作];他的两部传记研究《圣路易》(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与《阿西西的圣方济各》(Saint Fran?ois d’Assise, Paris: Gallimard, 1999),传主都是13世纪的人物;在他著名的“炼狱的诞生”命题中,12世纪出现的炼狱意象的实体化,意味着以时间与劳作(包括祈祷和奉献)换取拯救这一中古基督教最大特征的确立(La Naissance du Purgatoire, Paris: Gallimard, 1981);他对于高利贷的研究(参考《钱袋与永生》,周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则突出了这种经济活动在西欧如何从最初被否认与排斥,到13世纪时被逐渐接受,体现了中世纪宗教—经济思想中蕴藏的现代性因素……
在这个意义上,身为盛期中世纪学者的勒高夫对文艺复兴史学进行反思,应当算是一次不大不小的学术跨界。可能与他的盛期中世纪视角有关,在《分期》中,勒高夫没有论及与他的主题密切相关的另一项传统分期“晚期中世纪”(大致1350—1500年)及其当代学术史,我们不妨在这里简略地加以补充。约翰·赫伊津哈的《中世纪的秋天:14世纪和15世纪法国与荷兰的生活、思想与艺术》(何道宽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出现在了《分期》书末的参考文献中,但勒高夫并未在正文中提及。在这部1919年用荷兰语写就的名著中,赫伊津哈以一种挽歌式的笔调勾画了勃艮第公国(位于尼德兰南部地区)与法国北部的法语文化圈(特别是宫廷)在晚期中世纪时一种“过度成熟”的文化氛围。“晚期中世纪并非一个新时代的起点,而是一个过度衰老的时代的缓慢消逝。”赫伊津哈的“北方文艺复兴”的迷人的病态,与布克哈特式健康、昂扬的文艺复兴形象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1924年,该书的首部英译本出版,在赫伊津哈本人的认可下,标题定为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中世纪的衰落)。而在1996年问世的新译本则把标题改为The Autumn of the Middle Age(中世纪的秋天)。译名的变动自然是出于对原书名中herfsttij(相当于英文中的fall tide)一词译法的重新考量,但背后的学术史背景是近几十年来几代学者对晚期中世纪文化活力与创新越来越积极的评价。如荷兰学者海科·奥伯曼就多少有点挑衅地把晚期中世纪唯名论神学的成就称为“中世纪神学的丰收”(Heiko Oberman, The Harvest of Medieval Theolog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与赫伊津哈的衰落命题相关,把晚期中世纪欧洲视为由饥荒、黑死病、教廷分裂、农民起义、百年战争与宗教迫害主导的危机时代的传统观点(可参考巴巴拉·W.塔奇曼著、邵文实译,《远方之镜:动荡不安的14世纪》,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也在近年来遭到了若干系统批判[如Peter Schuster, “Die Krise des sp?tmittelalters. Zur Evidenz eines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lichen Paradigmas in der Geschichtsschreibung des 20 Jahrhunderts,”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69 (1999), 19-55; Howard Kaminsky, “From Lateness to Waning to Crisis: The Burden of the Later Middle Ages,” 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 4 (2000), 85-125]。封建领主制度危机的旧命题[如Guy Bois, The Crisis of Feudalism: Economy and Society in Eastern Normandy (c. 1300-15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变成了社会经济转型的新命题(如克里斯托弗·戴尔著、莫玉梅译,《转型的时代:中世纪晚期英国的经济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战争与动乱在国家建构(Richard Kaeuper, War, Justice, and Public Order England and France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8)与新政治理念的创生(John Watts, The Making of Polities: Europe, 1300-15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方面具有积极意义;针对黑死病的医学创新及其取得的实际成效,被认为在欧洲社会为后来的文艺复兴奠定了积极、自信的思想氛围(Samuel Cohn, The Black Death Transformed: Disease and Culture in Early Renaissance Europe, London: Arnold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被伊丽莎
白·爱森斯坦过分夸大的15世纪末的“印刷革命”(《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实为在晚期中世纪取得重大发展的抄本文化的延续(Daniel Hobbins, Authorship and Publicity Before Print: Jean Gers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te Medieval Learning,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yslvania Press, 2009);教廷分裂时期(1378—1417年)与宗教改革之间的百余年被阐释为一个多元、自主的宗教实践百花齐放的基督教开放时代[John Van Engen, “Multiple Options: The World of the Fifteenth-Century Church,” Church History, 77 (2008), 257-84]。
近年来学术界对晚期中世纪的“去衰落化”与“去危机化”,在两个不同的面向上可以与勒高夫的“长中世纪说”构成对话。一方面,它进一步弱化了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断裂与对立。另一方面,它也提示我们,在强调长时段历史连续性的同时,也需要给予“长15世纪”这个晚期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重叠时段以专门的关注:并非因为期间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断裂,而是这个时段自身或许具有某些区别于之前的盛期中世纪与之后的早期现代的独特历史气质。
勒高夫的“长中世纪说”显然与法国年鉴学派的学术传统密切相关。勒高夫的老领导布罗代尔对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著名研究的时段选择,是从晚期中世纪至工业革命(参见《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与施康强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与勒高夫同为“年鉴”第三代掌门人的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从人口学的角度,把夹在盛期中世纪的第一次农业革命与19世纪的第二次农业革命之间的1300—1720年间,界定为欧洲的一段“停滞的历史”(l’histoire immobile,参见他1973年接替布罗代尔就职法兰西公学院的演说,收录于《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杨豫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这一富有争议性的论断也同样打破了“中世纪—现代”的传统分期。勒高夫从盛期中世纪史学者的视角出发,把这个法国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分期传统再向前延伸,以至囊括了整个古典时代之后的“中间时段”。
“长中世纪说”的分期方式也映射了勒高夫的中世纪观的一些特点。勒高夫的作品常常会给读者带来这样的感受:中世纪离我们现在的世界似乎既很近又很远。他生平最富学术原创性的两大论断刚好反映了这种张力。一是“时间”的发现。勒高夫认为,中世纪欧洲的最大发明是一种在经济和思想的双重意义上支配和管理时间的意识,而这种意识构成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石。二是“民间文化”。在他看来,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主流并非以规整的拉丁语著作和高深的神学思想为代表的高级“教士文化”,而是一种诉诸口头流传、缺乏严格的教义和仪程规范、充满怪力乱神的流行文化。如果说,前一个命题突出了中世纪的某种现代属性,后一个命题则更多地呈现了中世纪迥异于现代文明的非理性、甚至愚昧黑暗的“他者”一面。这种两面性在“长中世纪”的概念中则表现为,它既与19世纪之后的现代一分为二,又内在地蕴含了向现代过渡的“历史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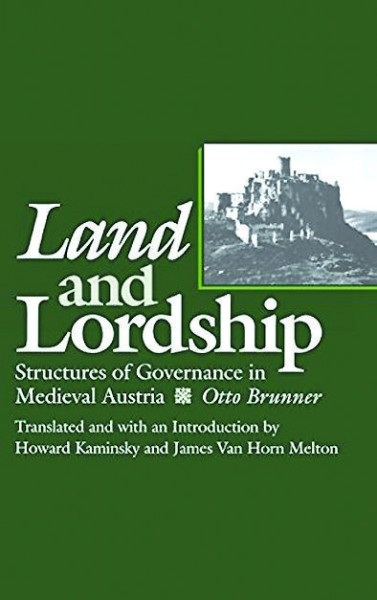
▲奥托·布鲁纳及其著作《领地与领主统治》
英、德学界的“早期现代”与“旧欧洲”概念
那么,对于这个长达1300年的“长中世纪”内部的变迁节奏,我们又该如何把握呢?勒高夫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没有在《分期》中出现,却可以在他之前的一篇名为“长中世纪”的访谈文章中找到(收录于Un Long Moyen ?ge, Paris: Tallandier, 2004)。勒高夫认为,推动中世纪历史进程的主要是三场“复兴”运动:9世纪时重新奠定拉丁书写文化并保留了图像在宗教生活中的合法地位的“加洛林文艺复兴”;以对亚里士多德的重新发现、大学的出现和世俗骑士文学为标志的“12世纪文艺复兴”;15—16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这三次以“自我更新”为主题的思想与社会浪潮构成了这个长时段中的历史演进动力。
用新的长时段打破旧的古史分期的思潮也并非法国学术所独有。在这里,我们可以简略提及在当代英语与德语学界备受瞩目的两个史学概念。其一是“早期现代”(Early Modernity/ Frühneuzeit),大致以15世纪到18世纪末为时限。“早期现代”概念伴随着20世纪60—70年代的现代化思潮兴起,在20世纪80—90年代的英、德学界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早期现代”强调从将近四个世纪的长时段内的历史演化来理解现代西方的发生史,并且看重欧洲不同区域内历史变迁节奏之间的差异与可比性。著名的“剑桥早期现代史研究”丛书(Cambridge Studies in Early Modern History)这样把早期现代史的核心主题界定为“延续与变迁之间的互动,既表现为对中世纪思想、政治与社会组织的接续,也表现为新思想、新方法和对于传统结构的新需要”。法国年鉴学派,特别是布罗代尔的研究,对作为独立学科的“早期现代”的兴起影响重大,尽管这个概念本身极少被当代法国学者接受和使用(包括勒高夫)。如今,“早期现代”与“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一同构成了英美欧洲史学界最热门的两大领域。
第二个概念是“旧欧洲”(Old Europe/Alteuropa),大致以1000—1800年为分期。这个概念的源头可以追述到上文提到的布克哈特甚至更早的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奥地利史家奥托·布鲁纳(Otto Brunner)是首位在20世纪的史学研究中发挥“旧欧洲”概念的学者。布鲁纳的“旧欧洲”的核心特征是以自治性的小共同体为基础的领主土地制度和建立于其上的统治与法权关系,区别于在1800年之后确立的以国家政治权力的支配地位为特征的现代欧洲。因为涉身纳粹,布鲁纳的学术在“二战”后一度遭冷遇。但伴随着布鲁纳的学术复出,以及犹太裔德国学者迪特里希·格哈德对“旧欧洲”的提倡,这个概念在20世纪后半叶再度焕发活力。尽管格哈德尽量回避提及这个概念与布鲁纳的渊源,他以传统性、区域性与法团性对“旧欧洲”的界定,显然受到那位前纳粹的影响(Dietrich Gerhard, Old Europe: a Study of Continuity, 1000-1800,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布鲁纳的名著《领地与领主统治》的英译本在1992年的问世(Land and Lordship: Structures of Governance in Medieval Austria, trans. by Howard Kaminsky and James Van Horn Melt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以及该书主译、美国中世纪史家霍华德·凯明斯基对“旧欧洲说”的提倡,大大提升了这个概念在英美学界的影响。凯明斯基认为,布鲁纳对德语地区的历史判断也适用于法国与英国;此外,他更强调“旧欧洲”的贵族统治属性,区别于布尔乔亚主导的现代欧洲[参看Howard Kaminsky, “The Noble Feu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Past and Present, 177 (2002), 55-83; “Citizenship vs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Bonum Commune vs Private Property: A Modern Contradiction and its Medieval Root,” The Medieval History Journal, 6 (2003), 111-137]。
对比“早期近代”、“旧欧洲”与“长中世纪”,既能看出在不同的学术传统中发育出的史学框架的不同侧重,也可以看到勒高夫之道不孤。可以说,勒高夫在《分期》一书中的个人思考,反映了当代西方史学的一项普遍努力,即通过新的历史分期尝试为探索西方文明的前世今生提供新学术引擎。对于在书的标题中为自己提出的问题,勒高夫最终的回答是肯定的。勒高夫对传统的“中世纪—文艺复兴”分期法的批判没有使他抛弃历史分期工作本身,而是促使他思考更有效的历史分期可能。正如他所言,“历史学家必须掌握时间……因为时间是变化的,历史分期对历史学家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分期》,第131页)。诚然,历史分期不能替代基于史料的实证研究与细致的史学分析,正如“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历史分期终究是一种有用的史学武器,是帮助史家收束读史心得的储物盒,是便利与同行交流切磋的平台,是与社会科学互通有无的管道,也是进行跨区域比较史学研究的脚手架。这或许是《分期》一书可以给古史分期问题逐渐成为史学化石的中国学界带来的一点启发。
杨嘉彦先生的翻译清楚晓畅,很好地呈现了《分期》原文轻快而明晰的语言风格。不过,在几处涉及中世纪专门知识的地方,译文似有不妥,在这里分别列出,供读者参考:
第8页:“按照佛拉金的雅克所说,这个时间由两个原则,即礼拜仪式日(sanctoral)和世俗生活(temporel)所定义。”
此处的sanctoral与temporal(中译本中标出的temporel在法文原版中当为temporal)指的是中古基督教年历中同时使用的两套礼仪周期,分别是按照圣徒纪念日安排礼仪的“圣人循环”与按照基督的生平与复活安排礼仪的“基督在世时序循环”。
第18页:“一种‘共同体’(commune)制度在以君主制为主导的欧洲出现……”
commune一般译作“城市公社”。
第24页:“让·马比荣……著有《论外交事务》(De re diplomatica)……”
De re diplomatica当为《论文献学》。
第28页:“我们可以通过‘生活的重要历史’(historia magistra vitae)来概括这一时期历史教学的核心目标……”
historia magistra vitae当为“历史乃生活的导师”,语出西塞罗。
第100页:“在这种连续性中,应该注意一种有着美好未来的新事物:酒精。它的出现算是晚的,正如布罗代尔指出,如果16世纪‘可以说创造了它’,18世纪的时候它才普及。”
此处译作“酒精”的法文alcool,更恰当的译法是烈酒。低浓度的葡萄酒和啤酒在很早时候就是欧洲普及的饮料。
第128页:“从13世纪开始,大学就制造了相当多的手抄本(pecia)……”
pecia这里指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手抄本。该拉丁词的原意指一刀牛皮纸,相当于英文中的quire。这里特指中世纪大学的书店向学生提供的拆分成多个部分的课程讲义样本。拆分的目的是使样本可以在需要借去誊抄(或雇人誊抄)的学生中间更快地流转。
瑕不掩瑜。我相信,这本可靠的中译本会在未来很长的时间内列身国内世界史研究的必读书目。它也将吸引更多的读者产生探索中世纪史的兴趣。而这,正是勒高夫一生所求。
文 : 刘寅(作者为美国圣母大学博士)
编辑制作 : 范菁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