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5日19时,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正式揭晓。挪威剧作家Jon Fosse(约恩·福瑟)摘得殊荣。其获奖理由是:“创新的戏剧和散文,为不可言说的事情发声。”得知自己获奖,约恩·福瑟表示:“我认为这是对文学的奖励,首先是文学,而不是其他考虑。”
约恩·福瑟是挪威当代著名作家、诗人和戏剧家,也是北欧地区最重要的在世作家之一,更是当代欧美剧坛负有盛名,作品被搬演次数最多的在世剧作家。他的作品至今已被翻译成五十多种文字,超过千场制作公演,获得了北欧地区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奖,入围了国际布克奖和美国全国图书奖翻译奖的短名单。本报作者崔莹曾经亲自采访过约恩·福瑟,这篇访谈被收入崔莹新书《访书记》中。这是一部关于书与国际写作者的访谈录。访谈的内容涵盖汉学、历史、文学、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透过访谈,读者可以更加走近这些赫赫有名的佼佼者,了解不同领域的动态,深入探究各个领军人物的思想。经崔莹本人授权,本报特刊载她对约恩·福瑟的访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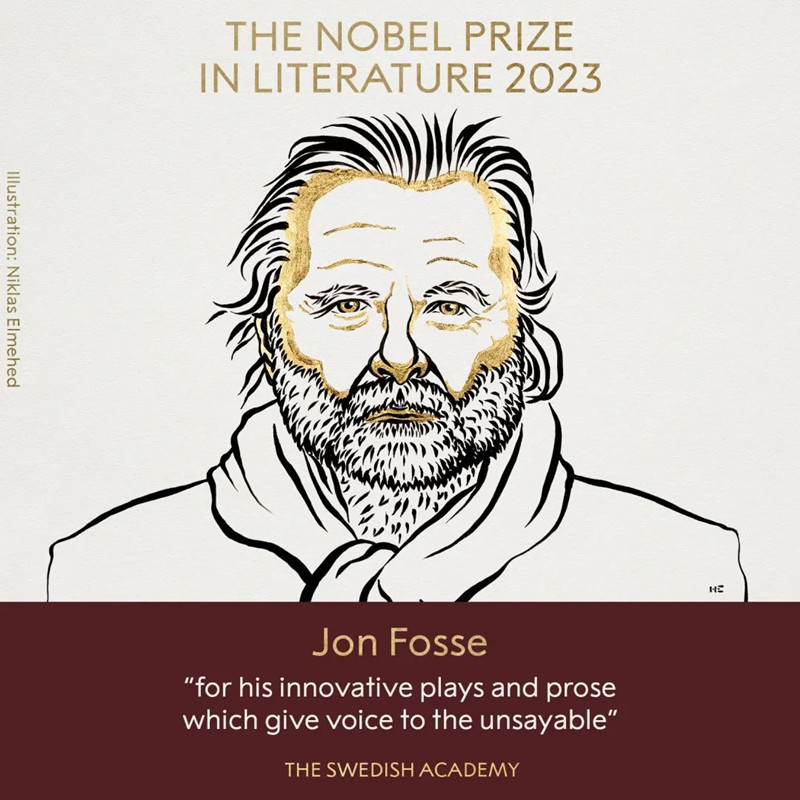
>>内文选读:
故意反抗贝克特的福瑟
当代欧美戏剧家中,谁的作品被搬演的次数最多?答案是:约恩·福瑟。
这位挪威剧作家的作品已被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制作成九百多部舞台剧,在世界各地上演。因为在戏剧领域的杰出成就,他得过包括易卜生国际戏剧奖、斯堪的纳维亚作家奖在内的诸多奖项。《纽约时报》评价,他的作品“充满激烈的、诗意的简洁”。易卜生国际戏剧奖给他的授奖词称:“福瑟迫使剧场和它的观众们以全新的方式思考。他是未知的诗人。”
1959年9月29日,福瑟出生在挪威一个叫豪格松德的小镇。这里毗邻大西洋东海岸的卑尔根市。福瑟从小喜欢音乐,经常自己编曲,也写诗歌和小说。他的首部小说《红与黑》于1983年发表。1996年首演的《有人将至》,则是他的戏剧处女作。此后,他就以戏剧创作闻名。他的剧本,都用新挪威语创作。(注:在挪威,有两种官方书面语,即“书面挪威语”与“新挪威语”。有10%-15%的挪威人使用新挪威语。)
孤独、爱和死亡,是福瑟一直探讨的主题:在《一个夏日》中,男主人公毫无预兆地选择了投身大海,他的妻子自此日复一日地眺望大海,与记忆搏斗。在《死亡变奏曲》中,大海吞噬了一个年轻的姑娘,她早已分手的父母被迫重新面对彼此,寻找她的死因……他笔下的人物,都处于某种生存困境。他们都是孤独的。
福瑟常被誉为“新易卜生”,外界也将他与贝克特、品特比较,但这些对比多少忽视了福瑟的特质——他的戏剧世界自成一体。在这个世界里,主人公经常没有具体的名字,只是“一个女人”“一个男人”“他”;时间分界模糊,过去、现在与将来杂糅;语句经常重复,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韵律感;静场和主人公话语的戛然而止频繁出现,令观众“于无声处听惊雷”。
福瑟与东方有缘。他曾说,东方人仿佛能比西方人更好地理解自己的作品。他的戏剧选集《有人将至》和《秋之梦》已经在中国出版。他曾来到中国,观看上海戏剧学院演出自己的名作《有人将至》。他认为,这个版本是对自己作品最好的舞台呈现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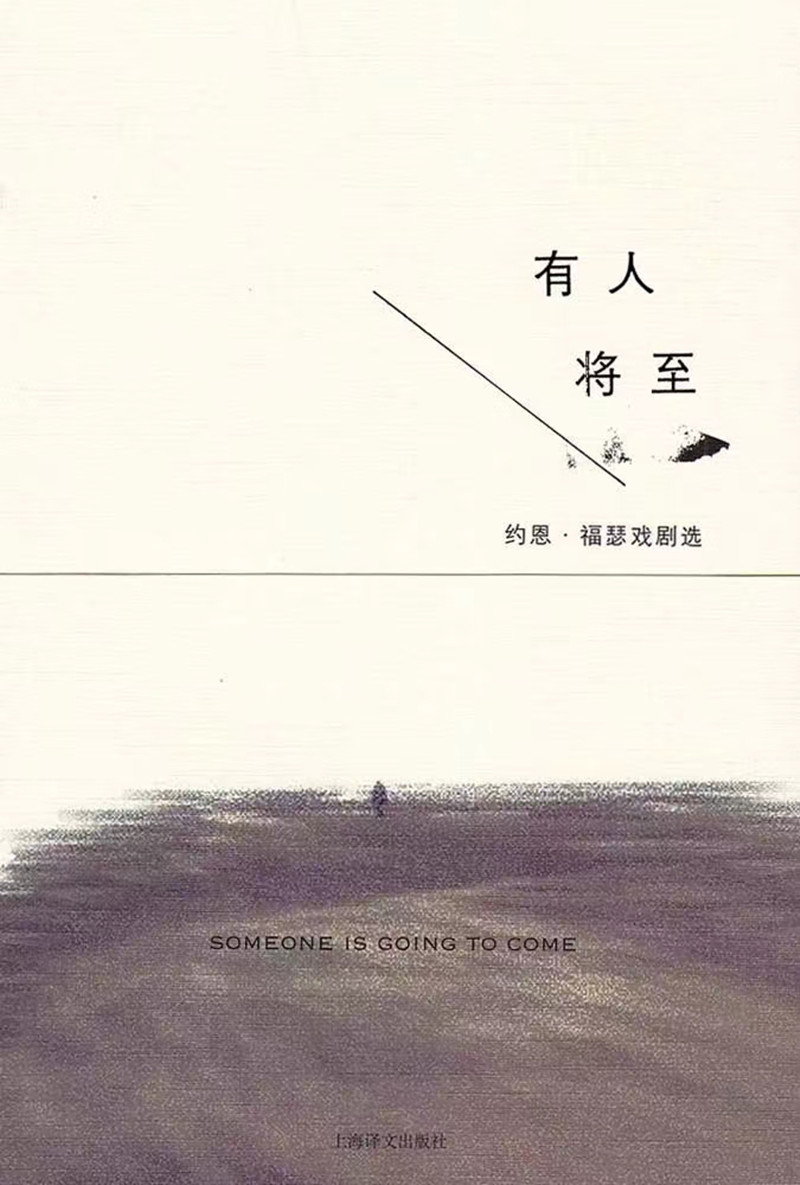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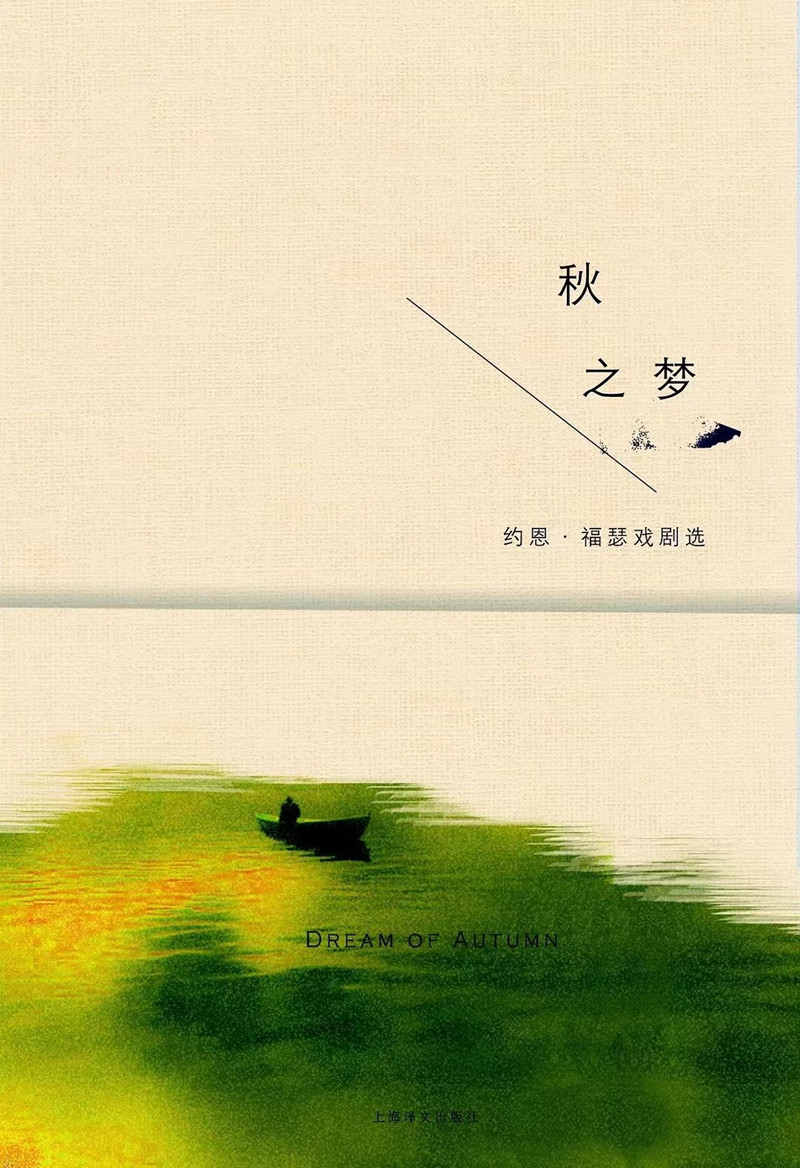
1. 写剧本就像在编曲
崔莹:“大海”在你的作品中分量很重,往往奠定了全文基调。它有时给人安全感,更多时候却令人恐惧。为何这样描写海洋?你的主人公经常长久地凝视大海,你也会这样做吗?
福瑟:是的。我在挪威卑尔根附近的小镇豪格松德长大,在那里总能看到海和海浪。这对我影响很深。坐下来集中精力写作时,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出自己第一次看到海、看到船的情景。
现在,我有时也去卑尔根附近的一所房子写作。它离海很近,从那里二楼的书房眺望,可以看到海、海浪和峡湾对面的陆地。我经常会在那里凝视大海。我在挪威北部山区,我还有一座小木屋。那里更开阔,可以看到更大的一片海。
我父亲喜欢船。他有一条船。后来,我也有了船。我现在用的是一条邻居造的小木船,天气好的时候,我会沿海岸线驾驶它。在广阔的海面上,你会感觉到自由。但同时,这种自由是有限的——所有的时间里,你都必须呆在船上。你会热爱大海,会喜欢海浪的节奏、海水变化的颜色,但同时你也会发现大海的危险:它变化无常,发怒时会很残酷,很多人葬身其中。我想,大海是世界上最大的墓地,仿佛意味着死亡。
可以说,大海是个矛盾体。我的作品也是个矛盾体。而这是因为,人生本身就充满了矛盾。
崔莹:你反复书写人的孤独感:“我将只有独自一人。”这与你的成长经历有关吗?
福瑟: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我的孤独感要追溯到我的婴儿时期——它在我一两岁时就出现了。从小到大,虽然有很多亲密的朋友,但我一直性格内向,有些害羞。我感到我和他人、和整个世界的距离都很远。正是为了减少这个距离,我开始写作。
崔莹:你最早写的是短诗和歌词。当时的你是怎样开始创作的?这段经历对你的戏剧创作有什么影响?
福瑟:12岁时,我很喜欢弹吉他,就开始编一些小曲子,也为它们写歌词——我至今依然记得其中的几首。16岁时,我参加了一个乐团,弹摇滚吉他,也拉小提琴。但我最终意识到自己没多少表演天赋,就放弃了演出,继续编曲。
可以说,我的写作就是从与音乐有关的创作开始的——音乐需要聆听,写作也需要。有时我感觉自己只是在听我的人物说话,然后把它们记录下来。
我的作品“语句重复”的特点,也是从那时开始的。写剧本时,我就像在编曲,戏剧就仿佛是我的乐谱。
崔莹:你曾如此热爱音乐,那你最喜欢的音乐家是谁?
福瑟: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没有音乐家能和他相提并论。
崔莹:写作之初,哪位作家对你的影响比较大?
福瑟:最初开始写作时,挪威作家罗尔夫·雅各布森对我的影响很大。当时我的作品仿佛都不是用自己的语言写成的,而是用他的语言写成的。直到二十多岁时,我才逐渐形成自己的语言。我正儿八经在报纸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叫《他》。我后来的作品风格,和那篇故事的差不多。写的是生活的本质,与人物的名字无关。
崔莹:一开始,你发表的是小说。十多年后,你的剧作《有人将至》才真正问世。你是如何从小说转向戏剧创作的?
福瑟:说实话,我的第一部戏完全是别人掏钱聘我写的:有人问我想不想写戏,那时我是自由作者,收入不高,非常需要钱,就接受了。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会写戏剧。
用了一周时间,我写了《有人将至》。在我的作品中,它至今仍是被搬上舞台次数最多的一部。
我并不喜欢剧院,甚至有点讨厌它,但我喜欢写戏剧的感受——不仅可以决定如何使用语言,也可以决定在何时沉默。沉默是语言之间的间隔。
崔莹:说到这一点,你的戏剧的一大特点,就是静场的频繁出现。在你看来,沉默在戏剧中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你如何判断哪里该沉默?
福瑟:沉默和孤独有关。这种孤独并非是一种坏事,而是一种平和。沉默也和虚无有关,而沉默和虚无都是我作品的血肉。我认为这些停顿或者沉默,比那些说出来的话要有分量得多。这种沉默也会令观众感受到氛围的紧张、故事的戏剧化。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很容易意识到哪些地方需要短暂的停顿,哪些地方需要长久的沉默。
崔莹:家庭关系是你关注的另一主题。在这方面,你本人的经历是否影响了你的创作?(注:福瑟离过两次婚。)
福瑟:在我的作品中,所有情节都与人物之间的关系,或与他们因为缺少某种关系而导致的虚无感和空虚感有关。其实在人生中也是这样。我自己关于各种关系的感受,影响着我的作品。
不过,所有的好作品都要包含人生,也要和它保持一段距离。
崔莹:在你的剧本中,人物多为无名氏,人物名往往只是“一个人”“另一个人”“他”“她”。为什么这样设计?
福瑟:一开始写作时,我就没给主人公起正式的名字,只用“他”或“一个男人”来指代。然后我就习惯了这样做。我或者不用具体的名字,或者一遍遍地用同样的名字指代不同角色。
名字本身会透露太多信息,产生太多干扰——一个女孩的名字可能暗示了她属于某个社会阶层,来自哪个国家。这不是我想要的。我写的是生活的本质,和人物的名字无关。

2. 故意反叛贝克特,未受易卜生影响
崔莹:在你的早期作品中,有的是以时间顺序来安排的,比如《有人将至》就分开始、中场和结束。但在你的后期作品中,过去和现在混合、渗透在一起。这在《秋之梦》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你在后期为何这样处理?
福瑟:我将过去和现在的混合与渗透称为“片刻”。比如我的戏剧《睡觉》,就是发生在某一片刻的故事。片刻和永恒是联系在一起的,它描述的是一种状态。它看似不存在,但实际上又存在。
在作品中,假如将某个片刻独立出来并加以扩展,我想,这部戏就不再像是一曲音乐,而像是一幅画了。
崔莹:请谈谈影响你的戏剧和剧作家。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对《有人将至》的创作有怎样的启发?
福瑟:年轻时,贝克特的作品非常吸引我,我也很崇拜他。他给了我很多启发,但在某种程度上,我故意反叛贝克特——我故意写得和他不一样。所以我的《有人将至》实际上和《等待戈多》是相对的。在《等待戈多》中,他们等啊等,没有人来;但在我的戏中,他们不用再等了——有人来了。
当然,我的性格和贝克特的不同,我们的作品风格也不相同。我并不认为我的作品受贝克特的影响。
崔莹:那易卜生呢?
福瑟:易卜生从未对我有多大的吸引力。我反而对那些挑战易卜生戏剧的作品很感兴趣,比如贝克特的——它们和易卜生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截然相反。
易卜生与莎士比亚、契诃夫一起被誉为世界三大剧作家,但我从未觉得和他很亲近,也从未觉得他影响过我的写作。我和易卜生的区别很大。
崔莹:据你观察,在你创作戏剧的这些年里,欧洲的戏剧创作有什么明显的变化趋势?剧作家的生存状况如何?
福瑟:在欧洲,戏剧最繁荣的国家是德国,这种繁荣也扩展到意大利、法国和挪威等地。我觉得欧洲各国的戏剧发展状况都差不多。一开始,欧洲的剧院非常热衷于将原创的新剧本搬上舞台。但是后来,越来越多的剧院导演开始决定戏剧的内容。他们倾向于将小说改编成剧本,纯粹的原创剧本不再受重视。我并不喜欢这样——大多数剧院导演并非天才,排的大多数作品不值一看。
在欧洲,当剧作家的收入并不丰厚。和排新戏相比,导演更爱将经典戏剧再次搬上舞台,观众对新戏的兴趣也不大,所以被搬上舞台的新戏很少。这是我自己的感受。

《有人将至》中国版剧照
3. “希望中国读者看到我的更多戏剧”
崔莹:《有人将至》曾被上海戏剧学院搬上了中国舞台。你也来中国看了这场演出,感受如何?
福瑟:印象非常深刻!我看过很多场根据《有人将至》编排的舞台剧,中国的这场如果不是最好的,也是最好的之一。在演员的表演、场景的布置和装饰及声音的处理等方面,它都很好。比如舞台上的流水声并非是提前录的,而是工作人员现场制作的。我认为,这场演出非常准确地理解和再现了我作品中的音乐和情绪。
演绎我的戏剧,不光靠对话,还要靠很多沉默的时刻,以及人物的肢体语言和表情,比如手势的一个小小的变化。这场演出对此也把握到位。这些都是我喜欢的。
崔莹:你说,东方人仿佛能比西方人更好地理解你的作品。这是为什么?
福瑟:我也无法解释,上帝才知道。我的戏剧在法国也很受欢迎,但我发现,最能演绎好我的作品的,是东方的演员;最能理解我的作品的,是东方的观众。
我的中译者邹鲁路是当代欧美戏剧研究学者,她正在探寻我的写作方式与亚洲人心理之间的关系。最近她告诉我,上海戏剧学院打算在中国出版我的另外两部作品,对此我很开心。希望中国读者看到我的更多戏剧。
崔莹:你在2014年表示不打算继续写戏剧了。那你最近在创作什么?
福瑟:我已经写了三十多部戏,包括二十多部长戏和十多部短戏,我觉得写够了。戏剧需要一定的舞台性和紧张情绪,但这种紧张情绪太多了,我感到疲惫。我现在需要安宁。
我最近一直在写小说、诗歌和散文,这也是我最初的爱好。去年,我的小说三部曲《不眠之夜》《奥拉夫的梦想》和《倦怠》赢得了北欧理事会文学奖,这是北欧最高文学奖。
我一直想写“慢散文” (slow prose)。现在我就在挑战自己,写一个这样的长篇。我已经写了1500页。它将分三卷、七部分,在2019年、2021年和2023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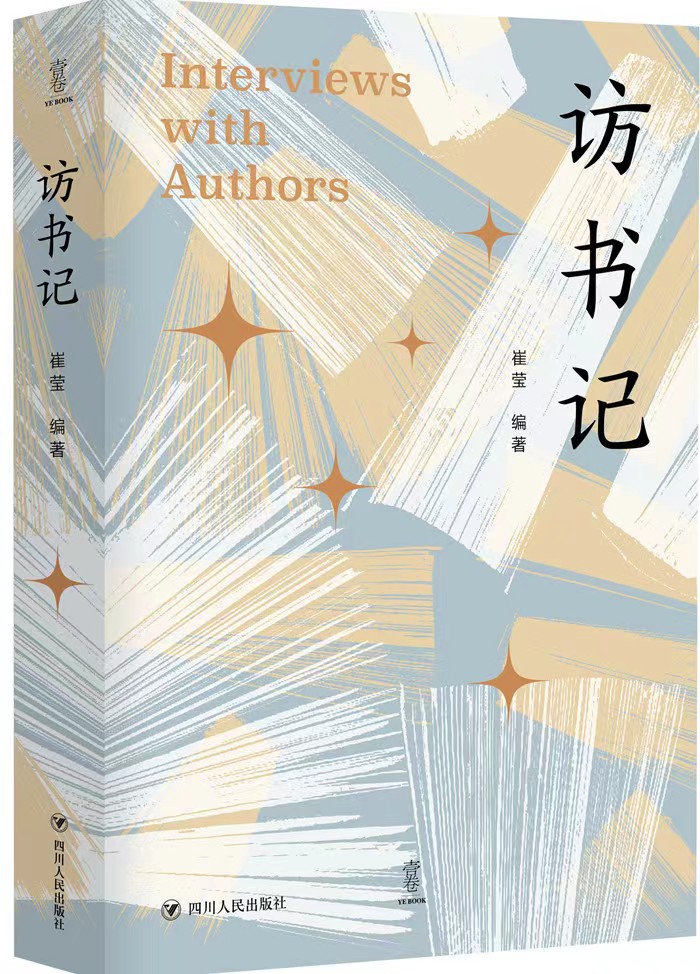
作者:崔 莹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