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因城市的存在,拥抱了数之难尽的美好;城市,也在持续不休的营建和修饰中“容光焕发”,刷新着人们对“美好城市”的想象边际。2015年,城市规划界泰斗约翰·弗里德曼提出,要建成并持续享有“更公平、更宜居的城市世界”,务须自生态、经济、公正、道德、文化等方面着手,在地化且长远化地更新各子系统。概言之,就是需要结合内外“变数”,在不断自我磨砺中,缔造出“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美好城市”。
回观近代世界城市史,剧变期始终是城市酝酿重大变化、争取明显突破的关键节点。百年前,在时局汹涌湍急的20世纪大变局里,向着近代文明挺进的中国都市,因循深厚传统,倾注世界情怀,一步步迈向极具民族与时代标识度的“美好城市”理想。这是中国式城市治理的一脉源流,亦属世界城市发展长河的一股新流。在此,且借四篇时人写作的“美好城市”思索为引,回访四部北京、上海近代城市史著述,细观百年前中国大都会的“美好城市”寻路。
百货公司里的“大上海”城市魔力
之于近代中国,首重的“美好城市”期许,注定是物质发达、经济繁荣。这是反复经历“落后挨打”的贫弱农业国的“痛定思痛”。1921年,《新闻报》某撰稿人惊喜地发现:“近年来,上海一埠日趋繁庶。工商百业,无不日见发达。遂至上海本埠无复余地可容,不得不推及于四境滨水之区。于是乎,大上海之景象,乃渐涌现于外。”该主笔以江湾为例,称陆续建成的电厂水厂、硬化道路等城市基础设施,是“十年以前所想不到者”。昌盛的工商经济,塑造了繁华的城市。合宜的城市基础服务,标记并彰显了经济发展的成就水准,承载了时人对现代化生活的美好憧憬。
漫步近代上海街头,人们总会与源自、象征、促进经济繁荣的城市单元不期而遇。这当中,集天南地北名货,汇东土西风奇物的百货商店,无疑是最让人眼花缭乱的“大观园”,也是最能展示上海引领风尚一面的“大橱窗”。《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捕捉了此间发生的一些旧事。

《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
连玲玲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作者认为,百货公司诞生于城市空间营建,也通过建筑文化演绎、日常消费实践,化为城市生长的一处极峰、标志,“‘四大公司’的兴起为南京路注入了新的活力……百货公司更像是突出于一片低矮店铺的庞然大物”。这既“塑造了南京路”,也缔造了上海这座大型城市极为耀眼的“现代消费地景”。
整体辉煌之下,近代上海百货公司与城市文明的互相哺育,还生动地表现在百货公司对外宣传、内部设计的种种巧思。《打造消费天堂》指出,近代上海人头攒动的商业街里,“霓虹灯不但是一种广告形式,也成为文人笔下夜上海的象征”,而市民消费欲望膨胀,竟然间接推动了城市广播的崛起。作者梳理1927年新新百货公司运营中国首家民营电台——新新电台的历史,发现此般新业态与新技术在上海的相遇,向这座东方大都市“放送了娱乐至上的消费主义信条”,极大地促进了市民消费实践的近代化、丰富化。
披览《打造消费城市》,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些年间,上海百货公司内部装潢随时演替——从安装扶手电梯到增添冷暖气管,一切细节均在于殷勤地服务、热切地招徕顾客。作者敏锐地观察到,新颖设施的加入,使百货公司“提供的不只是商品,也是现代性的体验”,这是全然不同于农业社会贸易经验的、浸润体验重于商品流通的城市文化和市民红利。窥一店而知繁荣,进一门则感现代,这便是充盈在百货公司里的“大上海”城市魔力。
开放之城让上海领跑时代
述及上海的繁荣,最直接的来源和最绵长的影响,要属全面、强烈、深刻的开放性。开放,让上海领跑时代,也让上海值得生活。1923年,《艺术评论》杂志由衷赞扬了上海的文艺“国际范”:“有名的意大利歌剧、莫遮德(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音乐、俄罗斯的舞剧,哪一样不是在上海先看见,先听见呢!”在上海,享天下,开放之城,常见与共之美。
《世界之城:上海国际大都市史》呈现了百年前开放上海中几处常见却又非凡的“荟萃之景”。

《世界之城:上海国际大都市史》
王 敏 著
格致出版社出版
在作者笔下,上海的豁达开放,首先表现为广泛接引时代前沿,把世界的美好注入上海城厢。上海或许是近代中国电影覆盖面最广的一座城市。作者考证,早在1930年代,“看电影已是上海现代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并且借由首轮、二轮、三轮、露天等多层级影院的接力传播、渗透,电影悄然步入了从富贵绅商到普通职工的上海市民的日常文化生活。
上海不只接纳世界,她还向全球来客传达着东方之美、中国之声。在旧租界内“洋派”公园里,“本土化”的美好体验令中外市民齐声赞叹。1928年,外滩公园举办了一场赛龙舟活动,共吸引1.6万市民入园观战。1946年,早期“按照欧洲人审美习惯精心设计和建造”的兆丰公园,“从东南各省引进了200多种树木,移植到园内”。本土珍草与舶来嘉木共有一块沃土,此情此景,恰是上海开放特质的鲜活脚注。
最精彩的一点,是上海的开放性并未停留在“来与去”的单向度取送,而是毫不违和地让东西文明和谐同处,在传统与异域文化交响中,弹拨出国际都会的大气音符。作者在书中谈到,1912年,新新舞台五层楼顶建成了东西融合风格的“楼外楼游乐场”,那里的主要表演是中式传统的杂耍、滩簧、大鼓。与之相伴的,是当时颇显稀奇的现代电梯,以及荷兰进口的哈哈镜。东西文化,荟萃一堂。这正是上海的美好,这就是美好的上海。
文脉积淀撑起了近代北京的城市脊梁
物质丰裕是城市的“血肉”,但倘若脱离了精神高度的“筋骨”,城市势必会滑落至不堪目睹的混乱与肮脏。城市,是近代中国的文化教育高地,也是文明向前迈进的制高点。1935年,《教育辅导》杂志评议了那时城市远超乡村的文教基础:“城市识字的人多……在偏僻的乡村,没有学校,文盲触目皆是。”汇聚“通文墨者”的城市,保存、推进、弘扬了人类文化的诸多内容,培育、团结、发挥着文化阵线的主要力量。
《旧都新城:近代北京的社会变革与文化演进》以近代北京为样本,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刻阐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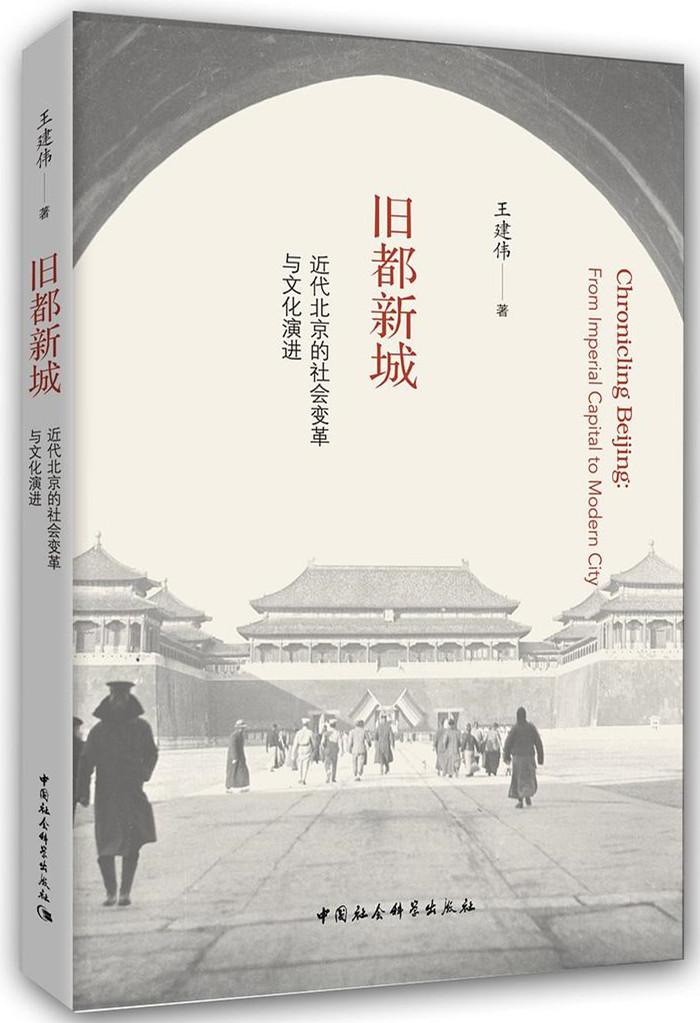
《旧都新城:近代北京的社会变革与文化演进》
王建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指出,1912年后,“北京作为教育中心的地位不断强化”。虽然1927年后因政治中心南迁,“北平对学生吸引力下降”,但其教育氛围并未消散。各在平高校,仍保持着旺盛的学术活力、重要社会影响力。作者从两方面着眼研究了大学对近代北京城市的意义:其一是“明里”的,“数量可观的大中学生群体,对于民国初年北京的城市消费,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意义是相对“暗中”的,“北京的学生群体,在思想意识以及知识结构方面,完成了最初的储备。学生势力崛起,成为引人关注的社会现象”,学生们敢于也善于“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成为城市文明,乃至发端于城市之近现代文明社会的突出的进步力量。
文化蓬勃,也是北平于风高浪急中行稳致远的一把船舵。《旧都新城》谈到,政治中心迁移后的“阵痛期”,北平走上了“文化复兴城市”的道路,将四九城内外俯拾皆是的遗珍,转化为“旧都新造”的一缕生机。1934年,北平市府设立三年发展目标,提出“将北平建成‘东方一最大之文化都市’”,为此还专门推出统称“旧都文物整理计划”的北平城游览区、沟渠、河道建设或整理计划。文脉积淀亦撑起了北平临危不乱的城市脊梁。作者观察到,在全面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北平深厚的人文积淀以及悠久的文化传统,对于日本因素的入侵,构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从而发生了一定的‘消解’作用”。一座座中国文脉“灯塔”,在暗黑的时代迷雾里,照亮了北平城的“破晓前路”。
“美好城市”需要“人文与自然双美”
1923年,成都《农业杂志》发表了题为“都市公园与文化生活之关系”的资政论说,开篇即言“蜀都古称天府,夙号锦城。既富自然风景,复不乏古迹名胜。窃以为都市修饰,乃现在市政上最重要之问题”。钢筋水泥筑就的城市,不应斩断其与自然的联系。同样,沉淀下来的历史风韵并不阻碍城市奔腾向前。美好的城市,需要自然哺育,呼唤人文陶冶。
《公园北京:文化生产与文学想象(1860—1937)》,便再现了近代北京城对人文之和、生态之美的愿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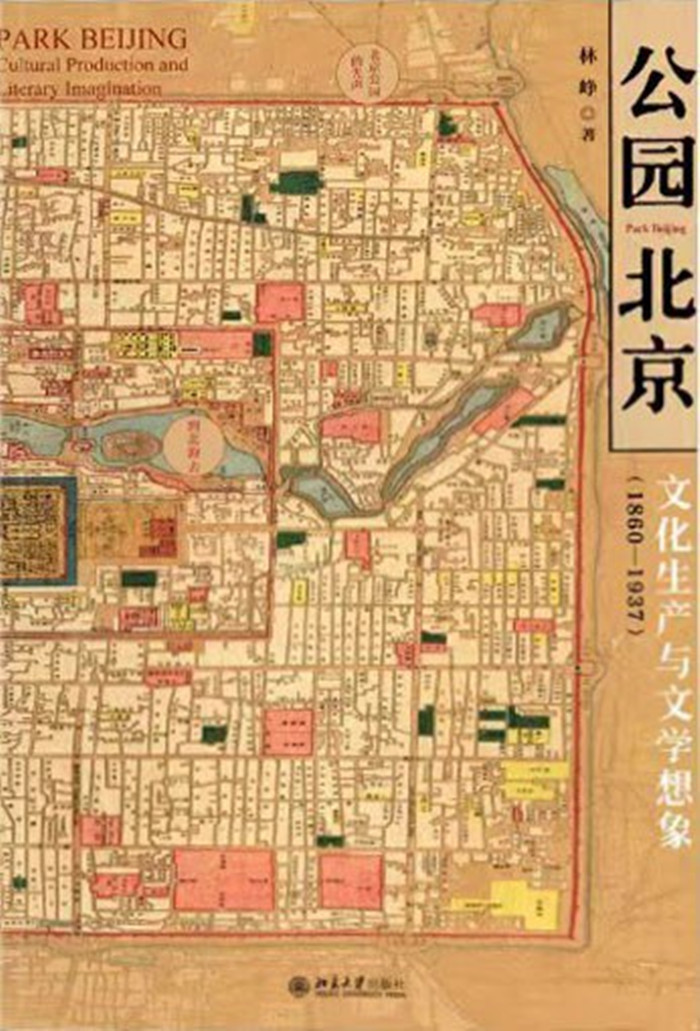
《公园北京:文化生产与文学想象(1860—1937)》
林 峥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公园北京》细致勾画了北海公园的人文与自然双美:“北海公园的一切设施皆出自美术的匠心,希望给予游人审美的享受。”围绕着这湾秀美湖水,北平三家著名图书馆次第坐落,如此“盛况即使是在民国时期图书馆与公园普遍共存的前提下,也十分罕见”。同样合围着北海的,还有各类公共体育设施,“青年男女飞驰冰面或泛舟湖心的身影,不啻北海最为动人的风景”。
老北京的公园,如何达致“人文与自然双美”的和美境界?上面呈现的是事实层面的“表”。在《公园北京》里,作者还交待了一层隐而不彰的“里”:“中央公园的茶座,提供了知识分子议政、论学、休憩、写作的空间。公园茶座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独特渊源,某种程度上承袭了中国士大夫的园林美学传统。”
看来,“美好城市”的所有奥秘最终落脚、最大依靠,都是城市里那一群群蓬勃向上的人。
作者:邹赜韬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