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的意义》是美国当代哲学家约翰·萨利斯的最新力作。他从哲学史和艺术史上有关“风景”的画作和著作入手,在深入探讨莫奈、塞尚、大卫·弗里德里希、保罗·克利等画家画作,以及康德、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哲学家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风景”和自然的独到理解,通过将风景构想为“元素性的自然”,提炼出风景画的三重含义:大地的、自然的和场所的。
本书的独到之处在于,作者借助现象学和解释学的方法,从哲学角度对中外历史上的风景画和山水画进行审视,将风景的本质概括为元素性和大地性,为美学和艺术史研究提供了另外一种独到的视角。尤其是,作者同样关注了中国古代画家李成、郭熙等的画作,尤其注重对中国山水画中不同于西方传统绘画的显隐运作方式的阐发,可以为读者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思考提供借鉴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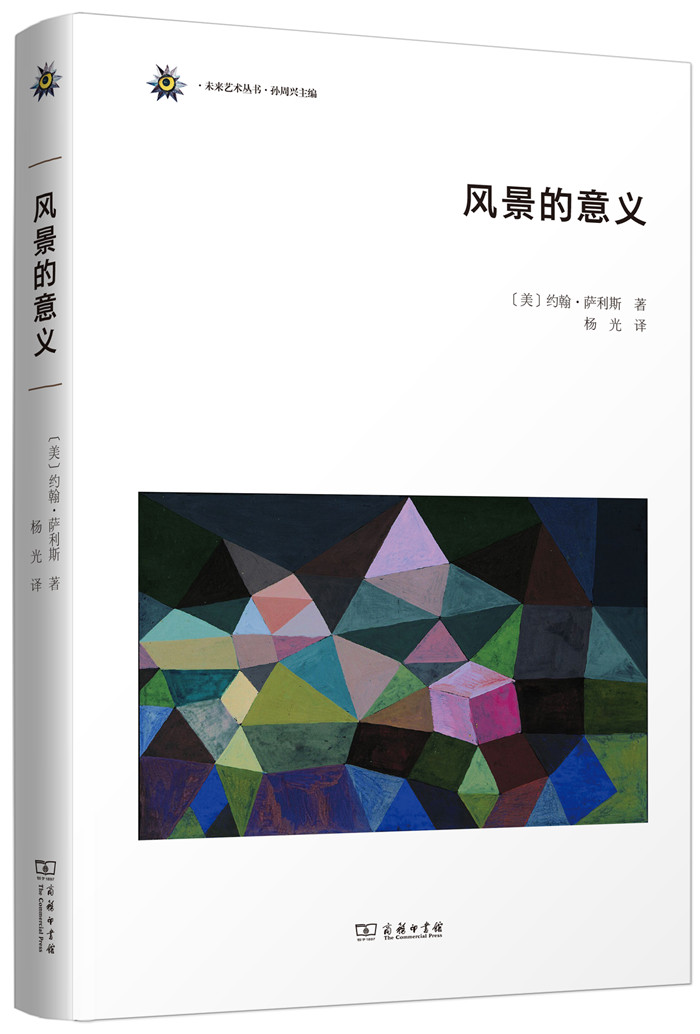
《风景的意义》
〔美〕约翰·萨利斯 著
杨 光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内文选读:
弗里德里希:让元素性的辽阔与浩瀚变得可见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也关注到洞穴,但它并不像圣维克多山中的那个真实的洞穴,并不能被认为是柏拉图洞穴的代表。相反,它完全是随艺术而诞生的场所。然而,就像塞尚的洞穴一样,它也被视为象征真理的地方,作为一种敞开,绘画在这里能够真正地照亮事物,这光亮来自远方,画家与观者都一定会注目凝视。弗里德里希的洞穴里所显明的是死亡的真相和那种基本的必然性,即人必有一死。然而,就像死亡之谜本身一样,弗里德里希的深褐色绘画《两个骷髅的洞穴》十分恐怖森然。两个骷髅躺在洞穴入口不远处,但很难说清楚观者一定就是朝洞穴里看,还是看向洞外。事实上,裸露岩层之外的地方看起来更明亮,在骷髅之上有一个圆盘,几乎可以看见,可能是穿过薄薄的云层或薄雾的月亮或太阳。除此之外,一些几乎透明的东西从岩石或从后面向下流淌到两个骷髅上:很像水从钟乳石流下来(然而,钟乳石通常只产生水滴而不是缓缓的溪流),或者可能是光线让骷髅在这个空间里清晰可见,而通常人们会认为这个空间是黑暗的。也就是说,光让死者重见光明。绘画呈现的不仅是死亡,死亡本身绝对不可能被呈现,也不仅仅是死亡的遗迹,而是死之谜、死亡的神秘。
同一系列里的另一幅绘画将这个谜设在风景之中,在《海边修道院与教堂墓园的废墟》这幅画中,一对年老的夫妇坐在挨着一棵死树的废墟前。废墟后面,陆地让位给大海,它一成不变,仿佛无尽延伸,与教堂墓地的粗糙与衰败形成对比。男人和女人都拿着铁铲;他们正在挖墓,毫无疑问,那是他们自己的墓穴。旁边有几座墓碑,废墟左侧下面还有更多。这幅场景中描述的一切都与死亡有关。然而,构成这幅图中心的这对夫妇仍然活着。在这一片废墟之外,在修道院、以树的形式展现的自然和墓碑石所标识的死者之外,大海在延伸,似乎无边无际,没有终点。
尽管这两幅画都呈现的是自然景色,它们呈现出的死亡之谜主要是关于人的,而不是自然;因为死亡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是必然的,所以是我们的本质性的根本特征,而我们注定要经历生死的轮回。尽管两幅作品描述像土地与海洋这样的自然元素,它们的意图并非是呈现这些元素本身;它们不是为了呈现自然元素的元素性特征,也不是元素对于人类的影响。从这个方面来看,它们不像弗里德里希的其他作品,尤其是他最有名的风景画,这些画中最突出表现的是自然元素。
有些风景如此具有自然元素的力量,以至于人们在它们面前只能静止站立,像被迷住看呆了。在这样的风景前徘徊,越过大地注视着远方的山脉,或者朝向无尽的海洋,一直延伸到海平面,人不是被想要了解土地、山脉或海洋的样子的欲望所牵引,也不是一定想知道或逐渐了解它们到底是什么或者什么构成了它们的本质。它们是什么,它们长什么样子,这都再熟悉不过了。然而,我们自愿地、满怀期待地、充满敬畏地好像着迷了一样站在这些自然元素前,或直接在自然中,或者是呈现在画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典型的态度不是仅仅迅速一瞥来抓住场景的外观,然后满足于这种外观或者将其抽离出来,并把它提升到好像本质性的地位。相反地,重要的是在自然面前徘徊逗留,以此来加强自然元素的经验;它是让这种经验反过来作用到我们属于自然元素的存在感。弗里德里希简洁地阐明了此种态度的关键:“我必须孤身一人,要意识到我的孤独是为了完全地感受和观察自然。我必须投身于我周围的事物中去,与我的云彩与岩石融为一体,这是为了成为真正的自己。”这种态度和由其而展开的经验那么就不仅仅是偶然的;相反,我们要想成为我们自己,即不仅属于自然,而且有这种强烈的归属感,有时就必须采取这种态度或立场,必须去经历这种经验。在弗里德里希的一些描绘自然景色的作品面前,它们所召唤的正是这种态度,持此态度的专心而敏锐的观者将会因作品本身的刺激而被吸引;在有些情况下,这一态度不仅是被召唤,它也会真实地展现在作品中。
弗里德里希的风景画是典型的具有展现自然元素的能力,其能使描述的场景的元素性得以显明。在这种方式呈现自然风景的过程中——确实这仅是一种手段而已——画家就改变了风景的通常显现出来的各个面向,因此其相互作用和影响也产生了变化。尤其是弗里德里为了加强元素性的一面以及与之相应的场所的因素,将自然物的面向弱化了。他严肃批评了他的一些同代人,例如约瑟夫·安顿·科赫,因其画了太多事物将画面显得局促拥挤,“他们将物体堆积在彼此的旁边、后面和上面,使得画面不堪重负,我想是为了呈现画面的丰满……那些在自然中彼此间被巨大空间隔开的事物都被聚集到一起,互相接触,充满了观者的视线,给他们留下了不是很愉悦的、躁动的印象。相比之下,弗里德里希更习惯于画风节制:他清除了画面上的物体,让画面变空,由此打开空间,以便让元素性的辽阔与浩瀚变得可见。
作者:〔美〕约翰·萨利斯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