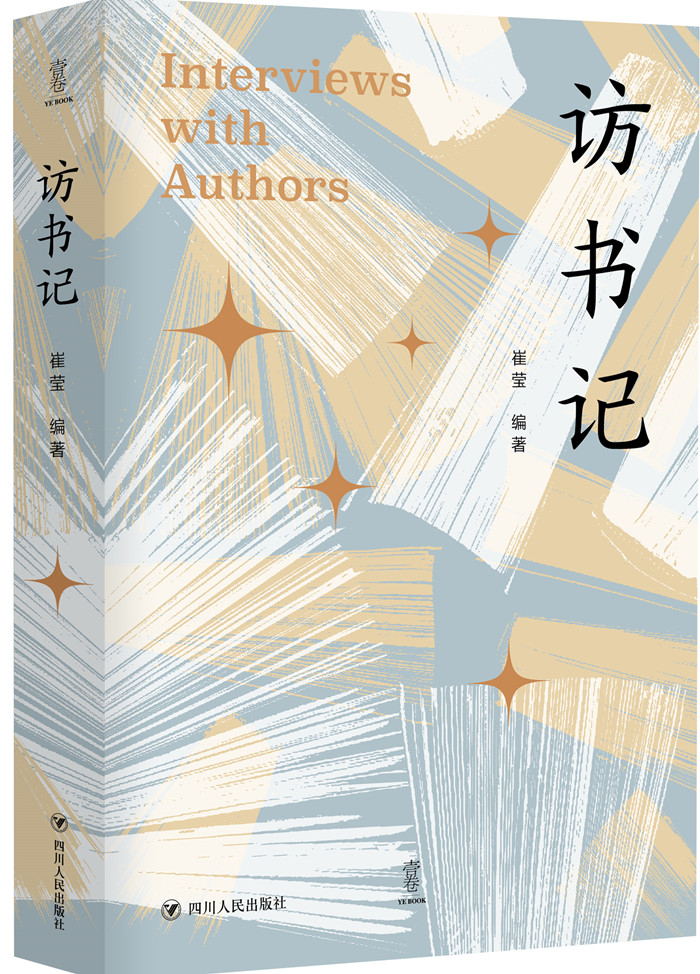
《访书记》
崔莹 编著
壹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11月版
《访书记》是一部关于书与国际写作者的访谈录。这些写作者,以学者和作者居多,比如马萨诸塞大学历史系教授裴士锋、著名汉学家卜正民、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百万畅销书《岛上书店》作者加布瑞埃拉·泽文等,也包括有从法官到殡葬师,从时装模特到漫画家的多样身份。访谈的内容涵盖汉学、历史、文学、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透过访谈,读者可以更加走近这些赫赫有名的佼佼者,了解不同领域的动态,深入探究各个领军人物的思想。比如,异域的汉学家如何理解中国,历史家怎样梳理历史背后的脉络,文学作家如何构思出一部小说,非虚构写作者怎样创作出客观又叫好的著作,社会学家如何阐释现代性,漫画、童书作者怎样看待这个世界,等等。跟随这些访谈,我们能打探这个多样的世界,也能回溯过去,思索未来,收获丰富的人文知识。

>>内文选读:
《红楼梦》如何译成英文?
迄今为止,《红楼梦》有两个最权威的英文译本,一个是由英国著名汉学家霍克斯和闵福德合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石头记》);另一个是由中国学者杨宪益和其英国夫人戴乃迭合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红楼梦》)。两个译本都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四位翻译家也相知相惜,结下深厚友谊。杨宪益的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White Tiger)便由闵福德作序。
闵福德还创建了《红楼梦》的英汉双语网站,他希望更多的西方读者了解这部中国经典,步入《红楼梦》的世界。
除了《易经》与《红楼梦》,闵福德还是《道德经》《孙子兵法》《聊斋志异》等书的英文译者。闵福德在采访中回忆他和霍克斯共译《红楼梦》的过程,与杨宪益和戴乃迭的交往故事,以及他翻译书的心得。
喜欢贾宝玉和薛蟠
崔莹:你是怎么参与到《红楼梦》的翻译工作中的?霍克斯在翻译中起了什么作用?
闵福德:那时我还是牛津大学的年轻学生,我的本科老师霍克斯希望我和他一起翻译《红楼梦》,他翻前八十回,我翻后四十回。在翻译过程中,除了理解原文,我花了大量时间学习霍克斯的译文和风格,学习如何写英文小说。我当时非常穷,但放弃了其他工作,全心投入。霍克斯也一样——为了翻译《红楼梦》,他放弃了牛津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工作。
我们的私交非常好,但是我们各自的工作都很独立,他从不干涉我的翻译。不是自夸,我觉得我翻译得还行。我觉得当读者读完前八十回、开始读第八十一回时,会感到中间的过渡比较自然流畅。霍克斯对我的译文也很满意。这是我此生做过的最令我感到开心的事情之一。
崔莹:你最喜欢《红楼梦》的哪个人物?
闵福德:贾宝玉。很多人认为贾宝玉不好,因为他易变、多情、敏感,但是我觉得,他从一个多情的人最终开悟,看破红尘,找到了真正的自我。
我喜欢的另外一个人物是薛蟠,虽然他经常招惹是非,但我觉得和他在一起相处一定很有意思。他一定是晚宴的主角,因为他不介意成为别人的笑柄。
崔莹:《红楼梦》在西方的影响大吗?
闵福德:说实话,读的人不太多。霍克斯和我翻译的《红楼梦》每年也就能卖出几百本。大概因为它太长了——《红楼梦》的英译本有5册,是《战争与和平》的2倍。对西方读者而言,读一部人物这么多、情节这么复杂的小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且这本书在西方的宣传也很不够,很多人连书名都没有听说过。
我正和《红楼梦》爱好者,主要是我的学生和同事,创建一个关于《红楼梦》的英汉双语网站,帮助人们步入《红楼梦》的世界。
崔莹:在西方名著中有类似《红楼梦》的作品么?
闵福德:最接近的应该是萨克雷的《名利场》,那本书的文笔也很优美,但是和《红楼梦》不在一个水平上。《红楼梦》是一座其他无法超越的高山。
中国文化始于《易经》,终于《红楼梦》
崔莹:你怎样评价杨宪益和戴乃迭合译的《红楼梦》?
闵福德:宪益和格莱迪丝(Gladys,戴乃迭英文名)是我的好朋友,我非常喜欢他们。以往我去北京,经常住在他们那里。我知道的是,他们两人并不怎么喜欢《红楼梦》,他们告诉我,他们更喜欢《儒林外史》。他们认为贾宝玉非常傻,他们不喜欢贾家这样享有特权的贵族,对小说中的人物不抱同情。
他们的译本算是准确的翻译,用的英文也很好,但是文字中不带有感情。宪益和格莱迪丝并不喜欢翻译《红楼梦》,只是不得不翻译。
霍克斯的译文充满了感情,他总是会在文中解释很多细节;遇到这种情况,宪益和格莱迪丝可能只会加个脚注。有人评价,霍克斯的翻译是“极繁式的”(Maximalist),试图解释所有的信息;宪益和格莱迪丝的译文是“极简式的”(Minimalist),只是把原文的意思写出来。
霍克斯几乎是在和读者对话,你可以感觉到他的存在。当我在医院给妻子读《红楼梦》的前三十一回时,我们两人时常会停下来,因为我们仿佛听到霍克斯在讲话——他用的是很个人的语言,他的翻译充满想象力,对话很有趣,也很感人。
后来格莱迪丝写信告诉霍克斯,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比他们翻译的强多了。
崔莹:有人指责霍克斯将原著中的道教文化改译成基督教文化,将中国词汇改写成符合外国读者习惯的词汇,比如把“潇湘馆”译成“the Naiad’d House”(Naiad’d是希腊神话中的湖滨仙女)。这样翻译合适么?
闵福德:在《红楼梦》的第一章,跛足道人唱了《好了歌》,其中一句话是“世人都晓神仙好”。霍克斯把这句话译成“Men all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很多人批评霍克斯用“salvation”(拯救),认为这是基督教用语,其实不然——所有的宗教信仰都可以使用这个词。霍克斯本人也不是基督教徒,他反对任何宗教信仰。
再比如,霍克斯将中国春节的最后一天翻译成“Fifteenth Night”,这借鉴了西方文化中的“Twelfth Night”(第十二夜),即基督教圣诞假期中最后一夜的用法。他的译文中类似的用法很多,这些只是翻译手段。霍克斯用西方文化中相关的词帮助读者理解中国文化,我倒觉得他这样处理非常聪明。这样译文更顺畅,读者可以理解故事,并且读得津津有味。霍克斯在和读者对话,他的翻译是以读者为主导的。
崔莹:有一种观点认为,你在《红楼梦》译著中有些夸张翻译得更直白。
闵福德:你可能指的是那位攻击我公开写妙玉对贾宝玉感“性趣”的德国人。读过后四十回的人都知道故事的情节,可能是我写得太清楚了,也可能是我不够含蓄……在那部分我想要表达的是,妙玉在庵中修行,但是她禁不住想念贾宝玉,这是她作为人的本性。我觉得我的译文还不错,一点都不色情。
崔莹:你认为《红楼梦》和《易经》有什么相似点?
闵福德:我用16年翻译了《红楼梦》,用12年翻译了《易经》。和《易经》一样,我觉得《红楼梦》也是一个“Spirit”。它们都是中国文化的巨著,都是读者的“镜子”——《红楼梦》的另一个标题“风月宝鉴”(Precious Mirror of Romance),指的就是一面两面皆可照人的镜子。
《红楼梦》的奇特在于,人们把《红楼梦》里的人物当作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人物,比如王熙凤,人们好像都认识她,见过她。《红楼梦》有点像《易经》,一旦你进入它的世界,它可能会改变你的人生。我认为中国文化始于《易经》,终于《红楼梦》。
崔莹:为什么说中国文化始于《易经》,终于《红楼梦》?
闵福德:《红楼梦》是完全“中国化”的作品,没有受其他国家文化的影响——曹雪芹从来没有读过西方的文学作品。《红楼梦》诞生不久,鸦片战争爆发,西方文化开始影响中国文化。因此,《易经》和《红楼梦》,就像是彩虹的两端。
译者要完全向翻译的文稿“投降”
崔莹:在翻译《红楼梦》时,你就爱上霍克斯的女儿瑞切尔?
闵福德:最简单的回答就是“是”。那时我经常去霍克斯的家,经常看到她。
她从来没有读过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直到她去世前两三个月。那时候她得了癌症,已经住院了。我建议她看《红楼梦》,她说:“那你就读给我听吧!”于是我就一直读,读了前三十一回给她听,这是她第一次“读”《红楼梦》前四十回,她非常喜欢。
但是读完第三十一回,她说她听够了,让我给读点别的。我想,她是觉得贾宝玉很讨厌:连衣服都不会穿,六七个丫鬟帮他穿衣服……我想,如果她多活几年,一定会把《红楼梦》读完。她学的是英文文学,帮我编辑了所有出版作品,包括《红楼梦》后四十回。
崔莹:从诗歌到小说,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你翻译了很多中文作品。你认为翻译是否存在技巧?
闵福德:我不觉得翻译有任何技巧,或者我没有感觉到。我的翻译经验是:译者要对翻译的文稿有感觉,喜欢这些文稿,能够全身心地投入。我不认同一些翻译理论,实际上,我反对它们,因为它们并不适合具体的情况。翻译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具有创造性的写作,在这种写作中,译者要忠实原文,也要投入自己的创造性,发挥想象力,而且译者的感觉和想象力要和原作者的不矛盾。总之,译者要完全向翻译的文稿“投降”。
在翻译《红楼梦》和《易经》的过程中,我完全沉浸于作品,这种投入帮助你找到合适的翻译方式。如同你在恋爱,只要你足够喜欢对方,即使出现问题,最终也可以找到解决方式。这种解决方式不是哪本书能够告诉你的,而是来自你的内心。
崔莹:严复的“信、达、雅”一直被认为是翻译的基本原则,后来你又加了一个“化”。
闵福德:严复的“信、达、雅”永不会过时。“信”指的是译文要忠实原文,如同译者和原作者有合约在先,译者不能想怎么译就怎么译。“雅”指的是怎么把文字写得优美——实际上,汉译英存在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在于译者并不知道怎么把英文写好。译者通常认为懂汉语最重要,但这只是翻译的第一步。霍克斯是优秀的翻译大师,这并非仅仅因为他的汉语好,而且因为他的英文写作也是一流的。他读过大量英文经典著作,如果你研究他的译作,你会发现他掌握了大量的英文措辞。伟大的翻译家都是如此,比如霍克斯的好友亚瑟·威利(Arthur Waley),他的英文也超棒。
“达”指的是译者要能将文稿融会贯通,译者要深入到文稿中去。至于“化”,指的是译者要能够在重铸、重塑、重组文稿等诸方面下功夫。
作者:崔 莹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