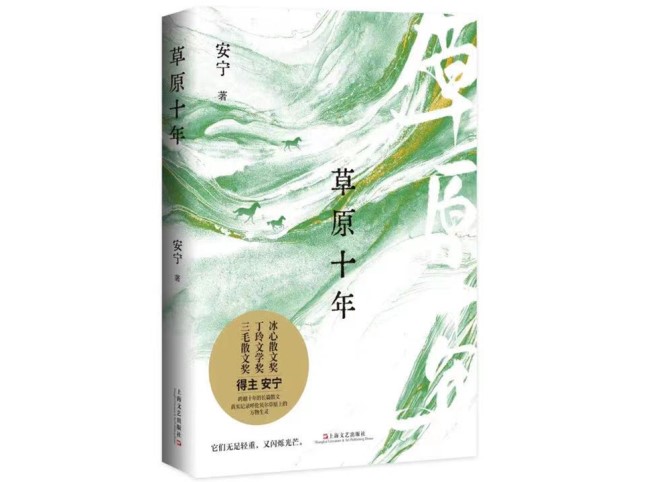
《草原十年》
安 宁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
《草原十年》是一部长篇纪实散文,它以一个草原小镇为标本,记录呼伦贝尔草原上普通牧民十年的生活变迁史。作家安宁在30岁到40岁的十年时间里,一次次回到自己的第二故乡——呼伦贝尔大草原。她看到了一个草原小镇的历史,一代人的历史,一个牧民家族的变迁,以及草原生态的变化。一切犹如汪洋大海,波澜起伏,每一道小小的褶皱中,都闪烁着时代耀眼迷人的光芒。
>>内文选读:
一切都在继续(后记)
犹如白驹过隙,十年转瞬即逝。我与这片广袤草原的吉光片羽,都记在了这里。这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有记忆,都化为我的血肉。从30岁到40岁,我将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年华,全部交付给这片辽阔深沉的大地。
在最初的几年,我并未意识到这种记录的价值,只是单纯以日记的形式,记下在草原小镇上历经的点点滴滴,记下我听到看到及敏锐捕捉到的细微的一切。而今,将十年的记录作为一个整体重新审视,我忽然意识到这种持续记录的意义所在:它以一个草原小镇为标本,用文学这种动人的形式,折射出呼伦贝尔草原上,普通牧民的十年生活变迁史。是的,我在跨越十年的记录中,看到了历史的变迁:一个草原小镇的历史,一代人的历史,一个牧民家族的变迁,以及草原生态的变化。历史之所以让人深思,是因当我们回望,会发现它犹如汪洋大海,波澜起伏,每一道小小的褶皱中,都闪烁着时代耀眼迷人的光芒。
只要草原永恒存在,这种记录,就没有休止。所以这是一部没有结局的作品。或许,我还会继续记录下去,一直到生命终止。就像每年的暑假,我都会带女儿阿尔姗娜前往呼伦贝尔草原,让她代替我,对这片苍茫大地继续新的观察和发现。

一切都在变化之中。犹如不息流淌的河流,生活也在继续向前。女儿阿尔姗娜已经六岁,阿爸阿妈也在呼和浩特跟我们生活了六年。记得阿妈最初从草原抵达千里之外的城市时,很不适应,常常望着窗外一栋拔地而起的三十层的高楼叹息说,她要老了,就一个人住,跟谁也不在一起,她不喜欢人来人往的热闹生活。几年前,赶上政府免费给牧民翻盖房子,她坚持加一部分钱,让凤霞贺什格图给自己和阿爸盖了一间跟正房隔着五六米远的小房子。看完阿尔姗娜她就回去继续喂牛喂羊,她不要死在呼和浩特,她也不要跟凤霞贺什格图住在一起。阿妈这样说。所以六年里,不管往返飞机票多么昂贵,每年暑假,我都会带着阿爸阿妈和阿尔姗娜,前往呼伦贝尔草原。有时,照日格图会劝说阿妈隔一年再回去,她便像个孩子一样倔强地发脾气:不行,那是我的家,我每年都得回去!借钱也得回!而阿爸在最初阿妈一个人前来呼和浩特时,因无法忍受孤独,甚至在某个夜晚,做出用镰刀割颈自杀的举止,幸亏抢救及时,没有大碍,在送往海拉尔医院的第二天,他就乘坐飞机奔呼和浩特的阿妈而来。
我眼看着这六年里,得了小脑萎缩的阿爸,从可以一个人下楼活动,生活简单自理,到而今大小便慢慢失禁,从客厅到洗手间的这一点距离,常常没等走到,就拉了裤子。有时捡起地上的东西,双腿快要废弃的他,甚至要费力地爬过去。他已经接近瘫痪在床的境地,有大半年,没有出过楼房了。每天,他要么塞上耳机,漫不经心地听收音机里的乌力格尔;要么艰难地扶着墙站起来,挪到窗户旁边,看着外面在大风中狂舞的柳树发呆。他的世界,只剩下一扇窗户。
阿妈也老了。她虽然比阿爸更快地适应了城市的生活,但因为不识字,汉语也不好,只能在家附近的街巷市场里走走,再远一些,她就会迷失方向。阿爸阿妈始终觉得,草原才是真正的家。所以就在今年暑假,我们决定让阿爸跟着阿妈和阿尔姗娜回草原后,不再一起返回呼和浩特,他将在草原上养老。有清甜的空气,湿润的泥土,朗塔的陪伴,几亩菜地,十几头牛羊,还有窗外大片的草原,和凤霞的悉心照料,比起坐监狱一样困在城市的楼房里,只能看到窗外一小片天空的生活,草原能让阿爸更舒适地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

生活还有其他的一些变化。小猫嘎塔不幸被狗咬死。去年的某一天,七条大狗从马路上冲过来,朗塔英勇迎战,无奈寡不敌众,只能眼睁睁看着其中一条狗,混乱中叼起嘎塔,呼啸离去。凤霞老舅跟前妻复婚后,一家三口搬去了陈巴尔虎旗,在那里养了很多牛,生活和睦幸福。经历过家庭变动的佐拉,格外珍惜失而复得的亲情,听说学习非常努力,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而萨日娜,再也没人知道她的消息,人们似乎将她忘记;惟愿她在打工中,也能寻到属于自己的爱情。阿爸在草原上做老客的巴特,他的姐姐大学毕业后,实习期间去蒙古国出差,不幸死于车祸。异国他乡,很难查到肇事者,更难获得赔偿,巴特的父母只能悲伤地将女儿带回,让草原护佑她最后的灵魂。塔娜的父母将西苏木的房子和牛羊全部卖掉,跟塔娜和通拉嘎夫妇搬去海拉尔市区。塔娜依然什么也不做,乐于享受生活。塔娜的母亲也不喜欢干活,人们都说,有其母必有其女;当然,她已经老得什么也做不了了。在一次西苏木的升学宴上,她啃骨头的时候,门牙不幸脱落了一颗,她没有钱补牙,又觉得不好看,于是每次出门见人,就用泡泡糖沾住。于是,她的这颗门牙的故事,就在西苏木人们的口中,流传了很久。
阿妈离开了草原,留下来的贺什格图和凤霞,却已经可以独当一面,支撑起整个的家庭。草原上的生活条件,比十年前有了很大的变化,虽然厕所还在户外,但水泵已经移到了室内,只需插上电源,打开开关,水就会哗哗流进水缸,比起过去的压水机,节省了很大的人力。打草也不像过去那样辛苦,放牛则可以手机软件遥控。为了牛犊的快速成长而不再人工挤奶后,养牛再也不需像阿妈那样早起晚睡,凌晨三点挤奶。当很多卖了牛羊进城打工的牧民,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停止工作且失去收入时,贺什格图和凤霞则每天都在辛勤劳作,喂养着二十头奶牛和十几头绵羊。今年又一下新添了十二个牛犊,每生下一头,凤霞就兴奋地朝阿妈微信汇报:又捡了一个大红包!在历经过去艰难的几年后,牛价飞涨,一头大牛值两万多,一头小牛也能卖到一万多块。很多如小叔小婶一样卖光牛羊的牧民,都纷纷后悔。但想要买回之前的牛羊,对于没有存款习惯的他们,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存牛比存钱更合适,贺什格图和凤霞忽然间意识到这个致富法宝。照日格图甚至也兴致勃勃地打算,花两万多块买一头优质母牛,让弟弟贺什格图代养,一年生一个小牛,十年后,两万块就变成了十二万,可是如果存银行,十年后,利息加本金,也不过四万块。

因为草原旅游业的兴盛,贺什格图在夏天时,就将牛交给人代养,自己开着六万块买来的二手车,拉零散游客在呼伦贝尔各大景点之间跑来跑去。他跟朋友们还组成了车队,消息共享。如果愿意花几千块钱,加入某个车队网站,活多得应接不暇。贺什格图还开始学习摄影,开车的同时,负责给游客拍美照,然后借传照片的机会,加人微信,这样可以有机会被客人介绍更多的活做。凤霞也会时不时地去旅游景点给人帮忙做饭,当服务生。在六月游客尚未到来之前,贺什格图和凤霞就去剪羊毛挣钱,给主人家剪羊毛是免费劳动力,但剪下来的羊毛,却可以自己拿去卖钱。剪完羊毛,贺什格图就会去做泥瓦匠,一天二百。在全民直播的年代,我还建议他们做牧民生活直播,尤其打草这种活计,外面人了解得不多,肯定充满好奇,慢慢积累人气,或许可以做大。但不管怎样,30多岁的贺什格图和凤霞,已经走上越过越红火的生活轨道,外人无需再为他们担心。在草原上,只要有牛羊,肯努力,能吃苦,挣钱不难,草原会善待所有肯辛苦付出的人们。
即便如此,西苏木小镇上的牧民,还是越来越少。人们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永无休止。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像凤霞所忧虑的那样,整个镇上,只剩下他们一户人家。但习惯了关门安静生活的他们,或许能够坦然面对这样的变化。
忽然想起多年前写过的一段话,那时,我以为记录完草原上的故事,就再也不会回来。不曾想,我却一次又一次地抵达,重新发现那些野草般蔓延至整个大地的故事。摘录在此,作为纪念,也作为结束: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即将离开草原。新鲜的故事,依然随了草原上清冽的空气,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一直觉得,人的悲欢,皆与我们灵魂中的孤独感有关。而草原上的故事,因为人烟稀少,更是植满了孤独。邻居家夏天时捉到的那只狍子,因不愿束缚在后园里,将绳子一圈圈缠绕起来,“上吊”自杀。镇上一个女人,因无人陪她喝酒,竟是醉醺醺地坐在草原上,捉了一只同样寂寞的青蛙,与其开怀畅饮。另外一个男人,在去年秋天近两个月的打草生活中,随身所带的收音机坏掉,收不到节目,但他依然开着,津津有味地听着嗤嗤啦啦的噪音,并因此觉得人生富足;看到人来,不管是否熟识,他都真诚地挽留,希望他们陪自己再多待一会,随便说一些什么……
但尽管孤独,草原上的人们,依然驻守在这片水草丰美的大地上。每年蜂拥而至的游客,带来多少关于外面世界梦幻般的想象,最终都尘埃一样消失。所有喧哗,途经此地,都如大风吹过,不过片刻,便静谧如初,宛如婴儿降临,世界一片洁净。”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前,再补记一段文字:朗塔,这只忠诚善良的牧羊犬,于2021年秋天的某个黄昏,预感到自己大限已至,于是悄无声息地离开家园,自此再也没有回来。我想它没有消失,只要草原上的人们俯身或者抬头,就能看到它,在辽阔的大地或广袤的星空中,散发微芒。
此刻,我很想它。
>>作者简介:
安宁,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荣获华语青年作家奖、茅盾新人奖提名奖、冰心散文奖、丁玲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作者:安 宁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