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
赵毅衡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
叙述学是一门条理相当分明的学问,但经过了100多年的研究,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这门学问才逐渐成熟。而作为其出发点的几条公理,20世纪80年代才有人点破。赵毅衡教授根据自己多年的体悟,得出其中最基本的一条公理:不仅叙述文本是被叙述者叙述出来的,叙述者自己,也是被叙述出来的——不是常识认为的作者创造叙述者,而是叙述者讲述自身。在叙述中,说者先要被说,然后才能说。
>>内文选读:
关于叙述学
叙述行为能叙述一切,就是无法叙述叙述行为本身,叙述行为实际上比被叙述出来的文本高一个层次。正如一面墙上有告示“此处不准贴告示”,此告示违反规定吗?不,它首先要被告示出来,才能进行告示。哪怕叙述者(无论是真人还是被委托的人物)说“我这就寄”“我即刻发”“幕在落下”,他说的依然不是了结叙述的叙述行为,而是被叙述的内容。
叙述学实际上是个条理相当分明的学问。只要把头开准了,余下的几乎是欧几里得几何学式的推导——从公理开始,可以步步为营地推及整个局面。在人文学科中,这样的好事几乎是绝无仅有(可能语言学会有类似情况),尤其是,这样一门再清晰不过的学问,100多年来有那么多名家,写了那么多的书,却要等到20世纪下半期,到70年代后,这门学问才渐渐成熟。而作为其出发点的几条公理,竟然要到80年代才有人点破,而公理中的一条最基本公理,我觉得我自己的体悟,可能比旁人更为清楚。这条公理就是:不仅叙述文本,是被叙述者叙述出来的,叙述者自己,也是被叙述出来的——不是常识认为的作者创造叙述者,而是叙述者讲述自身。在叙述中,说者先要被说,然后才能说。说者/被说者的双重人格,是理解绝大部分叙述学问题的钥匙——主体要靠主体意识回向自身才得以完成。
困难在于,叙述学没有一个欧几里得。它是反向积累的:先有很多学者研究个别题目,例如视角、意识流、作者干预、不可靠叙述,等等,然后有一些结构主义者试图综合成一个个体系,然后有许多后结构主义者试图拆解这些体系,只有到这个时候,公理才被剥露出来。本书的讨论得了后瞻的便宜,才有了一个貌似整齐的阐述。
从这个意义上来回顾,的确叙述学这门似乎并不复杂的学问,也只有依托当代文学/文化学的全部成果,才可能精密起来。首先是詹姆斯、伍尔夫、普鲁斯特、契诃夫等人创造了现代小说,实践远远地走在理论之前,才在本世纪初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小说技巧的讨论。但这只是叙述学的“前历史”。叙述学是20世纪的文学文化理论大潮(很多人认为20世纪是理论世纪,文学理论比文学创作成绩更大)的最具体实用的产品: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索绪尔语言学、布拉格学派、新亚里士多德学派诸家群起;60年代结构主义积富而发,直扣门扉;直到后结构主义符号学,以人类学术思想提供的最精密分析方法,登堂入室。所有这些学派无不关注小说的叙述(以诗为分析基型的英美新批评,也数次试图把他们的理论系统使用于小说叙述),把它作为分析其他人类传达活动文化活动的范式。
骄傲睨世的巴黎知识分子群体,竞争激烈的美英大学才子,如此多强有力的头脑倾注精力于此,必然有所原因。明白了小说的叙述学,就有了一套最基本的工具,并不复杂却十分犀利的工具,就可以比较清楚地进入电影学、传媒研究、传播学乃至文化学。反过来说,没有叙述学的基本知识,做这些研究就有可能犯一些沙上建塔的常识错误。
我不想说叙述学是什么了不起的学问。应当说,叙述学谈的看来是一些很浅显的分析工具问题,要弄清楚却还是需要动一番脑筋。尤其是,许多批评家似乎认为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布斯《小说修辞学》等比较容易读的“前符号学”叙述学著作,已经解决了全部问题。基于此而写出的整本小说研究,往往理直气壮地重复他们的错误,已经被后来的叙述学家说清了的一些错误。因此,系统地学一下叙述学(或补一下叙述学课),或许对每个专攻文艺学的学生有好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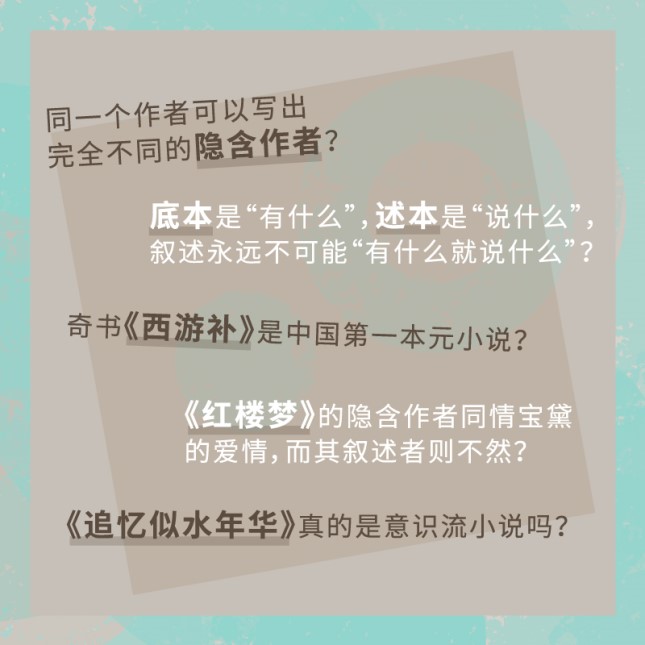
关于叙述者决不是作者
法国现代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多卷本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是一个叫马塞尔的人讲述他自己一生的经历,在最后一卷的结尾,马塞尔历尽人世沧桑,看透了爱情和荣华之空虚,决定坐下来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有阅读经验的读者很容易猜到小说中的马塞尔,是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影子”,或“人格转化”。他想写的这本书应当就是《追忆似水年华》,因此,此书是一般所谓的“自传体小说”,或“有强烈自传性的小说”。这样说当然有道理。但把作者等同于叙述者,从叙述学上来说,会漏洞百出。《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卷《斯万家那条路》出版于1913年,最后一卷《时间失而复得》在作者去世(1922年)之后才整理出来。而根据作品中的情节推算,叙述者马塞尔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五六年之后,也就是说,大约1924年左右,才下决心坐下来写作。叙述者马塞尔在作者马塞尔(普鲁斯特)死了两年后才下决心叙述十年前已经开始叙述的马塞尔的故事。
要解开这个乱成一团的时间之谜,我们只有把马塞尔分成三个人,即叙述者马塞尔、主人公马塞尔以及作者马塞尔·普鲁斯特。叙述者马塞尔并非作者马塞尔·普鲁斯特(文学史家很容易证明这两个人多么不同,当然他们也能证明他们如何相似,但这与叙述学无关);叙述者马塞尔也并非主人公马塞尔(叙述者马塞尔成熟、深沉,善于观察、分析,被叙述的主人公马塞尔热情、冲动、靠本能行动;叙述者马塞尔在全部情节结束后的某个时刻开始叙述行为,被叙述的马塞尔从年轻时开始经历小说中叙述的全部事件)。这个区分法适用于一切文学叙述。
关于作者与隐含作者
与叙述分析有关的所谓作者,是从叙述中归纳、推断出来的一个人格,这个人格代表了一系列社会文化形态、个人心理以及文学观念的价值,叙述分析的作者就是这些道德的、习俗的、心理的、审美的价值与观念之集合。这个价值与观念集合与文学史家所找出的作者思想意识(如果他们能找出的话)可能完全相合,可能部分相合,也可能完全不相合。不管如何,这个集合是实际参与写作过程的作者的代理人,作者的“第二自我”,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二自我”是作者通过作品的写作创造出来的一个人格。
对于叙述学而言,只有这个作者的“第二自我”才是真实的、可靠的、可触及的、可批评的、可分析的人格。这个作者的第二人格,这个支持作品的价值集合,现代文学理论一般称为“隐含作者”,因为他是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中推论归纳出来的。
从隐含作者的概念可以得出一个乍一听可能十分奇怪的结论:同一个作者可以写出完全不同的隐含作者。因为他完全可以在不同的作品中使用完全不同的价值集合,有时是因为他思想变化了,有时却可能是他戴上了不同的面具而已。讽喻诗和闲逸诗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白居易。宋人写的诗和词经常判若两人。《蚀》三部曲的隐含作者与《子夜》或《林家铺子》的隐含作者很不同:前者热烈而悲愤,后者冷静而观察犀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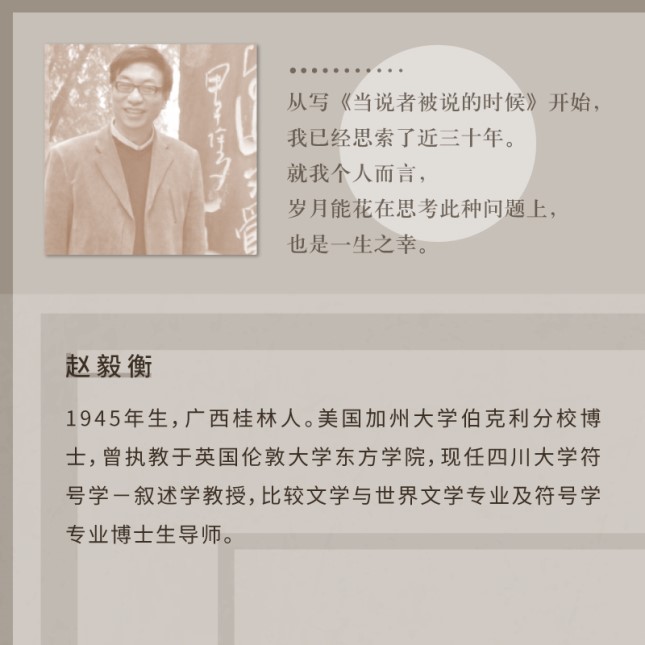
作者与隐含作者的区别
隐含作者不能等同于作者本人,只要有文本,隐含作者永远不死。一般来说,隐含作者很多都含有美化的成分,《吴宓日记》中的隐含作者比吴宓本人更加高尚。元稹《离思五首·其四》(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这首诗中的隐含作者是个对妻子、对爱情忠贞不渝,非伊莫属、爱不另与的痴情之人,用世间至大至美的形象来表达对亡妻的无限怀念,任何女子都不能取代韦丛。然而,真实世界中的元稹却与隐含作者截然不同,他风流浪荡,与薛涛、刘采春等女性有染。
沈从文的小说《边城》的隐含作者拥有宁静恬淡的人格,《丈夫》的隐含作者拥有世俗激愤的人格,它们都代表作者价值观的一部分,但都不是作者本人。
《少年维特之烦恼》是曾经让无数的青年为之倾倒的一部小说,其隐含作者肯定是一位情感丰富的少年,他深谙维特之苦,他将维特引向了死亡;但是,歌德本人非常全面,理性和感性同样发达。
由此可见,任何叙述的隐含作者不能等同于作者本人。隐含作者是由读者阅读归纳、推断出来的一个人格,并不代表作者本人的人格。一般来说,隐含作者都比作者高尚,因为隐含作者是受社会道德、习俗、审美价值及文化形态等因素影响的,因此与作者本人相比,隐含作者是倾向于道德的、符合社会价值的人格。
作者:赵毅衡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