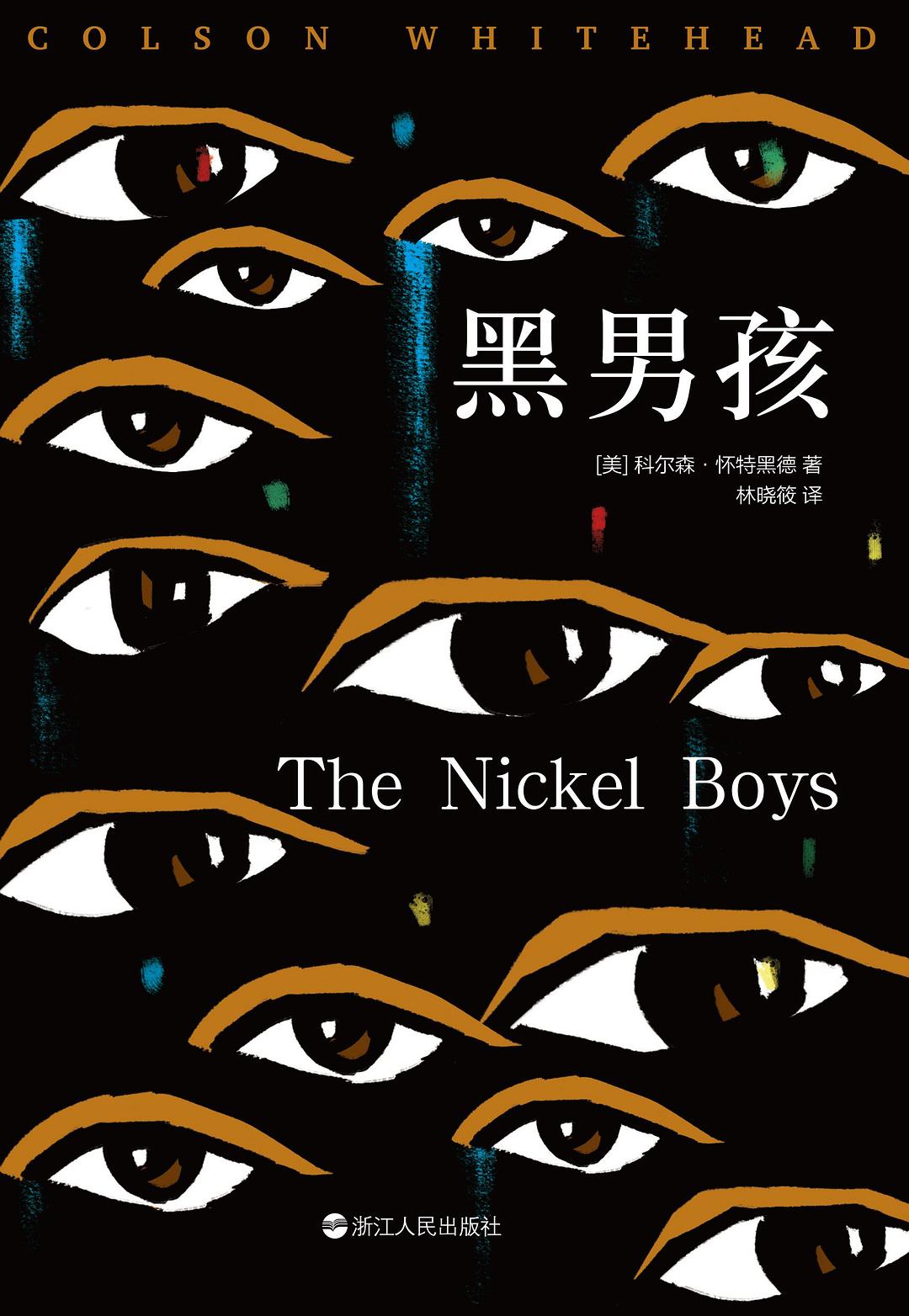
凭借《黑男孩》,科尔森·怀特黑德再度获得普利策小说奖——这是能与福克纳、厄普代克比肩的殊荣。近期,这部作品被引进出版,更多读者得以走近这位当代英语世界最受瞩目的小说家之一。
在《地下铁道》之后重访“种族主义”这个沉重的话题,并不是怀特黑德一时兴起,而是他多年来的“夙愿”。2014年夏天,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市一个手无寸铁的18岁黑人青年被白人警察枪杀,进而引发了“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反种族主义抗议与骚乱。但身为小说家,在催泪瓦斯和燃烧弹面前,怀特黑德感到了“深深的无用感”。他回忆道,“弗格森的夏天开启了我们对暴行的新一轮讨论”,尽管有关黑人与警察的探讨“总是冗长而乏味,我们或许会就警察暴力执法的问题讨论上个一年,之后便偃旗息鼓,再然后一个新的轰动性事件让我们重新开始讨论”。怀特海特不禁自问:“我又能做点什么?”
同样是2014年的夏天,怀特黑德被另一个“暴行”事件震惊。在浏览推特的时候,他看到了有关阿瑟·多齐尔少年管教所的报道。这座位于佛罗里达州首府附近、成立于1900年、曾是全美规模最大的少管所遭到举报,被指控涉嫌虐待、毒打、甚至谋杀其看管的未成年人,最终经调查确认属实,被州政府在2011年正式关闭。2012年,得到授权的南佛罗里达大学考古团队对其进行了遗骸考察,测算显示,有将近100名男孩死在这里。此消息被各大媒体竞相报道,整个美国为之惊骇。那时的怀特黑德有种直觉,有一天他会为此写点什么。
在之后的几年,“白人警察”“少管所”“暴力执法”“监禁虐待”等词条不断汇聚交织,怀特黑德开始一遍遍思考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身为非裔美国人,他自然而然地联系到种族问题——奴隶制、吉姆克劳种族隔离、无处不在的种族歧视。用他的话来说,“写一本有关我们体制性失败的书,有关种族主义和监禁体系的书,似乎能够帮我搞清楚,我们这个国家到底身处怎样的境况”。
《黑男孩》以多齐尔少管所的一名幸存者为叙述者原型,怀特黑德借其回忆之口讲述了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一个荒唐骇人的故事:行为得体、成绩出色、被马丁·路德·金深深感化的黑人男孩埃尔伍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搭乘了一辆黑人偷来的车准备去上大学,却被不问青红皂白的警察关进了尼克尔教养所,在那里开始了被奴役、欺凌、虐待的生活,最终丧命于逃跑的途中。
同是基于事实的虚构改写,但相比以黑奴逃亡为故事核心、首获普利策奖的《地下铁道》,怀特黑德坦言,《黑男孩》的创作让他感到更加沉重:对于前者,“我在动笔之前已经做好了起重工作,写作过程中只需要做些研究、再以某种(文学)方式将奴隶制呈现出来”;对于后者,“我是在一种永远无法平息的(愤怒)中一步一步走向小说尾声的。而当我写完它,我看到新闻中正有一大批(移民)孩子在美国边境被送往集中营监禁”。如果说《黑男孩》是一个关于有权的强者凌虐无力的弱者、却从未遭受责罚的故事,那么令怀特黑德无比沮丧与愤怒的是,这样的故事不仅发生在种族问题最严峻的20世纪60年代,同样发生被宣称为“后种族时代”的当下美国。
就在《黑孩子》荣获普利策小说奖的当月,46岁的非裔美国男子乔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致死。作为一个悲观主义者,对于弗洛伊德案引发的全美乃至全球范围的反种族主义游行示威,怀特黑德并不认为会带来多少实质性的变化。“如果你要写有关体制性种族主义和(美国)人作恶能力的故事,你可以选择1850年、1963年、或者2020年。不幸的是,这样的故事实际上适用于所有时期,它正在发生,而且在未来的许多年,它仍将继续。”如果说怀特黑德用历史与虚构的杂糅想象、通过《地下铁道》和《黑男孩》探访了前两个最黑暗的时期,那么出生于1969年的他本人却用50多年的人生见证了种族主义幽灵的无处不在。

怀特黑德出生在纽约一个优渥的非裔家庭,父母是成功的商人,他和兄妹四人从小就住在曼哈顿上城,上的是精英阶层专属的私立学校。但他父亲脾气暴躁,还有点酗酒的毛病,阴晴不定的家庭氛围让童年的怀特黑德性格孤僻、充满了不安全感。他自述继承了父亲“在看待美国种族问题上,那种犹如末日即将降临一般的悲观态度”,并且一再真实发生的可怕事情让他“放弃了种族问题终将有所改观的念头”。尽管1964年民权法案和1965年选举权法案彻底废止了种族隔离政策,尽管2008年奥巴马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裔美国总统,尽管怀特黑德毕业于哈佛大学英文系、现住在位于长岛的一处4000平方英尺、占地2英亩的房子,他清楚每一个黑人都知道的事实:无论取得多大成就、拥有多少财富,都无法摆脱黑皮肤所遭受的异样待遇,都无法改变他有一个曾是弗吉尼亚黑奴的祖先,他的名字科尔森正源于那个人。“每当有警察巡逻车从我身边缓缓开过,我都会想,我的生活方向会不会在今天发生改变”,怀特黑德一直真切地笼罩在这种惶惶不安之中。
怀特黑德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黑男孩》中,埃尔伍德是马丁·路德·金的忠实粉丝,不仅将金的演讲当成自己的座右铭,更在日常生活和少管所中切实践行了金的非暴力抗争理念:坚守正义的原则,坚信人性的力量,坚持用爱感化敌人、进而赢得自由。但残酷的现实一次次嘲讽、粉碎了金的理想主义,直到遍体鳞伤的埃尔伍德只保留了隐忍的能力。对所有曾遭受殴打、强奸、残杀的“黑男孩”而言,“爱”只是一种奢侈、甚至有些荒唐的要求。怀特黑德亦坦言,他无法像马丁·路德·金那样,用博爱去拥抱压迫自己的人,但他可以做到、也必须做到的是,在残酷的现实中保留一点希望感。尽管小说的笔调是阴森灰暗、令人压抑的,但怀特黑德并没有将叙述引向彻底的毁灭,而是收尾于一个死里逃生者的救赎与重生。
在创作《黑男孩》的日子里,每天早上打开电脑,怀特黑德都会看到两句话:“犯罪的人逃脱了惩罚。无辜的人忍受着痛苦。”这是动笔之初他为自己写下的备忘录,希望以此提醒自己,到底要讲述一个怎样的故事。然而,写完后他却发现,小说后三分之一讲述的都是这两句话之外的东西:“面对这个事实,你会怎么做?明白这就是现实之后,你会选择如何生活?你又将如何适应它?”
“乐观是我不得不保持的心态”,在怀特黑德看来,这是身处种族主义的黑暗漩涡而不被绝望吞噬的“自救”。毕竟对万千随时可能成为下一个埃尔伍德和弗洛伊德的美国黑人而言,活着本身就是一件需要用尽全力的事。
作者:孙璐(文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编辑:范昕
策划:邵岭
责任编辑:邵岭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