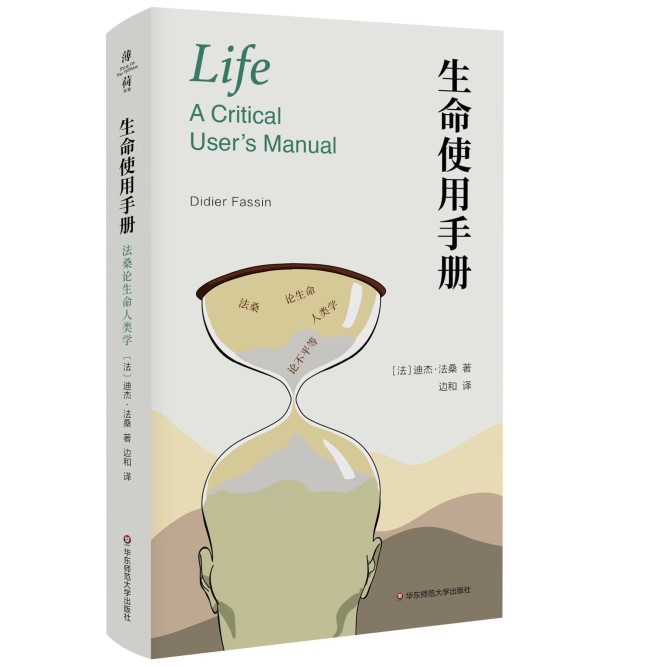
《生命使用手册》
[法]迪杰·法桑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人类学家、哲学家迪杰·法桑教授在法兰克福关于生命伦理的系列演讲集。在社会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的当下,迪杰·法桑教授论述了人类生命价值的问题,对生命伦理进行了综述和反思。本书通过在三大洲进行的研究,并与维特根斯坦、本雅明和福柯进行批判性对话,以敏锐的哲学洞察力、生动的人类学细节为基础,以物质和经验、生命和生活的双重表现形式来思考生命,揭示了我们对待人的生命所涉及的道德过程,从而调和了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方法。
>>内文选读:
当我们在讨论生命时,我们在讨论什么?
但是,当我们谈论生命时,我们真的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因为这种种不确定性,我们需要首先考虑这个词语本身的意思。
“生命,一个不能再熟悉的词汇。如果追问它到底什么意思,可能会让人觉得这是种挑衅”,约翰·洛克写道。他话锋一转,“然而,如果我们问:一颗植物的种子有生命吗?一枚卵子形成的、还未发育的胚胎有生命吗?一位晕厥过去、失去感觉一动也不动的男子还活着吗?可见,并没有一个清晰、稳定而明确的意思附着在生命这个如此常用的词语上”。对洛克而言,首要的问题是去确定生命的边界:从种子或卵子中的源起暧昧不明,围绕这一议题今天仍存在着关于自主终止妊娠的辩论;在无声无息中失去意识的死亡亦难以界定,例如后世关于脑死亡认定的争议。然而,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层面去理解试图对生命加以定义所带来的问题,即这个词语本身的多义性。它同时代表了以下意思:一切有机体所共有的一种特质;一系列生物现象;从生到死的时间区段,以及在此期间发生的所有事件?还有它作为同义词和隐喻所生发出来的各种用法,例如伟人的“生平”或是事物的“生涯”等。在所有这些用法中,我们所说的都是同样的生命吗?一个人的生命与组成他/她身体所有细胞的生命之总和,是同一尺度上的事实吗?在所有这些用法中,我们所说的都是同样的生命吗?一个人的生命与组成他/她身体所有细胞的生命之总和,是同一尺度上的事实吗?
当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语言不会纠缠在这些复杂的情形中。虽然它的用法纷繁多面,例如“生命科学”(life sciences)、“预期寿命”(life expectancy)、“乡村生活”(life in the country)或者“观念的生命”(life of ideas),大家却都能明白彼此在说些什么。而哲学家们则不是这样,他们似乎无法去尝试考虑生物学家视野中的“生命”究竟如何与小说家笔下的“生涯”相互联通。

乔治·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对这个问题阐述得很清晰:“即使是今天,也许我们仍然无法超越这个最初的想法:任何能够在出生与死亡之间的历史跨度中被描述的、经验层面上的零散信息,就可以说是活着的,并且构成生物学知识的对象。”这个看似足够简单的定义,实际上将若干异质的元素拼合在一起,产生语义学的张力。知识与经验、生物学与历史:或许这就是生命内部最重要的二重性。这个看似足够简单的定义,实际上将若干异质的元素拼合在一起,产生语义学的张力。知识与经验、生物学与历史:或许这就是生命内部最重要的二重性。汉娜·阿伦特也在《人的境况》中指出:“就人受生物生命的驱动而言,它与其他生物同样永远遵循着自然的循环运动;但由于人的生命又被一个开端和终结所限制,即被两个终极事件——在世界上的出现和从世界上的消失——所限制,从而它又遵循着一种严格的线形运动。人特有的生活的主要特征是,不仅它的出现和消失、生和死构成了世界性事件,而且他一生当中也充满了各种事件,这些事件最终可以讲述为故事,或写成自传。”自然的往复循环与世事变迁,生物性的生命与传记生平中的生命:这两条线索所建构的人生,总是同时在物质维度上被提前预定了命运,却在具体的生涯中充满不确定性。前者将人类纳入到万物生灵的巨大群体中,与动植物为伍;后者则将人类尊为万物之长,因其拥有意识和语言的特殊能力。自然的往复循环与世事变迁,生物性的生命与传记生平中的生命:这两条线索所建构的人生,总是同时在物质维度上被提前预定了命运,却在具体的生涯中充满不确定性。前者将人类纳入到万物生灵的巨大群体中,与动植物为伍;后者则将人类尊为万物之长,因其拥有意识和语言的特殊能力。
我们应该如何去破解这样的二元主义?同时去思考生物学意义上和传记意义上的人生是可能的吗?两千年以来,哲学家们孜孜不倦地试图攻克这个问题。有的尊崇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将人的生命看作获得了勃勃生机的物质;有的追随笛卡尔,认为生命是一种产生运动的机械构成;康德则认为生命是能够自我维护的有机体。因此,整个哲学史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即从活力论(vitalist)演化到机械论,最终达到以有机体作为理解和再现生命的基本手段,所关注的介质也从灵魂或气息过渡到肌体和体液,再到器官与内环境。然而,每一种理论解读都是为了去追问“活着的”和“人类的”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说成是前者的基础设施与后者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黑格尔的思想中,生命是“一个过渡性的概念,它将自然的领域和自由的领域联系在一起”,托马斯·库拉纳(Thomas Khurana)这样评价。人类虽然受到生物学因素的种种限制,但可以通过自组织的过程去产生自主性,进而获得去追求和实现人生道路的可能性。
和这些早先试图阐明生命二重性的思想理论相比,这两重意义之间的对立在20世纪的论述中变得尖锐和固化,近些年来尤甚。这导致生物学与人文之间的分歧变得似乎无法逾越。
作者:迪杰·法桑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