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形象诞生于1921年,迄今已经一百年。无论是否读过、读过多少,我们都知道这一形象是鲁迅先生用以讽刺当时社会一些心灵丑陋的中国人,知道“精神胜利法”的悲哀。诚如茅盾所说:“我们不断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遇见‘阿Q相’的人物:我们有时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上也免不了带着一些‘阿Q相’的分子……我又觉得‘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似人类的普通弱点的一种。”
一百年过去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再闭塞、落后,而是文明且欣欣向荣。然而我们是否全然摆脱了阿Q的“影子”?答案并不肯定。而回忆阿Q,再看阿Q,我们依旧能从他的身上窥见难以直面的民族根性,因此仍然有必要以阿Q为镜,以省自身。这是鲁迅先生的作品的超越性意义,更是阿Q形象的意义和魅力。
《阿Q一百年——鲁迅文学的世界性精神探微》为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鲁迅研究专家张梦阳先生历三十年沉淀而成的、再思考阿Q的全新学术专著,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从学史论、典型论、悟性论、历史论等大的宏观视野入手,高瞻远瞩而又入木三分地剖析阿Q的言谈举止;从微观视角深入揭示了阿Q精神现象活泼而又异常深邃的含意;从各个发展历程考察人性、民族性和阶级性的种种变化。借助阿Q这一人物形象和世界文学中经典角色哈姆雷特、堂吉诃德、奥勃洛摩夫比较,启迪读者对自己和宇宙重新进行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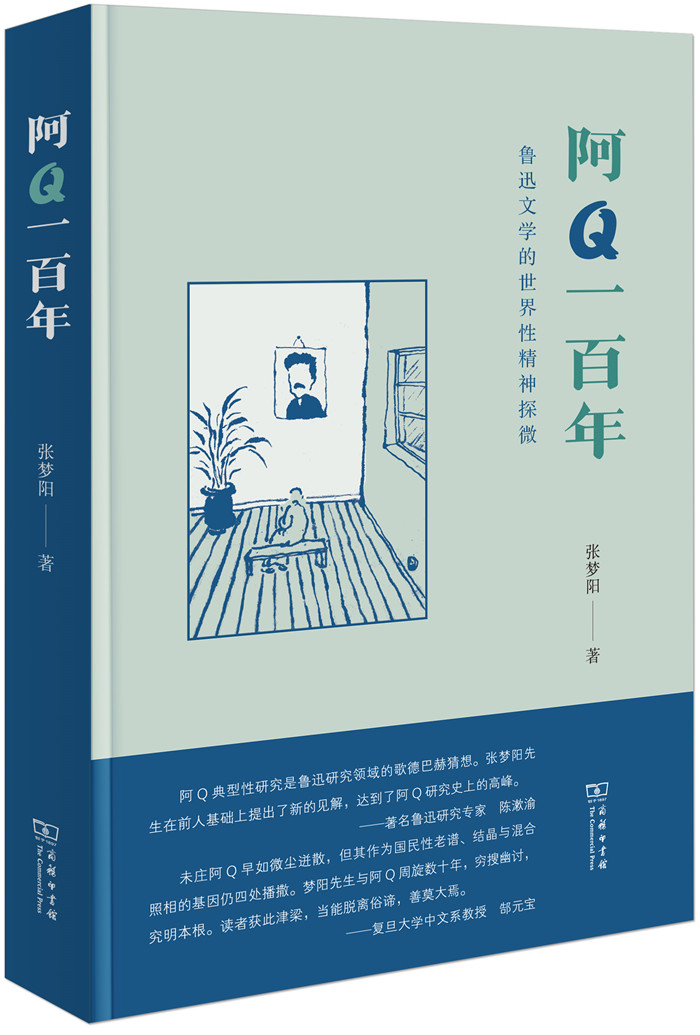
《阿Q一百年——鲁迅文学的世界性精神探微》
张梦阳 著
商务印书馆2022年5月版
内文选摘:
一百年前的1921年冬天,《晨报副刊》主编孙伏园到阜成门内八道湾11号拜访鲁迅先生。他是鲁迅在绍兴时的学生,打算在他主编的《晨报副刊》办个《开心话》栏目,刊载与汇聚一些可笑、幽默的文字,让人们在阅读报纸时获得轻松快意。他就是来向鲁迅先生约稿的。鲁迅答应了,写他酝酿很久的《阿Q正传》,当晚写出了第一章《序》。为了依循《开心话》的栏目风格,将先前用于《狂人日记》《药》等作品的笔名“鲁迅”更换为“巴人”,“取‘下里巴人’,并不高雅的意思”。第一章《序》的话语风格也与先前的含蓄深敛、凝练沉郁不同,多了许多幽默和风趣。表面依照传记通例,但具体内容却完全抽空式处理,姓氏、名号、籍贯等无从确认,与传统史传的严肃“崇高”生成反讽,也与先前严峻深刻的批判大相径庭。
从12月4日起,至1922年2月12日止,《阿Q正传》在北京《晨报副刊》分章连载,每周或隔周刊登一次。
据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说:“第一章登出之后,便‘苦’字临头了,每七天必须做一篇。我那时虽然并不忙,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里,这屋子只有一个后窗,连好好的写字地方也没有,那里能够静坐一会,想一下。伏园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胖,但已经笑嬉嬉,善于催稿了。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于是只得做,心里想着‘俗语说:“讨饭怕狗咬,秀才怕岁考。”我既非秀才,又要周考真是为难……。’然而终于又一章。但是,似乎渐渐认真起来了;伏园也觉得不很‘开心’,所以从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艺’栏里。”“大约做了两个月,我实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似乎伏园不赞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会来抗议,所以将‘大团圆’藏在心里,而阿Q却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园倘在,也许会压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几星期的罢。但是‘会逢其适’,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君,于阿Q素无爱憎,我便将‘大团圆’送去,他便登出来。待到伏园回京,阿Q已经枪毙了一个多月了。纵令伏园怎样善于催稿,如何笑嬉嬉,也无法再说‘先生,《阿Q正传》……。’从此我总算收束了一件事,可以另干别的去。”
这样,阿Q就诞生了。如果不枪毙,长寿的话,如今已经130岁左右了。
作者:张梦阳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