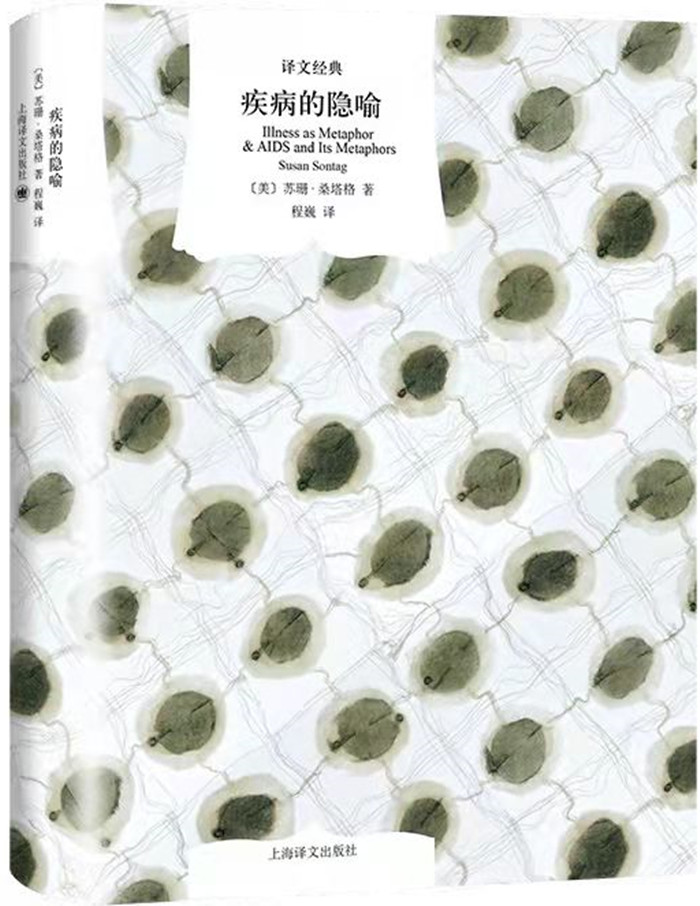
《疾病的隐喻》
[美] 苏珊·桑塔格著
程 巍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2020年年初,新型肺炎疫情不期而至,在较短时间内极大地改变了各国百姓的生活秩序和生存状态,迄今为止仍然难以驭服的新冠疫情,在某些国家很大程度上唤起人们的负面情绪和灰色心里,使人们经常将其与病魔、死神、灾难以及其他不祥事物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对新冠疫情的隐喻化和污名化,更易引发人们的烦躁心理和焦虑情绪,在这种情形下,阅读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一书,可能会带来些许慰籍、感悟和启示。
挥之不去的隐喻魅影
《疾病的隐喻》是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桑塔格的经典文论著作,在书中桑塔格运用知识考古的办法,考察和梳理了肺结核、艾滋病、癌症等疾病隐喻化的生成机制和重要表征,袒露和揭橥了挥之不去的隐喻魅影,还原和复盘了传染病的本来面目和固有属性,力求解蔽和剥离加诸传染病的种种预测、猜疑、类比和想象,为传染性疾病祛魅和正名。在《疾病的隐喻》中,结核病、艾滋病和癌症一直被人们视为上帝对违反天条的人做出的一种惩处,是对亵渎道德和践踏伦理的人做出的一种责罚,但桑塔格在书中并不认可这是上苍的一种愤懑,坚持认为结核病、艾滋病和癌症是纯粹的生理疾病,是属于医学范畴的疑难病种,不应被强行赋予政治意蕴和社会内涵,更不应将传染性作为界定和裁决人们身份与品行的主要标准。认知语言学创始人之一、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乔治·莱考夫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指出,“隐喻的本质就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依照莱考夫教授的这一逻辑,传染病似乎是一个内涵比较模糊、边界无法厘清的概念,是一种传染病患者难以用身体经验换取明确医学结论的逻辑,这势必将人们对传染病的认识引向不可知论,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在传统社会乃至当下时代,人们对包括结核病、艾滋病等传染病和癌症,更愿意从文化层面进行解释、阐发和演绎,且这种演绎沿袭甚久、杂乱无序,将原本由医学回应和解答的简单问题加以政治化和社会化,正如桑塔格在书中所说传染病隐喻化日益成为一种政治话语,成为某种社会意识与文化标签。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桑塔格对传染病隐喻化的文化理路进行了阐述和揭示:结核病被指涉忧郁和敏感的标志,甚至成为精致、优雅的代名词,肖邦、契科夫、雪莱、梭罗等西方文化史上诸多著名作家艺术家死于肺结核,但他们无一例外地被罩上一件情趣高尚的美学外衣,在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社会,肺结核还被当作上层社会独有的病种和最具美感的疾病,患上肺结核这种传染病就意味着人格的提升,每一位结核病患者其身份都比普罗大众高贵,肺结核就这样被浪漫主义思潮推上了神坛,成为风靡一时的“艺术家之病”。作者还联系西方文艺复兴以后人文主义大倡其道的社会背景,指出彼时人们给结核病和癌症镀上一层神话的光环,比如结核病是“容易触发感情”的气质即善感性引发的,患者脸色潮红的症状代表着娇涩羞赧的样貌,而身体发烧的症状则喻示着生命激情在体内的绽放和燃烧,更有甚者认为结核病对生命力的消耗与艺术创造力的迸发之间存在着一种隐晦的关联,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生理疾病被诗意化和浪漫化了;与结核病相类似,艾滋病也被人们加诸丰富的想象和不着边际的诠解,诸如艾滋病是侮慢人伦和破坏血统的行为所致,于是艾滋病患者被推上了道德法庭的被告席和审判台。那些在生理上尚没有死亡的患者,却在巨大而无形的道德谴责和舆论压力下,放弃治疗、陷入沉沦以致提前结束了生命,由此可见罹患传染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身边人乃至整个社会对传染病隐喻化,无辜的患者需要经受病魔和“隐喻”的双重摧残,换言之,隐喻是各类传染病患者死亡的主谋和杀手,“隐喻”后的传染病比真实的传染病更为狰狞与恐怖,这让桑塔格感到异常不安和极度愤懑,她坦承“无休止的隐喻将导致一个鬼魅般的影子世界存在,将使世界失去感觉和活力,”为此她以犀利的文化批评话语为武器,向愈演愈烈的疾病隐喻现象发出宣战。
隐喻是一个英语词汇,是指以一种事物暗喻另一种事物,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所理解的隐喻大体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人们对结核病、艾滋病、癌症等疾病之所以谈“病”色变,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社会上先天已经存在让人心寒胆怯的传染病,而在于患者面对疾病隐喻的施加而死于非命;二是传染病的病理或症状昭示着某种社会属性,这种社会属性又被人们用来作为某些相同属性事物的隐喻;三是传染病无疑会造成人类的死亡,而人们往往从政治角度和社会层面寻找死亡的根本原因,却忽略了传染病本身呈具的致死性功能;四是传染病的内涵边界应该是固定的,一俟疾病隐喻被揭露并遭到批判,以隐喻作为治理社会群体手段的运行方式将被终止,桑塔格在书中所探究的那些隐喻化现象大体都能从这四个角度得到合理解释。
蔑视陈见陋识的“思想护照”
通过对结核病和艾滋病隐喻化的深入抉发,桑塔格得出被隐喻的传染病患者生不如死、其精神痛苦远比病痛折磨更为致命的结论,毕竟道德评判使患者蒙羞受辱、丧失尊严,而这又与文明社会提倡的临终关怀南辕北辙。如何修正和改变传染病隐喻化这种状况?被称为“文学批评的帕格尼尼”的桑塔格在书中主张“反对文化阐释”,强调“揭露、批判、细究和穷尽”——这正是桑塔格精神面相的显著标识,也是这位致力于维护人类尊严的人文主义者坚执的道德信仰,只是,通过“揭露、批判、细究和穷尽”“使疾病远离这些意义、这些隐喻”有点过于理想化,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这都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和艰巨的任务。
如前所述,疾病隐喻化在西方由来已久,早在远古时代,传染病隐喻就与政治话语纠缠在一起,就与原始习俗密不可分,牧羊人放牧羊群时必然要面对羊群罹患的传染病,诊治的方法就是依靠神父祷告和巫师祈祝,这种天启式的信息传达机制是中世纪西方国家治理社会的重要手段之一,不仅拥有比较深厚的社会基础,而且形成了一整套事物隐喻化传统,这种基脉绵长的隐喻化传统在一些著名学者和作家那里得到充分印证,德国大哲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写到“对纯粹实践理性来说,激情无异于癌症,而且通常无药可医”,奥地利著名作家卡夫卡在《变形记》中描述“我的头和肺在我还不知晓的情况下就达成了一个协定”,英国诗人雪莱在看望患病中的同时期另一位英国诗人济慈时安慰道“痨病是一种偏爱像你一样妙笔生花的人的病”,这些圣哲先贤的形象表达和理性论述,汇聚成一座以疾病为主脉的浩瀚无垠的隐喻群山,据此桑塔格一方面认为如果没有隐喻,人类就可能失去思考的能力;另一方面坚决反对进入现代社会的人类继续使用传染病隐喻化表达范式。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桑塔格鲜明地提出那种对社会产生消极影响的传染病修辞方式,应当适时终结其历史使命;那种积弊甚深的传染病隐喻化现象,也该尽早地收场了,“让疾病成为疾病”,这无疑是全书的题旨和要义,也是为包括结核病、艾滋病、癌症在内的疾病正本清源所秉持的原则和恪守的立场。
作为美国当代极具影响力的文学家和评论家,苏珊·桑塔格目光敏锐、思维缜密、见解独到、言行优雅,其众多著述都使读者产生一种阅读的冲动和快感。《疾病的隐喻》虽然不是桑塔格的代表作,却是其成名作,正是这部蔑视陈见陋识的“思想护照”,以及蜚声文坛的《反对阐述》《激进意志的风格》《论摄影》等著述,奠定了其“美国最智能的女人”的学术地位,也助推其成为与西蒙·波伏娃、汉娜·阿伦特比肩齐名的当代西方文化界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疾病的隐喻》这本“小书”,是由“作为疾病的隐喻”和“关于艾滋病的隐喻”两篇文论合集而成的,是一部反对疾病隐喻的文化宣言,通过揭露和批驳围绕结核病、艾滋病和癌症而形成的系统性隐喻谱系,以求消除附着在传染病身上的政治考量和社会话语,其中寄寓着一位优秀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当写作“作为疾病的隐喻”这篇文论时,桑塔格自己正在罹受乳腺癌的困扰与煎熬,正在肿瘤医院与病魔进行扞拒和抗争,因而这两篇文论可以说是作者感同身受的结果,是作者有感而发的产物,强烈的经历感和在场感,使得这两篇文章的观点更加坚弥、可靠和精辟,也使她对疾病隐喻化派生的后果看得更加细微、深透和精准。桑塔格在书中简要论及了麻风病、梅毒、癌症等人类医学史上的重疾,详尽阐明了肺结核、艾滋病等既难以治愈又容易传染的顽疴,周密阐释了传染病隐喻化的演化逻辑和主要弊端,使传染病隐喻化被长期遮蔽的客观事实和盘托出。尽管西方一些学者将桑塔格与福柯进行比较和对照,但二人关于传染病的看法还是迥然有别的,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也对传染病做了抉发和诠释,但有些观点过于抽象和晦涩,对于普通读者而言犹如雾里看花;而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一书主题貌似专业化学术化,但在通达晓畅的行文中表达的思想似乎更为醒豁、鲜明和直接,易于为读者理解、接受和掌握。
还疾病以本来的面目
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桑塔格主要论述的是肺结核、艾滋病、癌症等疾病的隐喻化,但有一种传染病对于当下世人来说,隐喻后所带来的后果似乎更为可怕,这就是正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那些于不经意间地被动地患上新冠病毒的人可谓是时下最悲催的人,即便是已经治愈的新冠患者,在健康问题上其心理可能存有低人一等的感觉,事实上这绝非患者本人的问题,而是由隐喻化甚嚣尘上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正如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所说,“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为一种道德评判或者政治态度”。当然在现代医学还没有对新冠病毒得出科学结论之前,人们还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新冠病毒,于是由新冠病毒衍生的各种隐喻也就在所难免,特别是一些西方国家借机对中国新冠疫情加以隐喻化且不断升级,给新冠疫情溯源和防治带来了很大障碍与阻力。将任何传染病进行隐喻化或阴谋化,这是作为“美国公众的良心”的桑塔格所极力反对的,她要做的就是“将鬼魅般萦绕在疾病之上的那些隐喻影子进行彻底曝光,还疾病以本来的面目。” 我国清末民初的学者金松岑,在其所著《鹤舫中年政论》一书中主张“夫士,国之肝肾,夫士之言,国之声息也”;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资源、价值和发展》一书中强调:“知识分子是社会的守夜人。”桑塔格在权力博弈和资本竞争中以个人经验和价值判断发出独立的声音,成为底层社会的忠实守夜人,但遗憾的是,这样一颗充满仁爱之心和悲悯情怀的大脑,于2005年永远地停止了思考,而桑塔格终生反对的对传染病的隐喻目前还在世界范围内滋长与蔓延,这样的现状似乎是桑塔格的不幸:她只能以笔墨对非正义不公平的社会现象进行声讨挞伐,却没有能力去改变现实和救助患者。
历史反复证明,传染病对社会变迁的影响是深刻和迅猛的,消弭传染病或降低传染病的危害性,是任何一个时代都必须正视和破解的急切问题。在新冠肺炎疫情依旧汹涌张狂的当下,传染病的诡异行、未知性和突变性,的确给社会成员带来一定的恐慌,也在潜移默化中调整和重塑人们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正如桑塔格所说“任何起因不明、治疗无效的疾病,就容易为某种隐喻所覆盖,也容易改变人们的生活理念和社会治理模式”。作为一部影响广泛的经典文化批判著作,《疾病的隐喻》并未彻底否定和完全摒弃疾病隐喻,认为“适度的疾病隐喻有助于患者康复和洞悉个别人的不良动机。”承桑塔格的研判和高见,新冠病毒和其他传染病一样,已经拥有了自己的隐喻,但一些心怀叵测的人将这种隐喻加以夸大扭曲,希望籍此实现自己的目标或达到本国的目的。面对一些国家每天大幅攀升的新冠患者数字,我们唯有在观念上正确认识新冠病毒隐喻,才能在行为上从容应对新冠疫情,相信经过现代医学工作者的悉心专研,在并不久远的将来,新冠疫情将不再神秘莫测,届时关于它的种种隐喻也将灰飞烟灭。
( 作者系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兼职教授。)
作者:刘金祥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