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是中国传统文学与思想中一个永恒的母题,影响了当时及之后两千多年来无数的中国人,是中华文化、民族精神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内《庄子》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学者,陈引驰教授在复旦大学开设的“庄子精读”课历来是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本书即以课程讲义为基础,结合多年来研究成果,以文本为经,以广博的见识和精妙的理解为纬,可称是陈引驰教授《庄子》研究的全面总结,更是对《庄子》的一次经典呈现。
全书共九章。引言统说道家老庄,更通过对老子与庄子的关系和区别的讨论,阐明庄子的特殊之处。以下八章,第一章概述庄子其人、其书,第二至六章分别从《逍遥游》《秋水篇》《齐物论》《养生主》和《外篇》逐段讲解,选目与次序均精心设计,重在贯串与打通。第七章统讲《庄子》的美学观念,第八章讲《庄子》对后世的影响。全书统合,形成对《庄子》来源、其人其书本身,以及对后世影响的完整阐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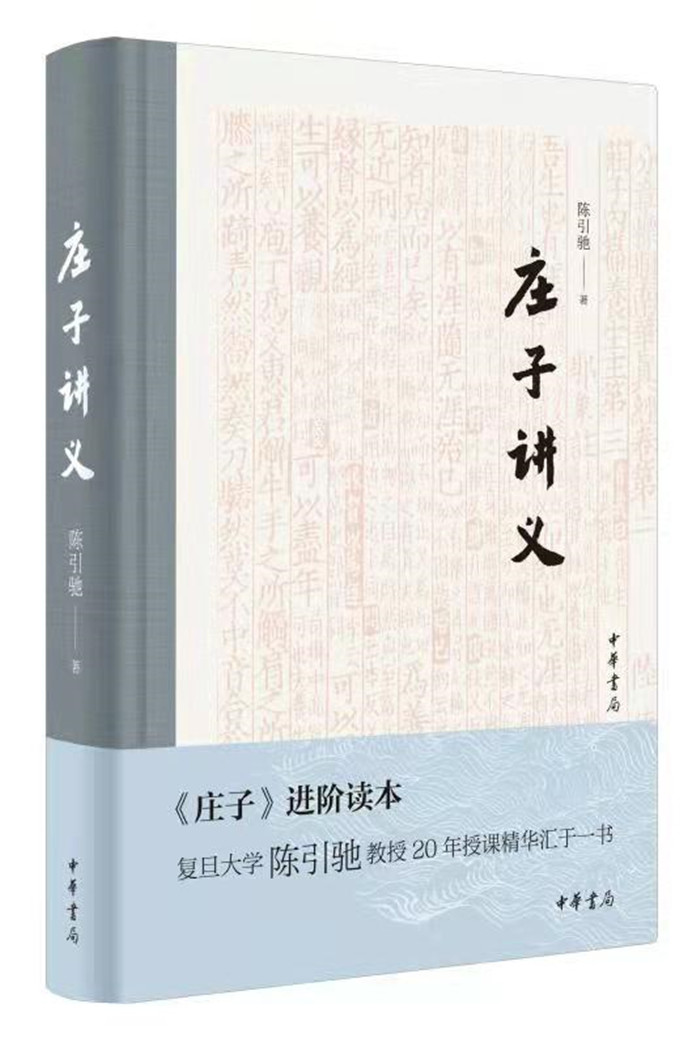
庄学对于死亡的达观,虽然具有甚高的境界,但远超常情之外,不是一时即可为人接受的。对于生命的关切是人类基本的冲动。这似乎是一个无法逾越的关口。
汉人对于生命的长生久视抱有强烈的企望,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对古典理性精神的反拨,对于长生法术的追求乃成一时风尚。这一点在文学中也有鲜明的表现。然而求仙之在现世难以应验,最终必然会引致对它的反省、疑惑。在企求破灭之后的失落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古诗十九首》里即充斥着生死之感,其最主要表达的就是人生有限的尖锐意识: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今日良宴会》)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回车驾言迈》)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
……
对此,古诗作者诉诸的法门是及时行乐、世间荣名等。这是一种执着生命的表现。在他们的视野中,死亡如果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不妨专注现世的生活;然而,这种专注恰恰是对于不在视野中心的死亡的强烈意识的证明。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对于庄子式的视死生为一体的观念,一定是不能理会的。
再后,因眷恋、执着于现世生命而对庄子的以理化情从而坦然面对生命的达观作出直接反对的有王羲之。
《兰亭集序》真伪曾有争论,然而似乎无论从书法史还是文本观念的角度,都没有充分的证据可推翻王羲之作为作者的地位。

兰亭会时在永和九年(353)春三月三日,众名士临水修禊,饮酒赋诗,将所作诗汇集后,王羲之作《兰亭集序》,时人比之石崇《金谷诗序》。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当那些名士们在四世纪的中叶,聚集在会稽山阴兰亭的“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之间时,“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他们“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相与“畅叙幽情”,“信可乐也”。一个“乐”字,突显了当时的氛围。然而,随后来临的是良辰美景难以久住的伤悲:“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岂不痛哉”!一个“痛”字,点明了此刻的情感陡转。以此看《兰亭集序》,大抵可认为其具有两层结构,即兰亭集会之乐以及由联想到快乐之不永而来的悲哀。
这在晋人生命意识敏感的背景下并不显得特殊,在山川美景及欣悦心情下,因深感这一切不能持久而骤然转向悲哀,古时作品中已往往可见。汉武帝刘彻的《秋风辞》就是典型,所谓“欢乐极兮哀情多”。而彼时人用以比拟《兰亭集序》的《金谷诗序》,也有类似的转折:在叙写众人饮宴于“清泉茂林”之间后,表达了“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世说新语·品藻》刘孝标注引)的伤感。孙绰因兰亭之会同时所作的《兰亭后序》也有类似的情形,他同样描画了兰亭周遭环境之美,“高岭千寻,长湖万顷”,记叙了诸名士“藉芳草,镜清流,览卉物,观鱼鸟”之乐,而后因时光之流逝而悲慨中来:“耀灵纵辔,急景西迈,乐与时会,悲亦系之,往复推移,新故相换,今日之迹,明复陈矣。”(《艺文类聚》卷四)
然而最引人瞩目的,是《兰亭集序》中对庄学生死观的直接否定:“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所谓“一死生”,见诸《庄子·德充符》“以死生为一条”及《庄子·大宗师》“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而“齐彭殇”,见《庄子·齐物论》“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
对于王羲之而言,生死之间有着截然的划界,这是一个无法解脱的困境,因而庄子寿夭生死一致之说是无法接受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态度与王羲之之天师道徒身份相关。王氏家族世代奉道,《晋书》卷八十《王凝之传》:“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同卷《王羲之传》载:“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许迈是当时有名的道士,晚岁与王羲之甚相得,《晋书》传云:“羲之造之,未尝不弥日忘归,相与为世外之交。”而在道教初期,相比较其他的精神传统之不同,最为根本的一点就是追求长生。葛洪《抱朴子》内篇《道意》云:“夫神仙之法,所以与俗人不同者,正以不老不死为贵耳。”在早期道教趋生避死观念之下,其视野中生与死的境界是断然不同的,所以庄子所谓两者“一体”或“一条”的观念,在道教徒王羲之必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这中间的不合,清乔松年即曾点到,以为《兰亭集序》与当时流行的庄学宗旨有别,其《萝蘼亭杂记》曰:“六朝谈名理,以老庄为宗,贵于齐死生,忘得丧。王逸少《兰亭序》谓‘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有惜时悲逝之意,非彼时之所贵也。”他并以此解释萧统《文选》之不取《兰亭集序》的缘由。乔氏之说,确属洞见。王瑶更进而言及王羲之的道教背景与该文的关系:“右军世事天师道,其雅好服食养性及不远千里之采药石,皆对于死生恐惧之表现,而欲求生命之延长也……《兰亭序》所申言兴怀者,本即此意。”
《世说新语》中有王羲之明确反对当时老庄玄谈的记载,而他的《杂帖》中更有直斥庄子之言。他称奉佛法者“荡涤尘垢,研遣滞虑,可谓尽矣,无以复加”,并称“吾所奉设教意正同,但为形迹小异耳”,而对于庄子之说则曰:“漆园比之,殊诞谩如下言也。”王羲之在当时名士奉庄甚烈的风气中之不以庄为然,是显见的。而在当时,庄学与道教的关系确实远远不像后来如李唐时代那样相与为一:毕竟《庄子》在当时人的心目中还是一部玄学要典而不是道经。据《隋书·经籍志》,道士之讲《庄》在隋时;而《庄子》成为《南华真经》更到唐玄宗天宝初年。即使在那时,还是有人对老庄道家与道教究竟有否关联表示怀疑,吴筠《玄纲论》便记载了有人对他的责问:“道之大旨莫先乎老庄,老庄之言不尚仙道,而先生何独贵乎仙者?”由此返观初期道教,更可体会其与道家之区别。至少在庄子看来,道教之希望长生久视实在是违逆自然的举动。《大宗师》表示了人作为天地自然的产儿当依循本分的意识:“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之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我相信,在庄子看来,道教追求人之永生的企望,实在与这里的“不祥之人”没有什么差别。
——摘自陈引驰《庄子讲义》,中华书局出版
作者:陈引驰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