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女性天才:生命、思想与言词”原创女性思想家传记丛书日前出版了玛格丽特·杜拉斯与西蒙娜·波伏瓦两部评传,分别由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黄荭与华东师范大学法语讲师沈珂执笔。在日前于上海朵云书院举办的题为“女性与写作:波伏瓦VS杜拉斯”的活动,袁筱一、毛尖、黄荭、沈珂四位嘉宾一同讨论了她们眼中的杜拉斯和波伏瓦。她们谈到杜拉斯冲击并鼓舞了她们的青春岁月,而波伏瓦为她们的女性知识分子生涯指明了方向。
许多人对波伏瓦的认识都离不开她的伴侣——哲学家萨特。长久以来,由于波伏瓦和萨特的亲密关系,人们经常对波伏瓦产生误解。“女萨特”“萨特的女人”这一类的说法也是专门针对波伏瓦的讽刺之一。当然,学界也普遍认同萨特对波伏瓦的深刻影响。对此,袁筱一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没有萨特的波伏瓦,她还是波伏瓦吗?”沈珂回应道,波伏瓦如果没有遇到萨特,她很难成为我们现在认识的真正意义上的Simone de Beauvoir。“波伏瓦不是生来的,她也是变成的。尤其在她的哲学表达当中,无论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还是对女性问题的阐述,一方面离不开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她对萨特哲学的拓展与丰富,这在她的几部哲学著述中都有体现。”
对于爱情之于波伏瓦有怎样的意义,沈珂也有自己的理解。她认为,爱情从来不是波伏瓦生命和写作当中的主旋律。她在美国遇到作家艾格林并且陷入爱河,但是当艾格林向她提出结婚的要求的时候,她毅然而然地回到了巴黎,回到了萨特身边。波伏瓦和萨特两人的关系已经远远超越了爱情,而成为智性的伙伴,每一次他们两个人成书、著作,其实都会成为各自第一个读者。无论是萨特对于波伏瓦,还是波伏瓦对于萨特,其实他们都在彼此交流,彼此给出意见,并成为彼此的第一个读者和评论者,与其说是夫妻,他们更像是彼此的灵魂伴侣。
如果说波伏瓦如袁筱一所说,是一位典型的学者,《第二性》的写作也是学者的写作,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写作,里面有着强大的推理过程,她无疑代表了理性的一面,同为女性作家的杜拉斯,象征的就是感性的一面。对于杜拉斯在国内的高知名度,毛尖笑言自己烦透她了。她提到,杜拉斯“写小说写专栏写剧本,玩先锋拍电影搞戏剧,把一个文艺青年能梦想到的事情,全部干了一遍,然而还不止这些。”整整一生,她夜以继日地恋爱,又高调参与政治,从1914年活到1996年,“她把我们十辈子才能做完的事情,用一辈子终结。”

活动现场
在毛尖看来,杜拉斯就像一本“青春教科书”,在她一生的写作中,都有着青春时期的激情与叛逆,她始终用叛逆少女的方式和这个世界撕扯、拥抱、分手、和解、决裂再握手。“杜拉斯说她可以同时拥有五十个情人当然是一种激进表达,但她锲而不舍的爱情生涯,的确有天神般的意志在其中。”
作为国内知名的杜拉斯研究专家,黄荭与杜拉斯结缘已久。“硕士论文做的是她,博士论文做的还是她,杜拉斯也让我的科研拿了一个‘大满贯’。用毛尖的话说,我在杜拉斯身上豪掷了四分之一个世纪。”黄荭笑言。“研究杜拉斯对我而言并不是枯坐寂寞无趣的事情,因为杜拉斯的写作是非常丰富的,她是一个触角特别丰富的作家,这也是我特别喜欢她的地方。”
以黄荭的理解,不少国内读者对杜拉斯存在误读,把杜拉斯一生的创作跟《情人》画上等号显得过于天真和轻率。实际上,杜拉斯不仅在写作上有追求,在政治上也有追求,作为法国知识界介入政治社会生活的积极分子,杜拉斯参加过抵抗运动、加入过法国共产党,游过行、卖过报、发过革命传单;作为文艺多面手,她既是作家,也是戏剧家、导演和专栏记者;作为热爱生活的模范,她热情好客,能做一手好菜,把家里打理得妥妥帖帖,花草照料得停停当当。但就像毛尖说的那样,杜拉斯一生的写作中,都有着青春时期的激情与叛逆,她始终用叛逆少女的方式和这个世界撕扯、拥抱、分手、和解、决裂再握手。
下面选摘毛尖为 《玛格丽特·杜拉斯:写作的暗房》一书所做的推荐序以飨读者。

推荐序
文 / 毛尖
喝完威士忌,杜拉斯写下一行字:杜拉斯,我烦透你了。
这也是我想对杜拉斯说的。这个没完没了的矮个子女人,我整个青春期不断地遭遇她,她在我的书架上有漫长的序列,她写小说写专栏写剧本,玩先锋拍电影搞戏剧,把一个文艺青年能梦想到的事情,全部干了一遍,然而还不止这些。整整一生,她夜以继日地恋爱恋爱恋爱,又高调高能地政治政治政治。从1914年活到1996年,真正“享”年82,她把我们十辈子才能做完的事情,用一辈子终结。
1992年,电影《情人》公映。尽管杜拉斯本人不认可这部电影,但毫无疑问《情人》让她成为超级明星、小资偶像。她的脸出现在各种时尚刊物上,我们在电影院看到她,在商场看到她,在飞机上看到她,临睡前一个电话,还听闺蜜感叹一句:哎呀,真希望等我老了,也有一个男人走过来对我说“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如此,杜拉斯挤走叶芝的《当你老了》,挤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之轻”,成为又积极又颓废的世纪末月亮。
抵抗杜拉斯的路上,我爱上加缪。再后来,我重返巴尔扎克和雨果,觉得他们俩,一人一句,就能把杜拉斯缴械。比如,雨果会说,人的心只容得下一定程度的绝望,海绵吸够了水,即使大海从它上面流过,也不能再给它增添一滴水。巴尔扎克接着总结,痛苦也有它的庄严,能够使人脱胎换骨。依傍着19世纪的两个男人,简直可以嘲笑杜拉斯:生活的痛苦,你还给写作,但写了一辈子,为什么一直没有脱胎换骨?
一辈子,她始终是个情人。一辈子,她始终用叛逆少女的语法和这个世界撕扯、拥抱、分手、和解、决裂再握手。她的人生主人公和小说主人公拥有共同的名字:情人。这个情人出生在加尔各答,出生在维也纳,出生在巴黎,出生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小镇,杜拉斯说她可以同时拥有五十个情人当然是一种激进表达,但她锲而不舍的爱情生涯,的确有天神般的意志在其中。她反复地爱,反复地受伤,反复地书写《战争笔记》中雷奥的故事,她把它写成《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再把它写成《伊甸影院》《情人》《中国北方的情人》,它是《琴声如诉》的题辞,也是《广岛之恋》的旋律。她写啊写,决意把全世界收入她的情爱宇宙,从她的第一个句子,到她生命终点的最后一句,她一直用酗酒的方式交出自己也灌醉别人,所以,当她说着,“即使在死后,我也能继续写作”,我们相信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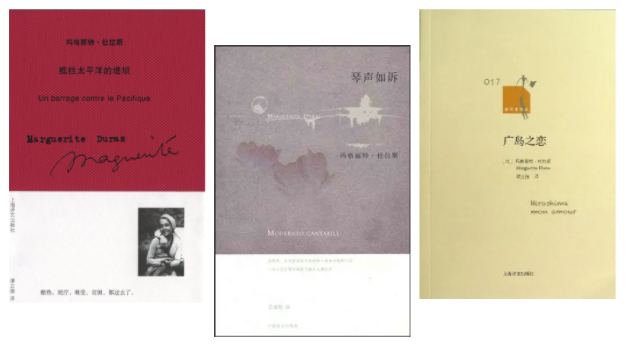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琴声如诉》《广岛之恋》中文版封面
至死不休,死了还要爱。在这个意义上,她当然拒绝脱胎换骨。她一生固执,从来没有赞美过别人对她作品的翻拍。一生,除了不断升级她的情人故事的版本,她没有修改过自己的身心。所以,有时候会突然觉得,大概,这就是杜拉斯的终极革命性。在现代主义风靡的时代,她在读者身上召唤出了涌动的情感潜流,人人都能和她的第一人称认同,她的湄公河往事也就成了全球的青春故事。
然后,黄荭出来。
黄荭的专业身份不用我介绍了,反正她就是全世界法语系都渴望拥有的那种教授。有一段时间,我们华师大外语学院院长袁筱一朝思暮想地想把她挖到上海来。权钱,黄荭都看不上,但大家知道黄荭是很牛的杜拉斯专家,将心比心,我们就准备策动一个特别好看特别有才也特别具有情人潜力的男人去南京大学拿黄荭。然而没等计划实施就有消息传来,黄荭已经有自己的王子,而且是不可能插足的那种。这样就和黄荭熟起来,知道她露台上的玛格丽特快开了,她去机场路上的柳树绽了新绿,她在厨房又炖了一锅腌笃鲜。和杜拉斯一样,她对生活中的一切都格外敏感;但她又和杜拉斯不同,黄荭从容,游刃有余,她和世界的关系是春花秋水,她享受她的孤独,并且把这种孤独变成灿灿莲花。像我们,进入法国文学,基本都沦为普鲁斯特、杜拉斯的手下败将,我们被他们弄昏了头清醒后,对他们又爱又恨,但身心惨淡。黄荭不是。黄荭爱杜拉斯,翻译杜拉斯,在她身上豪掷四分之一个世纪,硕士论文写她,博士论文依然和她缠斗,然后,她拿下杜拉斯。
《玛格丽特·杜拉斯:写作的暗房》因此不仅是一本杜拉斯传,黄荭在书中展示的是一次征服杜拉斯的过程。即便杜拉斯在世,也做不到对自己一生的脉络如此了然于胸。阅读此书,让我觉得,一个传记作者,就应该是传主的对手,而不是粉丝。
我们看杜拉斯,满纸情人,黄荭却说:其实不管是“印度支那”系列还是“印度”系列,爱情故事并非杜拉斯网络的结点和主题,爱情常常是表象和素材,主题一直都是写作,孜孜不倦对写作方式的探索。写作,怀着绝望写作,把一个故事重新写一遍,再写一遍。我们在杜拉斯的无数情人故事中看到的是情人的不同版本,黄荭看到的是,一个故事的另一种可能。她也因此能在杜拉斯杂花生树的一生中,钩沉出后者小说、电影和戏剧暗房里的理念:青春和专政、革命和阶级、殖民地和孤独。而黄荭最令人击节的地方是,所有这些理念,她不灌输,全部用杜拉斯自己的人生和文本来举证。比如,关于杜拉斯和电影,我一直不太能理解杜拉斯为什么要把电影推到那么反电影的地步,看了《暗房》,明白了。
......
而《暗房》也让我理解了,杜拉斯可以一代代“烦死”我们的主要原因。穷尽一生,她把“情人”变成了一个概念,一门理论,一种世界观。情人出没的地方,就有杜拉斯。
作者:傅小平 毛尖
责任编辑:张滢莹
来源:文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