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成为母亲这件事,英国作家蕾切尔·卡斯克用了整整一本书来描述,她的个人体验显然并非孤立,而是在许多国家、各种语言版本的女性受众中唤起了或多或少的共鸣:

蕾切尔·卡斯克《成为母亲》
有些人害怕,有些人渴望,还有些人游刃有余,让别人觉得她们对此事毫不在意。我的策略是否认,因此,等真做了母亲,我既惊讶又措手不及;我不知做母亲会带来何种后果,且有个毫无根据却很独特的想法:我随随便便就当上了母亲,这全拜某种比我强大的力量所赐,因此只能认命。
没有人天生就是一个母亲,在“成为母亲”的这条道路上,生活与心灵均需要建立新的平衡。对此,文学与艺术曾有过无穷无尽的展现。随着时代的发展,艺术作品中的母女关系、对“母亲”的阐释既在处在变化中,也仍有延续至今的内涵。作家张怡微是如何看待的?
文学中的“母职”
>>> 张怡微 <<<
近来我参加了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举办的“剧场与时代:聚焦女性成长的力量”对谈活动。活动的缘起是上话去年原创的一出新戏《房间》,由青年导演陈天然编剧、赵媚阳担任制作人,仅在去年10月演出过一场,如今进入剧本修改阶段,很快会再度上演。对谈前,其实我没有看过这部戏,也不认识主创。听说这部戏讨论的是母女关系与女性成长的话题,主办方希望我能谈谈艺术作品中的“母女关系”。

■ 《春潮》剧照
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在这两年,新时代“母职”成为了文学艺术界和社交媒体热议的话题,如电影《柔情史》《春潮》,英国作家蕾切尔·卡斯克的《成为母亲》、日本作家角田光代的《坡道上的家》等等,抛出的对于“母职”问题的反思,来自心理分析与性别社会学领域,集中讨论的包括“没有女人天生是母亲”、及克尽亲职的舆论压力等话题,都是社会文明的发展所带来的新思考。我的问题是,这些思考在文学艺术中的呈现应该是什么样的。《房间》的创作可能给了我们一点提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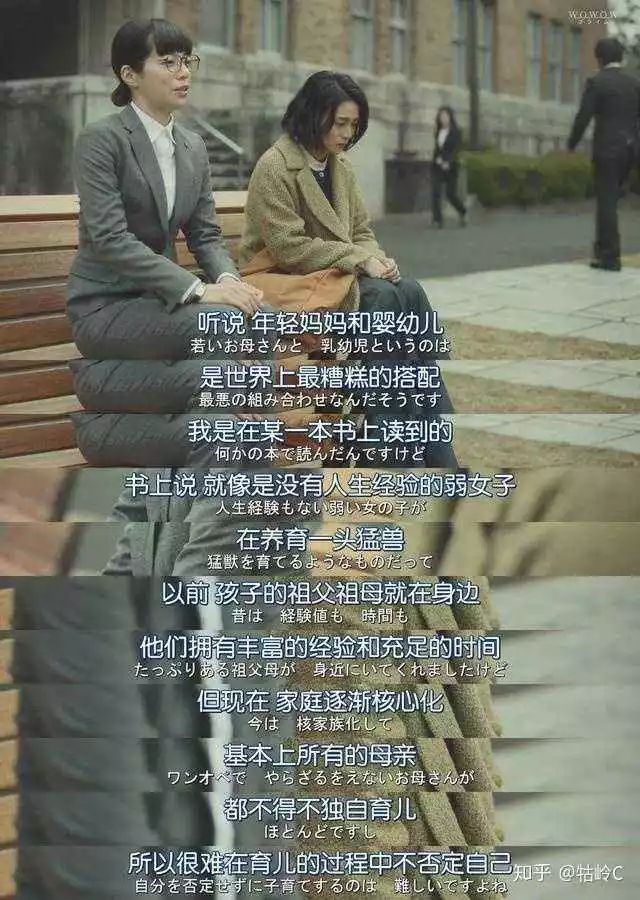
■ 《坡道上的家》剧照
故事将空间浓缩于“房间”,男性角色由同一名男演员扮演,两重设计都颇具女性主义色彩。全剧分为四幕,每一幕相隔七年。第一幕十七岁的女儿跟母亲一起去上坟,在千禧年破旧的旅社,母亲重遇初恋情人,她们有了第一次争执。第二幕女儿上了大学,母女在酒店,母亲告诉女儿父亲出轨,寻求女儿沟通。但母亲不想离婚,两人也不欢而散。

■ 2018年《房间》剧照
第三幕母亲在酒店斥责女儿退婚的行为,她们争论女人在三十岁走哪条路会更幸福。第四幕,母亲想要找她的初恋情人开始一段黄昏恋,而女儿年近四十,想要依靠人工授精得到一个孩子,寻求安稳的生活,她们再次发生冲突。关于女人的选择、爱情、事业、责任……从这趟旅程开始,这一对母女在往后二十一年间,在一个又一个陌生的房间里,一次又一次触及着这些看似没有答案的问题。
在创意写作的教学中,“母女关系”同样是一个经常被讨论的话题,由于我们的学员大多数是女性,母亲是距离创作者最近的女性楷模,被反复书写、批评和讨论,记得上学期有一份作业,有位同学写到了一位母亲一直在逃避当母亲的命运(好像总想辞职),女儿则显出超越年龄的成熟,在幽微的层面,母女的角色是错位的。在我们熟悉的小说作品中,无论是谭恩美的《喜福会》、王安忆的《长恨歌》、还是苏童的《妇女生活》,都将中国“母亲”的形象赋予了超越了母神“刻板印象”的复杂意涵。

■ 电影《喜福会》剧照
《喜福会》中的四位中国女性,从上世纪前半叶动荡的时局逃亡到美国旧金山,携带着各自的中国记忆,终于尘埃落定,聚首于喜福会,打着麻将,谈论往事。两代女性的情感割裂从外部看,是离散造成的语言、文化隔阂,这是一个常见的方法,为文学艺术创作反复利用,赋予隐喻的意涵。有一个细节很有趣,就是母亲对女儿发型的控制,被强化为童年的暴力回忆。后来许鞍华在电影《客途秋恨》中亦有影像化的搬演。
《客途秋恨》中的母亲有一个奇异的发型理论,“一家人”(包括母亲、姐妹)要烫一种头,这样的话,站出来一看就是一家人,很威风。女儿反驳母亲:“不是一个发型就不是一家人了吗?”母亲阴阳怪气回应:“也是啊,烫了一个发型你也不当我是一家人的。”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为,旧时代的“母亲”因为参与社会资源分配的能力不足,只得在私领域展现自己的控制力,但从另一方面而言,亲密关系中的控制力不仅存在于母女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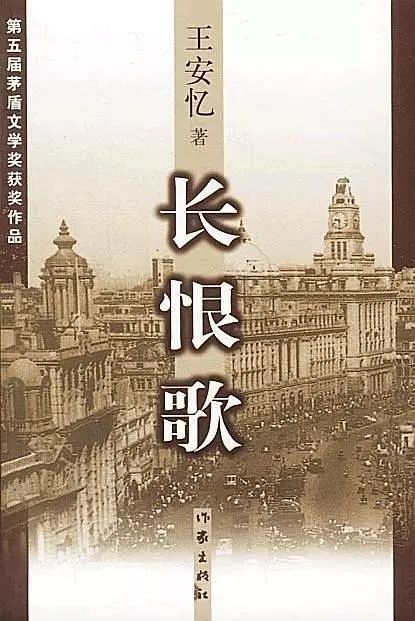
■ 《长恨歌》
将母亲还原为具有完整欲望的女人,本质上同样是对“母职”生理命运的挑战。如苏童的笔法就很有意思,《妇女生活》中三对母女离奇的相处模式凸显了性魅力的争斗。这非常动物性,男性作家将女性从司爱的女神形象中解放了出来,还原为暧昧的普通人。小说中的三代女性都反抗着自己的单亲母亲,但她们又不知觉地效仿着母亲的偏执,成为了和母亲很像的人,令虚构的故事有了宿命的意味。小说《长恨歌》也曾很直接地书写,“王琦瑶对女儿是有妒意的”,尽管王琦瑶比女儿漂亮很多。母亲和女儿谁更漂亮,虽是一个看似不重要的问题,却会生发出不同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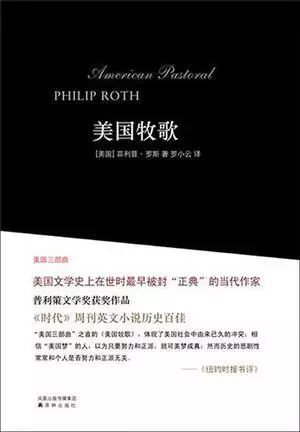
■ 菲利普·罗斯《美国牧歌》
菲利普·罗斯的《美国牧歌》中,生活看似完美的犹太企业家塞莫尔·利沃夫,因为家庭内部妻子与女儿的矛盾,卷入外部世界的纠纷。如果母亲是选美小姐,女儿却长相普通,从小就陷入到颓废与悲观中,这样的事应该怎么处理?《美国牧歌》显然提供了一个处理失败的可能性。
活动末尾的交流环节,许多听众都分享了自己与母亲的故事,有的人说着说着就哽咽了。还有一位女士,在会后问我,她今年48岁,女儿19岁,她想要离婚,她问我,未来会对女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又该怎么开口和成年以后的女儿谈论这件事,她还补充说,女儿并不优秀,是个普通人。我对这个描述很惊讶。但可见我们每个普通人都有困惑,特别需要互相启迪。
我们好像每天都在家庭内部沟通,但对真的需要沟通的事,又羞于启齿。我们没有正规的管道得以好好学习如何成为母亲,我们只能从虚构的小说里观看、批评和反思,完成并不完美的自我教育。这样的反思和“母职”天然的批判具有一个颇合情理的前提,即母亲可以不是一个完美的人(父亲也不是,我们也不是);爱不是每时每刻都带有完美救援的功能(也可能在润物无声中形成重压),也会迷茫,也会完全“不知道”。这都改变了人的命运,我们总希望,通过文学艺术传递心灵力量,能将一切改变得更好一些。
作者:张怡微
编辑:何晶
责任编辑:陆梅
*文学报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