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日后成为诺贝尔文学家得主的君特·格拉斯对中国读者来说还非常陌生。他应德国歌德学院之邀偕夫人首次访问中国,在北京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做讲座并朗读新作《比目鱼》,和冰心、王蒙、白桦、柯岩等中国作家在大使书房进行交流。此外,他还在使馆内举办了个人画展,但应邀去看画展的中国文化界人士,在当时很可能对这位德国作家一无所知。

如今,随着1980年根据格拉斯的小说《铁皮鼓》改编的电影获得奥斯卡奖、他的作品陆续引进出版,加之他于1999年获诺奖,格拉斯在中国的影响与日俱增。8月22日,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行的2019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宣布,该社将陆续推出新版《格拉斯文集》。该社还将推出由德语文学翻译家、资深版权代理蔡鸿君选编的《格拉斯读本》,收入格拉斯的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和部分美术作品。

电影《铁皮鼓》海报
01
抚今追昔,作为曾经“离格拉斯最近的中国人”,蔡鸿君感慨万千。格拉斯于1979年9月访问中国时,蔡鸿君还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德语系读大。他远远看到格拉斯在朗读《比目鱼》的部分章节,他根本听不明白这部原本就极难读懂的作品讲了什么,他只是去凑热闹。他那时根本想不到自己在此后三十多年里,还会有几十次机会见到格拉斯。作为格拉斯作品的中文译者,他有幸参加格拉斯的“72岁”和“80岁”两次生日庆典,还先后参加过格拉斯《我的世纪》等五部作品的翻译讨论会。这种翻译讨论会一般都持续三至五天,每天与格拉斯在一起的时间超过八个小时,可谓朝夕相处。

格拉斯(右)和德语文学翻译家、资深版权代理蔡鸿君
这得从蔡鸿君进入由鲁迅创办的《世界文学》杂志工作说起。大学毕业后,蔡鸿君换了两次工作,于1986年进入这家杂志当德语编辑。一年后,编辑部拟出“格拉斯专辑”,由他负责选编。专辑在当年第六期杂志上与读者见面。这是国内第一次以较大篇幅全面介绍格拉斯。其中除格拉斯论文学、格拉斯访问记、格拉斯小传、格拉斯的绘画艺术,以及中国学者的评论等外,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格拉斯的小说《猫与鼠》。蔡鸿君说:“这部小说是领导指定我和友人做翻译的。翻译时,我正巧接待了联邦德国赴北京参加毕希纳学术讨论会的代表团,其中有德国《当代戏剧》主编利什比特先生。他与格拉斯很熟。听说我正在翻译这部小说,他表示要把这个消息转告给格拉斯。我借机请他向格拉斯转交了一封信,请后者为中国读者写几句话,作为《猫与鼠》中译本的前言。”

《猫与鼠》漓江出版社
不久后,蔡鸿君收到回信。格拉斯在信中说:
我在撰写这部中篇小说时绝对不可能料到,这个我自以为过于德国式的题材,会在国外引起如此之多的兴趣。早已改变了这种看法的我非常高兴,中国读者现在也有机会熟悉我的这个带来死亡的猫与鼠的游戏。

格拉斯
1990年,蔡鸿君去德国留学。五年后的4月25日,他在德国法兰克福又见到了格拉斯,那是他首次公开朗读尚未正式出版的新作《辽阔的田野》(1995)。朗读结束后,他递上那本《世界文学》,请格拉斯在上面签名。格拉斯立刻认出他当年收到过这本样书,并且回忆了当时的愉快心情。“那时,我和太太任庆莉一起开始创业,把德国的图书版权代理到中国出版。作为格拉斯作品的中文版代理人,我们在1996年6月将他的‘但泽三部曲’《铁皮鼓》《猫与鼠》《狗年月》的中文简体字版权安排给漓江出版社。正因为此,在格拉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中国读者就非常幸运地读到格拉斯的书了。”
格拉斯的作品不无沉重。但他本人给蔡鸿君留下的多是轻松幽默的印象。1999年3月,他去参加《我的世纪》翻译讨论会。在三天时间里,他们10多个参会者,包括格拉斯夫妇都吃住在哥廷根的一家小旅馆,每天讨论文学。“格拉斯对所有译者都很客气和蔼,尤其是对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的新人更是体贴入微。他当时已经72岁了,却依旧终日不离烟斗。说到书里出现的一些经典老歌,他常常会轻声吟唱,尽管夫人乌特几次都说他‘跑调’。当谈到跳舞的章节时,擅长于此的格拉斯更是眉飞色舞:‘我个头矮小,年轻时,没有女士愿意和我一起跳舞。她们更喜欢那些个子高的活泼的男人。后来爆发了战争,这些男人最先被送去打仗了。这样我才有机会跳舞,熟能生巧!’。”

格拉斯和夫人乌特
在蔡鸿君的印象中,格拉斯还特别喜欢烹饪。据说最早参加类似讨论会的译者都曾有口福吃过他做的比目鱼。“提到一种烈性酒时,格拉斯对我说,这就像你们中国的茅台。他对访华期间看人表演用火点燃茅台记忆犹新,回德国后进中餐馆也会要一杯,还曾为孙子孙女模仿过。告别那天,我提出要给他寄一瓶茅台,他也没有客气,留下了地址。”
就在那次告别后大概半年,从瑞典文学院传来格拉斯获诺奖的消息。他的颁奖理由是,他在“语言和道德受到破坏的几十年”之后,为德国文学带来了新的开始,他在“清醒的黑暗的虚构故事中展示了历史遗忘的一面”。三年后,蔡鸿君曾为《格拉斯75周岁纪念文集》写过一篇题为《格拉斯说中文》的文章。里面这样写道:“他(格拉斯)那留着胡子、喜欢抽烟斗的形象,已经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可以断定,在他下一次访华时,肯定会在大街上就被他的读者们认出来。”遗憾的是,格拉斯考虑到年事已高不适合远行,他生前没能第二次来到中国。但他那些著名的作品,早已经像他的形象一样在中国读者中深入人心了。
02
事实上,格拉斯的作品,受世界各地读者的欢迎。而在他自己的祖国,他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作家。有人做过这样的表述:“全世界都在读他的书,惟独在德国,他受到敌视。”的确,在德国,格拉斯总是能够掀起激烈的争论,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毁誉参半,成为德国各种文化矛盾和政治势力交锋的话题。
2015年4月13日,87岁高龄的格拉斯于德国小城吕贝克的一家医院去世,他又一次成为德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话题”。而这一次,即使对他有过尖锐批评的德国媒体,亦是发表长文悼念。德国之声在文章中表示,“格拉斯一生打破禁忌。他的逝世令德国失去了一位斗士和最有影响力的声音之一。他将作为一位不屈服的作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他的积极参与、反抗精神以及自身的争议都对当今德国产生了影响。”
当时的德国外交部长斯泰因迈尔表示“非常悲痛”。时任德国社民党主席加布里尔说:“我们失去了一名伟大的作家,失去了一名为民主和和平而奋斗的战士。”许多德国网民在新闻网站留言,称“德国又失去一名伟大的时代先锋”,希望“君特·格拉斯安详入眠”。
这一看似悖谬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源于格拉斯发表于2006年的自传《剥洋葱》与其曾经发表的反对德国统一的言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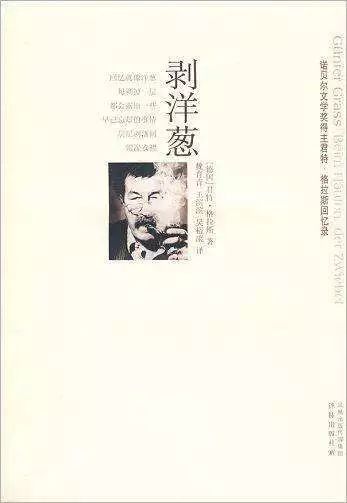
《剥洋葱》译林出版社出版
1995年,据二战结束已经50周年,战争的硝烟已经远去,政界与历史学家都有淡化战争的倾向。格拉斯却逆风而行,在《辽阔的原野》中用饱含忧患的历史哲学书写东德与西德,小说出版后,立刻引起轩然大波。赞扬者认为这是格拉斯批判德国社会和历史的集大成之作,批评者如评论家拉尼茨基,则公开在《明镜周刊》封面上以双手将这本书撕成两半来表达自己的批评。
而在《剥洋葱》里,格拉斯透露他曾在青年时代为纳粹党卫队效力,更是招致文学界、评论界、史学界和政坛人士的强烈批评,一时成为知识界的众矢之的。一些评论称,“道德法官”竟是“纳粹帮凶”,“格拉斯无疑是个伪君子”。
为此,格拉斯不得不为做出声明。当时刚刚过了80岁生日的格拉斯表示,正如其在自传中所说,他只是向军方提交了服役书,但最终加入党卫军并非出于个人意愿。声明中,格拉斯说,他当年是报名参加国防军,结果后来却被分配到武装党卫军,从军的主要原因是:“我一开始主要是为了出去,离开困境,离开家庭。我要结束它,因此我自愿报名了。这也是一桩奇怪的事。我报了名,大概是15岁,事后就把这事忘了。和我同年出生的人有许多都是这样的。我们参加了青年义务劳动军,一年之后,征兵令突然摆在了我的桌上。后来我大概是到了德累斯顿之后才发现那是武装党卫军。”
至于秘而不宣的原因,格拉斯说:“这事一直埋藏在我心底。为什么现在才说的原因,我也说不清。它始终缠绕着我,让我不得安宁。我以前觉得,自己作为作家和这个国家的公民现在所做的一切,和自己年轻时带有纳粹时代印记的行为针锋相对,这就足够了。所以过去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过。我是被征入党卫队特种作战部队的,没参与过任何犯罪行动,但自己一直觉得必须有朝一日在一个内涵较大的场合里对此予以说明。直到现在我克服了内心的障碍,终于拿起笔来撰写自传并将我的青年时代作为这本回忆录的主题时,这一机会才得以出现。这本传记记述了我12岁到32 岁这段年月的生涯,正是在这样一本书里我得以敞开自己的心扉。”
不同于一般的回忆录,《剥洋葱》不完全按照时间顺序回忆往事,而是将历史和现实生活拉近,将两个叙述层面交织在一起,格拉斯以一种“双螺旋”的叙述方式,以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织,试图向读者说明这段藏有秘密的青年时代是如何深深地影响了自己的写作及作家生涯的。以蔡鸿君的理解,《剥洋葱》可被视为开启格拉斯全部文学创作的一把钥匙,同时也让读者思考:如果没有这段曾被秘藏的“褐色”经历,是否会产生现在的格拉斯和“但泽三部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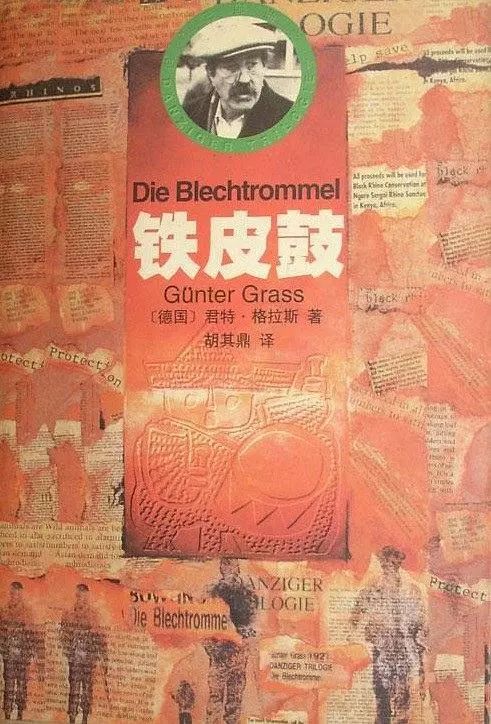
《铁皮鼓》 漓江出版社
难能可贵的是,格拉斯没有因为自己加入党卫队后没参与过犯罪行动就推卸责任。在小说《铁皮鼓》中,从3岁之后就不愿长大的奥斯卡说道:“我只是一个孩子,我不能为我所做的一切承担责任。”而格拉斯则以自己的生活与创作提醒人们担当责任,“切不可以为把所有的罪恶推给希特勒一个人就万事大吉”。
在接受德国节目主持人乌利希·魏克特的采访时,格拉斯反省道:自己参加党卫队,虽然没有做出有据可查的犯罪行为,但要是再年长二至三岁的话,他也完全有可能会陷入犯罪泥潭。“没有人敢保证自己会不参加进去,至少我不敢保证我自己。”
03
格拉斯的忏悔无疑是真诚的。但他时隔60多年后才说出真相,诚如作家沃尔特·科波夫斯基所质疑,这样的忏悔是不是来得“有点晚了”。有人甚至心存怀疑:他的忏悔,是不是在为自己“刷油漆”?
以德语文学研究专家孟钟捷的理解,格拉斯之所以不谈自己16岁时那段不光彩的经历,反过来反映了他作为个体的一种道德选择,即加入党卫军是一种耻辱,进而也反映了德国社会在看待纳粹历史时的坚定立场。“无数个如格拉斯那样战时有过糊涂之举而战后清醒认识到纳粹过去之恶的人,或许都曾对自己的历史讳莫若深,而对外却无比勇敢地站出来反省民族问题。尽管今天的人们可以指责他们掩盖了个体的罪恶,但他们此举又何尝不是一种带血的补偿呢?”
极而言之,很可能是青年时期这段经历,促使格拉斯对德国纳粹罪行进行彻底的反思。在为其自传所做的声明中,格拉斯还补充表示:“我知道那是耻辱,我也把它视为耻辱,60年来一直如此,并力图修得善果。它定义了我后来作为作家和公民的行为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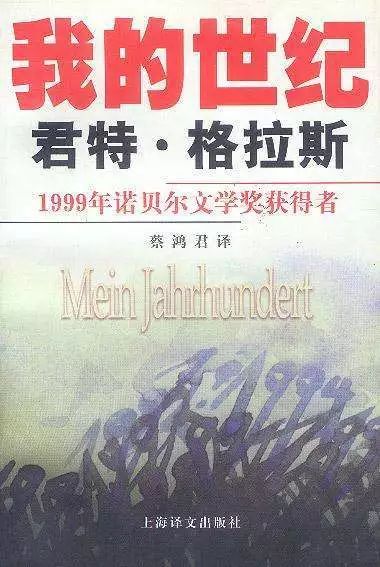
《我的世纪》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27年10月16日,格拉斯出生在现今波兰境内的格但斯克,那个地方又叫做但泽。有一段时间,由于犹太人的关系,德国人是被禁止前往当地的。日后在与萨尔曼·拉什迪交流时,格拉斯把但泽称之为为“一个失去的故乡”。“我俩一致认定,但泽属于一种遗失的东西,因此要求一种‘占有性’的写作,因为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可以通过作家的笔触,将已经消失的东西描摹得栩栩如生。”
经历过一段不长不短的“学徒期”后,1955年,格拉斯以诗歌初涉文坛,他的《睡梦中的百合》在南德广播电台举办的诗歌竞赛中获得了三等奖。与此同时,格拉斯开始创作剧本。此后,格拉斯才开始长篇小说创作之旅。1959年,格拉斯出版《铁皮鼓》,一举奠定了他在战后德国文坛的地位。《铁皮鼓》之于世界文学特别是德语文学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德国《时代报》做的一份“我们的经典”评选结果中可见一斑。共有5万名读者投票参与的该评选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铁皮鼓》,紧随其后的才是歌德的《浮士德》。而小说被拍成同名电影后,更使其获得了全球性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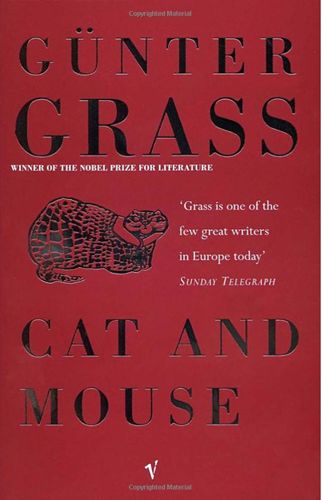
格拉斯作品《猫与鼠》德文版书影
此后,格拉斯一鼓作气,接连出版了长篇小说《猫与鼠》(1961)和《狗年月》(1963),他将这三部虽然在内容和故事情节上各自完全独立,但故事都发生在但泽的小说,命名为自己的“但泽三部曲”。三部曲的着眼点,都在清算二战期间德国纳粹给世界人民和德国自身带来的伤害。这在格拉斯此后创作的《比目鱼》(1977)《相聚在特尔各特》(1979)《母鼠》(1986)《铃蟾的叫声》(1992)《辽阔的原野》(1995)《我的世纪》(1999)等作品中一以贯之。
当然,格拉斯也写过一些相对轻松的作品。同为自传性作品,有别于《剥洋葱》,《盒式相机》(2008年)叙述的是家庭日常琐事,有很多作者本人和家人的生活细节,可以看作是用文字组成的格拉斯“家庭相册”。作者让子女们回忆早年的生活经历和他们眼中的父亲。据格拉斯证实,书里叙述的有些是真人真事,有些则是虚构,纯粹是为了表现作者的兴趣和爱好。书中那个盒式相机以独特的方式记录了这一切。它经历战火却幸存下来,“可以看见不存在的或者现在还没有出现的东西”,而且能够预知未来,这无疑为该书增添了魔幻色彩。

格拉斯和参加其作品翻译讨论会的译者们在一起
以蔡鸿君的理解,如果说格拉斯在《剥洋葱》里写了自己的历史,在《盒式相机》里写了他的家庭,那么《格林的词语》则是他“爱的表白”。格拉斯在这本书里只写了格林兄弟遭到撤销教职和驱除后,开始了编纂《德语词典》的工作。他重笔描述了编纂工作的艰巨,格林兄弟对编纂工作的执著等。同时,格拉斯对自己生活中的相似片段信手拈来,他所参与的重大政治活动和政治主张也不时地出现在字里行间。格拉斯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格林兄弟时代与自己的生活经历之间频繁穿越。至此,作家完成了自传三部曲,用“爱的表白”倾诉自己对德语语言的眷爱,似乎在为自己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画上句号。此后,媒体不约而同地将其称为格拉斯的告别之作。但实际上,创作力超强的格拉斯后来还出版了《在德国途中》《浮虫》 《勃兰特与格拉斯书信集》《我的六十年创作》。2015年3月28日,他还参加了《铁皮鼓》舞台剧的首演活动。而在去世前不久,格拉斯还完成了一部新作《关于无限》。这本书共184页,收入格拉斯生命最后时光创作的96篇诗歌和散文,以及65幅绘画作品。格拉斯以一种在三者之间换笔游戏的方式,抒发他对社会、历史、故人、往事、人生、老年等问题的思考、议论、感叹和讽刺。
概而言之,在格拉斯的身上,20世纪德国的命运已经变成了他必须去面对和清理的时代命运,也是他自身的命运。在这一点上,他丝毫不给德意志民族留情面。1991年,格拉斯接受《巴黎评论》采访,谈及自己对德国纳粹历史的持续关注。他说:“如果我是瑞典或瑞士作家,我可能会更加过分地胡搞,写几个笑话等等,但因为我是德国人,我不能这么做,我没有其他选择。”
因为是德国作家,格拉斯也别无选择地继承了德国文学的叙事传统。他的《铁皮鼓》假借17世纪德国作家格里美尔豪森的《痴儿西木历险记》的形式,在内里却充满了现代主义小说的荒诞感、黑色幽默和社会批判意识。
事实上,格拉斯的小说都有着黑色幽默和嬉闹夸张的特点,他经常以动物作为一本书的核心象征和意象来结构小说,比如:比目鱼、癞蛤蟆、猫、老鼠、狗、蜗牛、螃蟹等等,用以强调和比喻德国20世纪被遗忘和忽略的历史情境。

格拉斯在观看他的画作
正是为了拒绝遗忘,格拉斯自创一种将“往昔”“现今”“未来”合三为一的词“昔今未”。这代表了他的历史观,即过去不会就这样过去,吸取历史教训是为了悲剧不再重演。与此相应,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也从来不是所谓 “历史的创造与主宰者”、而是必须“承受与遭遇历史”的小人物,他要“从下往上来看历史”。换言之,在格拉斯看来,文学的职责与功能恰恰在于,记住这些所谓“历史的代价与牺牲品”,让历史的伤口永远保持新鲜。
或许,在格拉斯眼里,写作即是对试图冲淡一切的、不断流逝的时间的反抗。他这样理解特奥多·阿多诺“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的禁令。他说:“我们仍然在写作。我们靠心中的承担来写作。唯一的路径是我们可以绕着这句禁令走。无人有保持沉默的欲望和能力。引导迷路的德国走上正道,引导它从田园诗中,从迷茫的情感和思想中走出来,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作者:傅小平
编辑:李凌俊
责任编辑:陆梅
*文学报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