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大中文系教授团向上海师生送来阅读史
“说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生命史,是有道理的。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他的生命状态和变化,会在这个记录里留下痕迹。”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在《我的阅读史》里如是说。不同代际的阅读者的阅读倾向有什么区别?阅读对阅读者的生命轨迹起到了什么作用?这些问题如今都有了答案。前天(23日)下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礼堂再掀高潮,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戴锦华、贺桂梅与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教授毛尖以《文学经典与文学阅读》为题展开了深入的对谈。所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经典,一时代亦有一时代之文学阅读”。四位学者分别来自30年代、50年代与70年代,他们不同生命轨迹与阅读经验的碰撞不仅为现场听众提供了个性鲜明的“阅读样本”,也是对他们所成长的年代里的“历史大叙述”的别样解读。

▲(左起)毛尖、洪子诚、戴锦华、贺桂梅(摄/景柯庆)
30后洪子诚:万字论文三百个注解,严谨背后是细腻阅读人生
回想读博时,贺桂梅坦言很怕洪老师:“因为洪老师的文章总是特别严谨,差不多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有出处的。1998年他发表的一篇论文,也就一万多字的文章,有300多个注释,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要进入洪老师的世界是很难的事。”而当洪子诚将阅读里遇到的感动、眼泪、机遇、原初的读后感受都通过《我的阅读史》袒露出来后,贺桂梅却感受到了共鸣。
*《我的阅读史》《读作品记》都出自偶然?
“其实我的所有书都是没有一个计划的,往往是由一些偶然的因素引起,然后慢慢开始形成比较模糊的观念,《阅读史》也是一样。”被问及作品,洪子诚坦言《我的阅读史》来自一次偶然的约稿。巴金先生去世时,曾有报纸约他写纪念稿, 3000—4000字的《我的“巴金阅读史”》出笼,后来陆陆续续写成了一个系列。而《读作品记》则原是他在台湾清华大学授课时一个学期的讲课稿。当时台湾的同学对于中国当代文学非常不了解,因此只好通过与学生一起阅读文学作品的方式提炼出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贺桂梅注解:大约十年前,洪老和戴锦华等学生朋友一起交流读书心得,当时戴锦华提议一人写一篇关于阅读经验的文章,结果提议者没写出来,洪老师反而写出来了。

▲洪子诚这次来笑称找到了“对付”毛尖提问的方法,就是不回答她的问题,讲自己准备的题目
*令人流眼泪的作品未必是佳作?因拉赫美托夫磨炼身心
毛尖谈自己阅读《我的阅读史》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文中写到的几次眼泪。五十年代,不到二十岁的洪子诚第一次阅读巴金的《家》,看到鸣凤投湖那一段时躲在角落里痛哭;六十年代读契科夫时,则感到了一股强烈的忧伤感;八十年代,他读了《鼠疫》《局外人》再一次留泪。

▲洪子诚的两部阅读史作品《我的阅读史》《读作品记》
谈及这个话题,洪子诚对70年阅读中时常流泪还有点羞涩,但坦言:令人流泪的作品未必是很好的作品,好的作品也未必会使你感动得流泪。中学时参加剧团演出,即使是那些艺术成就不是很高的剧本里最样板化的情节与人物,也令他深受感动;七十年代带着纸巾去看越剧《红楼梦》,确实也是部好作品,自己却怎么都哭不出来,为此深感羞愧。戴锦华分享了类似的经历,当年宣传“带着棉被去看的”《卖花姑娘》也没用成功地让她留下眼泪。她分析道,大众文化、通俗文艺的催泪机制是一种机械的生物反应装置,而严肃的文学作品中的悲情场景往往是教人直面惨淡的人生,用高尔基的表述则是“直面深渊而不晕眩”,而“直面深渊而不晕眩”的审美对我们抵御大众文化的催泪机制是有很大帮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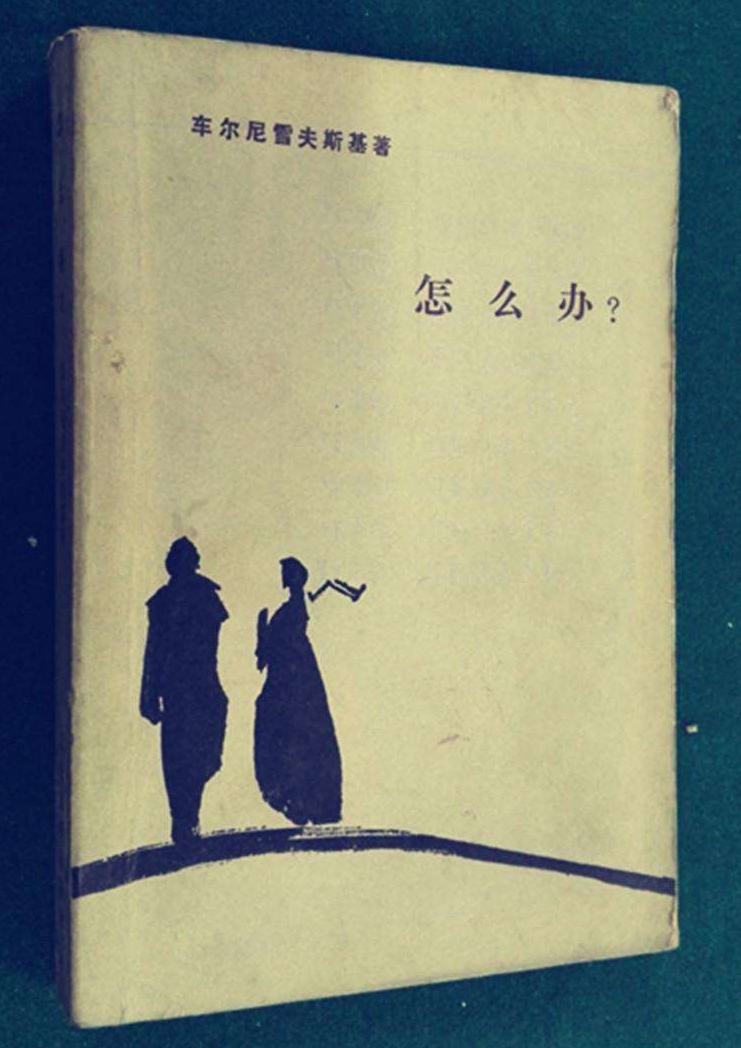
▲拉赫美托夫主动放弃优越生活,为磨炼革命意志睡 “钉毯”,激励无数学生争相模仿。
虽然二人相隔20年,巧合的是洪子诚与戴锦华竟然因为同一个小说形象——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中的拉赫美托夫做过不少傻事。洪子诚曾在寒冷的冬天洗完冷水澡穿着拖鞋跑回宿舍,到宿舍时头发都冻成了冰块;戴锦华坚持熬夜测试自己可以多久不睡,甚至在手臂上用炭火烫出一道痕迹。但这在当时并没有人嘲笑,“因为同样的经历与文化环境使同学们和我分享着一样的情感结构。”
50后戴锦华:庞杂无序的阅读造就了我们这一代人
这周一再一次坐在讲堂里听洪子诚演讲俄苏问学时,戴锦华才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除了严谨地治学风格与学科性的治学方法之外,老师的学术不可效仿的重要原因就是始终保持着原初读者的状态进行广泛而大量的阅读,这也是自己与他的区别,也是“洪老师以一己之力使当代中国文学研究成为一个学科,使当代中国文学史成为可能,使关于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成为可能”
*纯洁的趣味与高度去阅读,还是求答案地阅读?
戴锦华坦言,当下的学生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就是他们只把文学作品作为学术对象,然后带着解决某个特殊命题的任务去阅读;稍微好一点的学生虽然也是文学的读者,但他们往往只愿意读小说。但洪老师是一个毕生保持着读诗、读小说的阅读者,所以即使是在他的《阅读史》等带有散文随笔性质的作品,也具有这么高的思想含量。“因此,这几十年来洪老师作为我的老师,我还能跟他有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因为我们经常交流对阅读的体会。”而在书写阅读史时,戴锦华认为洪子诚始终保持着一种诚实的、同时又是极端严谨的态度面对自己、面对历史、处理自己的历史经验。他写自己流泪的时刻,不是为了艺术烘托,也不是自恋式自我表达,而是他为哪一本书的哪一个角色、哪一个故事流泪这件事本身就是某种时代的课本,或者时代痕迹。可以说洪子诚正是以这些为基础、为前提、为方法去处理学科,处理提出的问题的。

▲毛尖称戴锦华是“少女戴锦华”,她的文字有一种悬浮感
在这个意义上,戴锦华表示自己和洪子诚之间很重要的区别就是洪子诚是保持着纯洁的趣味与高度进行大量阅读的,而自己则会阅读所有涉及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的著作。
*很晚才读《钢炼》?50后的阅读顺序无法再现
戴锦华常说自己“有着一条精英主义的大尾巴”:“我可是阅读纯文学的,我可是拥抱高雅艺术的,我可是极端有教养的,我可是听斯特拉文斯基,听拉赫玛尼诺夫的,我可是阅读普宁长大的”,洪子诚却戳穿她:“她的性格、爱好中,本就有亲近‘大众文化’的成分……一个自幼 ‘大众’,也由精致、‘高级’文化(许多是她所说的‘十九世纪的幽灵’)所喂养过人对比中可能更会在内心形成难以摧毁的‘文化等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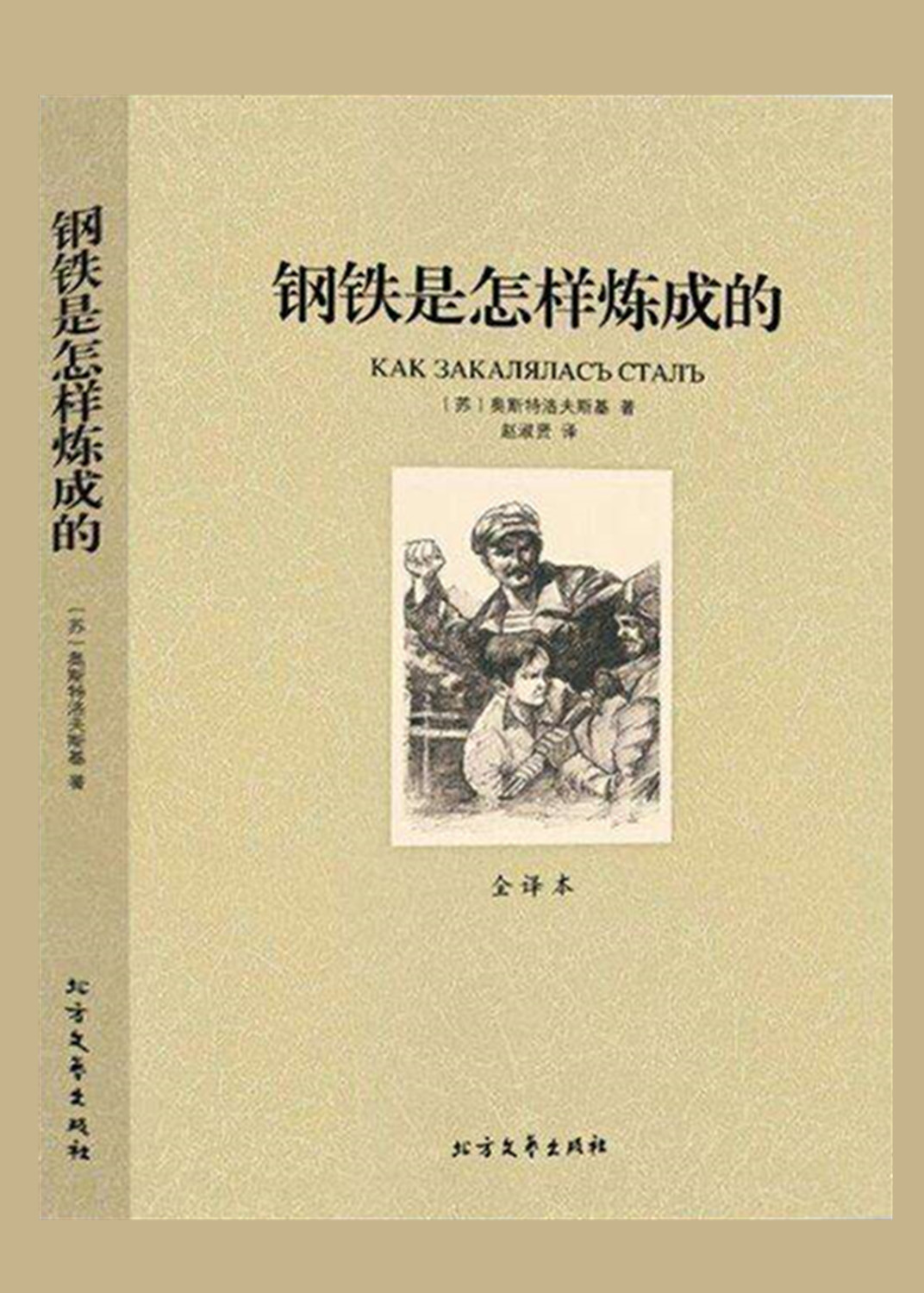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这时戴锦华才唤起了自己在60年代的阅读记忆,当时没有什么适合她读的书籍,她翻遍了家里书架上剩下的全部书籍。她读完了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的全部教材、读完了各种马克思主义初级读本、读完了《宇宙起源》……“但是只有一本书我一直没有读,直到很晚很晚才爱上了那本书。因为那本书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我原来一直以为是本讲冶金的书,一点不跟大家开玩笑。当时我读完那本书后,我父母还很惊讶,认为我读不懂。直到我清晰地说出保尔·柯察金的哥哥叫阿尔青·柯察金后,他们就觉得我真的懂了。”
戴锦华感叹道:“我们这一代人的阅读大概是非常奇特的,不是按照文学史,也没有按照对文学的追求,我今天很感谢这种经验,因为我觉得这种庞杂造就了我,造就了我们这一代人。虽然我们永远难以抵达洪老师他们的高度,但是我们也是别人不可以重现的。”
从文艺青年到专业学者:阅读史是70后贺桂梅的精神谱系
毛尖称贺桂梅为“70后的骄傲”,言其身上既有70年代人身上少见的强烈情感,又有“罗丹那样工作的工匠精神”。谈起阅读经验,贺桂梅首先指出欧洲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文学阅读成为一个普遍的、塑造人文理想的行为,可以说,阅读是自我教育、自我培养和自我境界提升的过程。当人们读文学作品时,会投入自己的情感,因此反思个人和一代人的阅读经验,不仅是对文学史的考察角度,也是对人们精神谱系的考察。
*《约翰·克里斯朵夫》曾是枕边书,阅读史是自我的知识考古学
由于父亲是一名乡村知识分子,所以贺桂梅最早的文学启蒙是古典文学的阅读,四岁的时候她就开始被父亲要求读《千家诗》了。但真正开始自认为是一个文学青年,是在她初中的时候。那时是1982年,文学的黄金时代,周围的老师、同学也都是文艺青年。她开始读司汤达的《红与黑》、读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也开始读屠格涅夫的散文、泰戈尔的诗,当代里也读朦胧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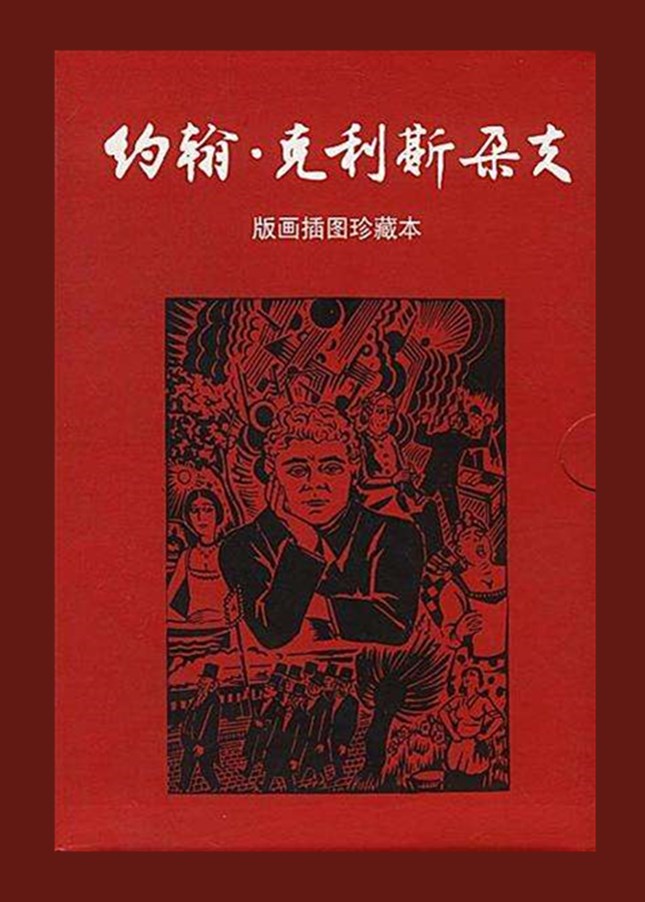
“有很长一段时间,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是我的枕边书。我拿着那本书,就好像是有一种神奇的作用,能让我镇定下来。这本书甚至被我带进北大。”
回忆当时青春期的阅读,她发现当时喜欢那些书,是因为能在书里看见自己或者看到自己想成为的样子;后来进入专业学习后,再看书第一反应就是要用什么理论去解读了。“我觉得文学阅读很大地塑造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它告诉我什么是好的情感,什么是好的人心,我成为今天这个样子,跟我的阅读关系非常密切的。所以我才说我们关于自己的阅读史的一个考察,是一个关于自我的知识考古学。”
*专业阅读后否定之否定的转变,要像里尔克一样化身万物
读研时,因为曾被老师说过灵性不足,贺桂梅更加拼命地学习学术规范、学习怎么写论文、学习怎么做注释做论证,学习怎么进行专业化的阅读而不是当初文艺青年的爱好式阅读,并安慰自己要“带着镣铐跳舞”。后来比较熟练之后,这个镣铐就不存在了,她可以把镣铐耍得很顺溜。但随着进入到专业的程度越深,她惊愕地发现专业阅读总让自己站在外部世界而不是进入文本。

▲70年的贺桂梅因为是洪老的入室弟子,所以常常被调侃是“萝卜虽小,长在辈上”
于是这些年她进入“否定之否定”,想做到把这种爱好的阅读和专业研究结合起来。她从冯至写的《里尔克》中获得了启发:“我们常听人说,这不是诗的材料,这不能入诗,但是里尔克回答,没有一事一物不能入诗,只要它是真实的存在者;一般人说,诗需要的是情感,但是里尔克说,情感是我们早已有了的,我们需要的是经验:这样的经验,像是佛家弟子,化身万物,尝遍众生的苦恼一般。”
从此之后,她在阅读时开始把自己放进去。“这些年来,我重新做冯至、柳青、丁玲、甚至是毛泽东诗词的研究,会把自己放空去体验,而且我知道了我们可以通过阅读,通过思考去不断地提升自己,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这些体验让我很感动很欣喜。”
70后阅读史的另一面向:受俄苏“光明正大”滋养的毛尖
阅读经验,不仅有代际的差异,有时区域差异会更大,同样是70年出生的毛尖,在宁波与上海成长,从湖北的农村进了北大的贺桂梅回忆:“虽然是同年,但总觉得她比我大很多,因为她是88级,我是90级,我入学时她已经颇有名气了。”这次活动由于北大教授团主场,毛尖自称“我基本上是打酱油的,我要给他们递话筒”,但当开始分享阅读经验时,她依然是那个舌灿莲花的才女。

▲毛尖作为主持人,这次依旧相当犀利,引得几位嘉宾纷纷向洪老学习先回避话题
*70后的文学观是天空与大地,80.90后的文学观是地平线
毛尖读中学时,教英文的老师大都是俄语专业转业,她至今还记得普希金的一首《我曾经爱过你》:“我曾经爱过你:爱情/也许在我的心灵里还没有完全消亡/但愿它不会再打扰你/我也不想再使你难过悲伤。我曾经默默无语/毫无指望地爱过你/我既忍受着羞怯/又忍受着嫉妒的折磨/我曾经那样真诚、那样温柔地爱过你/但愿上帝保佑你。”这首诗写出了诗人的深情,也写出了一种无私奉献的胸怀。但到了大学,兹维塔耶娃的诗歌开始流行,风格发生了巨变,诗人们不再言说希望“另一个人也会像我一样地爱你”,而是宣誓“要把你从天空从大地那里夺回来”,“我要一决雌雄把你夺回来”。
回想当时的文风变化,毛尖觉得贺桂梅的“知识考古学”的界定一点没错,确实从中学到大学,她所接受的美学、情感方式、修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直到听过洪子诚的关于俄苏文学的讲座,她突然又觉得这种从默默祝福到一决雌雄的转变背后,一直贯穿着俄罗斯文学的一种“光明正大”的逻辑。“我觉得我们青春期时世界观非常辽阔明媚,就像天空大地一样,但到了80年代甚至是更后面的90年代,天空大地的意象开始消失,视线是集中在地平线上的。”

▲普希金、兹维塔耶娃
*直言莎士比亚是全能的,阅读能从遇挫中回归正途
听众提问环节,被问及最喜欢的一本书或是作家时,其他学者都有点难以抉择,但毛尖非常坚定干脆地回答:“那一定是莎士比亚。特别是当我受到挫折的时候,我都会回到莎士比亚那里,因为他永远能提供把我又拉回到正常状态的能力。”
虽然常被戴锦华说看烂剧,但其实她对电视剧的喜好也是受莎士比亚影响,她喜欢《权力的游戏》就是因为它很有莎士比亚的艺术感,而她讨厌偶像剧也是因为偶像剧里一点莎士比亚感都没有。“莎士比亚在任何时候是全能的,它可以用来解释我对人生的所有的好感,也可以解释我对人生的所有的那些失望,特别是他还能提供一种人生的升华感,真正的为人感,可以把我重新可以组装起来。”
阅读史在学科研究之外是否还有意义呢?戴锦华在访谈中表达了对阅读的共享性的担忧,洪子诚的一次尝试也向我们展示了代际差异的障碍:他曾因一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漫画作品匿名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却被大学生认为“写得挺好,但什么都不懂”……由此可见,从跨代际交流的角度来看,阅读史的写作非常重要。如《我的阅读史》里洪子诚表达的自己的期望:“就可能给过去干涩的文字添加一点水分,一点情感,也有可能收缩评价的尺度,将它降低到个别的感受和认知的范围,个人的感受的价值当然不能和那种代言式的叙述,那些宏大叙事相提并论,但也可以为一些有差异的,有的看来是无关紧要的小碎片留出表达的空间。”
作者:夏佳丽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李念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