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生中总会与药打交道,但真的了解它吗?药从哪里来?安全性如何保障?如何治愈我们?了解新药诞生背后的故事,才能读懂我们身体的健康密码,新药研发一线的科学家,带你重温人类挑战疾病的动人时刻。
在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中,平均每五人就有一个糖尿病患者。我国每年宫颈癌新发病例约9.89万例,且呈现年龄年轻化趋势。HPV疫苗的主要发明人之一原来是中国人……这是一本写给大众的医药科普读本,兼具专业性和趣味性,结合最新的数据,配以生动的故事,让严肃的医药知识不再枯燥,让有趣的人文故事更加真实。
“后抗生素灾难”年代,中国制药人应该有何担当?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之间该如何平衡?本书作者梁贵柏常年坚守研发一线,具备极高的学术素养,严谨的科学精神和丰富的从业经验,他分别从研发者和患者的角度出发,详细叙述了新药研发过程中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该书从一位一线科学家的专业视角出发,讲述了十余种对人类健康产生深刻影响的新药的故事。从广为人知的降压药,到如今备受热议的宫颈癌疫苗,从价格一度令人瞠目结舌的乙肝疫苗,到有望对抗多种癌症的抗癌药物,新药研发的历史也是人类对抗疾病的斗争史,该书以科学的态度、严谨的逻辑,再现了药物研发过程中的“黑天鹅”与“灰犀牛”。
这是一本深蕴人文关怀的药物发展史,帮助你理性看待疾病,多一点思考,少一分恐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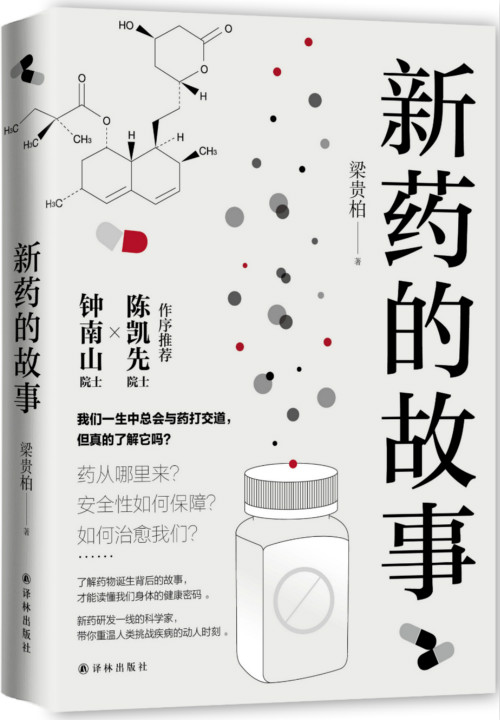
《新药的故事》
梁贵柏 著
译林出版社出版
2011年4月,美国南加州59岁的凯瑟琳女士得知自己被确诊为恶性黑色素瘤晚期时,感觉就像是听到了自己的“死亡判决”。手术和化疗之后,她的病情并不见好转,反而体重锐减,行动困难,不得不依靠轮椅生活。2012年下半年,凯瑟琳成为默沙东PD—1抗体药物—帕博利珠单抗(Pembrolizumab,商品名Keytruda)临床试验的受试者之一,开始在医院接受试验性治疗。
转机出现了,除了自我感觉和精神状态的明显改善之外,凯瑟琳的体重和气力也逐渐恢复,渐渐不再需要轮椅了。影像学检查显示,凯瑟琳体内已扩散的肿瘤大部分都稳定下来,其中一些正在缩小,还有一些甚至已经完全消失了!
在默沙东的帕博利珠单抗临床试验中,像凯瑟琳女士这样的故事还有不少。根据美国癌症学会提供的数据,美国每年大约有7.6万人被确诊为恶性黑色素瘤患者,每年因此而死亡的人数大约是1万人。在此之前,绝大多数晚期患者经确诊后生命持续不超过1年。2017年发表的一项临床试验数据1显示,在655例接受帕博利珠单抗治疗的患者中,105例(16.0%)在中位随访43个月后达到完全响应(Complete response,简称CR)。在数据截止时,92名患者(87.6%)有完全响应,中位随访时间为30个月。14名(13.3%)患者继续接受中位治疗40个月。91例患者(86.7%)停用帕博利珠单抗,其中67例(63.8%)在没有接受进一步抗癌治疗的情况下继续观察。所有105名患者在观察到完全响应后的24个月无病生存率为90.9%,其中67名完全响应患者在停用帕博利珠单抗后的24个月无病生存率为89.9%,疗效十分显著。
对于那些正在与病魔顽强抗争的恶性黑色素瘤患者,以及相关癌症的患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好消息,一道希望的曙光;对于那些工作在抗癌药物研究第一线的专家与学者来说,这是癌症免疫治疗的又一次突破性进展,是业界同行们经过多年不懈的艰苦努力而达到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库里医生: 肿瘤免疫疗法之父
肿瘤免疫疗法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早在1891年,也就是医学界对人体免疫系统刚刚有了初步认识之后不久,美国医生威廉·库里(William Coley)就最先尝试了肿瘤的免疫疗法。
库里当时是纽约肿瘤医院的外科医生,在查阅医院记录时,他发现了1例奇特的肉瘤病例,患者弗里德·斯坦的肿瘤在丹毒(即化脓性链球菌)感染高烧后消失了。这引起了库里的兴趣,并驱使他找到以前类似的癌症治疗病例,结果发现包括巴斯德在内的其他几位医学先驱也记录了丹毒感染与癌症消退相吻合的观察结果。
库里医生认为,这很有可能是因为细菌感染激发了患者自身的免疫反应,而免疫细胞在杀死细菌的同时,也杀死了癌细胞,帮助患者得到更好的恢复。于是,勇于创新的库里医生开始尝试给他的癌症病人直接注射链球菌,人为地造成感染,后来因为造成感染而带来的严重副作用,他转而使用两种灭活细菌,即化脓性链球菌和沙雷灵杆菌制成的疫苗,被称为“库里毒素”。库里医生把他的工作成果作为一个系列的案例公布,而不是系统的临床研究报告,使同行们很难解读。美国癌症协会当时的报告称:“需要做更多的研究,才能确定这种治疗方法对癌症患者有何益处。”英国癌症研究机构则表示:“现有的科学证据并不支持‘库里毒素’可以治疗或预防癌症的说法”,以此作为替代治疗方法有可能会严重危害癌症患者的健康。
100多年过去了,库里医生这种大胆且不无风险的肿瘤免疫疗法除了个别的成功病例之外,对大多数癌症患者收效甚微,根本无法大规模推广。但是,肿瘤免疫疗法这个新概念却在医药学基础研究领域里获得了同行的广泛关注。1953年,库里医生的女儿海伦创立了非营利性的肿瘤研究所,进一步推动肿瘤免疫学的基础研究,并于1975年设立了一年一度的“库里基础和肿瘤免疫学杰出研究奖”。第一批获奖者是一个由16位科学家组成的名叫“癌症免疫学奠基人”的团队,而库里医生则被誉为“肿瘤免疫治疗之父”。
免疫系统: 坚决清除入侵者
免疫系统对于人体健康是至关重要的,免疫细胞无时无刻不在搜索着身体的每一个角落,及时有效地清除各种对自身有害的外来入侵物,这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
每天,我们都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大量的细菌、病毒等病原体和各种其他污染源,是免疫系统把它们一一识别出来,然后“扫地出门”。只有在我们自身的抵抗力下降时,某些“入侵者”才有可能突破第一道防线,偶尔露一下“狰狞的面目”,给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但随之引发的免疫反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能够及时地、有针对性地实施反击,清除入侵之敌,恢复人体健康。而且免疫系统还有长期(甚至终身)的“记忆力”,使这些入侵者的下一次企图无法得逞(这就是疫苗的原理)。
这个强大的防御体系的关键是它的识别系统,只有准确无误地分清了敌友,才能有效地打击入侵者,保护自身的健康。在人类的生存环境里,入侵者种类繁多,面目各异,所以人体免疫系统也相应地进化出了一整套相当复杂但极其有效的识别系统,像一面巨大的“照妖镜”,让各类入侵者无处藏身。
然而,人体免疫系统的“照妖镜”再强大,还是会有狡猾的“漏网之鱼”。不断变异中的原始癌细胞就有可能产生出能逃避免疫系统识别的“异形”,在“照妖镜”的死角里潜滋暗长,直至在人体内建立“根据地”,成为恶性肿瘤,随之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最终耗尽患者的生命。
漏网之鱼: 癌细胞误打误撞走“后门”
现在流行的医学理论认为,人的身体里几乎每时每刻都会有零星的原始癌细胞产生,但它们大多成不了气候,因为人体免疫系统能有效地识别这些原始的癌细胞,并及时地将它们清除掉。
免疫系统之所以能识别癌细胞,是因为癌细胞表面有区别于正常人体细胞的特征性标记分子。早期的癌症免疫疗法,采用非选择性的方法(比如库里医生的人为细菌感染)来增强人体的免疫反应,所以效果并不理想。后来科学家们采用癌细胞表面的特征性标记分子作为人工抗原,培养有针对性的抗体,再注射给患者,疗效有一定的提高,但仍旧离期望值甚远。为什么呢?最近的研究显示,有些癌细胞找到了躲避免疫系统搜捕的“后门”。
本应“铁面无私”的免疫系统怎么也会“开后门”呢?这就要回到前面说过的免疫识别了。免疫系统只有准确无误地分清了敌友,才能有效地打击入侵者,保护自身的健康。但是再精准的识别系统也有犯错误的时候,一旦出现了错误,“不分敌友,认友为敌”,其结果就是“自身免疫性疾病”(Autoimmune diseases)。所谓自身免疫性疾病就是指人体的免疫系统对自身的正常细胞或器官发起攻击,后果是很严重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及时纠错,受到无端攻击的自身正常细胞可以通过释放针对性的信号配体,反馈到免疫系统,让它们停止对自身的攻击。由此可见,这个“后门”—免疫系统的信号反馈回路—是非常重要的。
既然免疫系统有这么一扇应急用的后门,那么擅长“误打误撞”的癌细胞就有可能“撞开”这扇后门。癌细胞的最大特征之一,是它快速和多异性的基因突变。在变异过程中,尽管癌细胞表面的特征性标记分子依然存在,但是它也有可能在其表面“误打误撞”地产生能打开人体免疫系统后门的“钥匙”—功能性标记分子。一旦免疫系统接触到了这些标记分子,就好像是被灌了迷魂汤,即使能确认癌细胞表面的其他特征性标记分子,也会对它们网开一面,让这些癌细胞从“后门”溜走。这样一来,这些癌细胞就进入了免疫“照妖镜”的死角,有机会在人体内站稳脚跟,伺机发展。
钥匙开锁: 程序细胞死亡因子配体
在目前已知的癌细胞“走后门”的机理之中,癌细胞表面的程序细胞死亡因子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ligand 1,简称PD—L1)是被研究得最透彻的一种。2002年,耶鲁大学著名华裔科学家陈列平教授的研究团队首先发现了PD—L1配体,其他研究团队随后发现,小鼠体内的癌细胞过量表达PD—L1,就能躲过免疫系统的围剿;而多数人体癌细胞的PD—L1的基因表达都有所提高,首次阐明了癌细胞逃避免疫攻击的主要机理之一。陈列平教授也因此与1992年发现免疫T—细胞表面程序细胞死亡因子(Programmed cell death—1,简称PD—1)的日本科学家本庶佑(Tasuku Honjo),以及另外两位美国科学家于2014年一道荣获了肿瘤免疫学界顶级大奖—威廉·库里奖。
程序细胞死亡因子PD—1是免疫系统中的“巡逻兵”—T—细胞表面的调控受体之一,它的主要任务是防止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爆发,这些调控受体被称为“免疫检验点”(Checkpoint)。担任巡逻兵的T—细胞在正常情况下只是处于“警戒”状态,只有发现敌情时才进入“战斗”状态,这个过程被称为T—细胞的活化。有些癌细胞正是利用免疫系统里这个重要的信号反馈回路躲过了T—细胞的识别,程序细胞死亡因子配体PD—L1就是癌细胞打开免疫系统后门的“钥匙”。当癌细胞表面的PD—L1与免疫T—细胞表面的调控受体PD—1结合时,就好像钥匙插进了锁眼,免疫系统的后门被打开,免疫T—细胞的活化被抑制了,不能进入“战斗”状态,所以就停止了对癌细胞的攻击。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系列看似“十分精准”的生物过程,并不是任何“超自然”的“设计”,它们仍旧是进化论原则下随机变异、“物竞天择”的结果。没有自身免疫反馈回路的个体或是物种,肯定都逃不过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困扰,都已经成了遗留在历史长河里的零星化石碎片;没有有效“逃逸机制”的癌细胞,也肯定躲不过免疫系统的剿杀,就不能发展成为癌症。正因为癌细胞只有“误打误撞”这点本事,我们大多数人才能幸免于癌症,要不然我们这个物种恐怕也早就成了历史。
杜绝后门:“不抗癌”的抗癌新药
在癌症的免疫疗法出现之前,所有的抗癌药物都是针对癌细胞本身的。抗癌药嘛,不抗癌怎么能行?这些药物通过直接杀死癌细胞而达到治疗效果。但是手术之后传统的化疗和放疗都没有多少选择性,它们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会不可避免地杀死人体的正常细胞。因此,完成一个疗程的化疗对患者的身体会有很大的损伤,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恢复。更重要的是,除了快速变异之外,癌细胞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它有异常活跃的增殖能力,往往超过正常细胞,所以化疗对癌细胞的杀伤往往不够彻底,不能将其根除,会有卷土重来的可能性。近年来发展很快的靶向药物在这个基础上进了一步,可以有选择性地杀死癌细胞,对身体正常细胞的损伤大大降低。但是跟前面讲过的细菌耐药性一样,癌细胞早晚也会出现耐药性,因为它们跟细菌一样,基因类型的分布很广,而且能快速变异。
现在,我们弄清楚了癌细胞“走后门”的机理之一,就可以换一种思路对症下药了: 你不是利用程序细胞死亡因子的反馈回路吗?那我就想办法用药把这个回路切断,把你暴露在免疫细胞面前,让你无处躲藏。
以默沙东的抗癌新药帕博利珠单抗为代表的PD—1单抗药物就是这样一类“免疫检验点抑制剂”,从全新的角度,通过帮助免疫系统有效识别癌细胞,达到一举剿灭癌细胞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单抗药物其实是不抗癌的,因为它们并不是针对癌细胞本身的。离开了人体的免疫系统,这些抗癌药物在体外的试管里是杀不死癌细胞的,它们在人体内起到的作用是阻断免疫系统里的一个信号反馈回路(“堵死后门上的钥匙孔”),让癌细胞没有空子可钻。
暴露在免疫系统下的癌细胞所面临的是一场有针对性的歼灭战。因为免疫细胞能识别癌细胞与正常人体细胞,所以能在正常细胞不受损失的情况下,将癌细胞彻底清除出去。同时我们还有理由相信,免疫系统的长期记忆能力将会有效地阻止漏网的癌细胞卷土重来。
顺理成章?几次三番不招待见
现在听起来,这一切是那么的顺理成章。可是就在十几年前,除了几个异想天开的学者,相信PD—1抗体治疗癌症效益大于风险的业内专家可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
2003年,总部位于荷兰的欧加农(Organon)制药公司开始寻找PD—1受体的激动剂,希望通过活化PD—1受体而钝化免疫T—细胞,从而达到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目的。这个项目的初衷不仅与癌症治疗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还是相反的思路。到了2005年,项目团队没有得到任何好的激动剂,却意外得到了活性很高的拮抗剂,但是当时欧加农上下没有人清楚地知道PD—1受体的拮抗剂能有什么潜在的临床应用。他们考虑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之后,勉强决定在当时充满争议的癌症免疫疗法上进行尝试。
欧加农手里的这个抗体来自小鼠,与人体没有兼容性,除了做临床前研究外,不能用于进一步开发。于是他们找到了英国著名的医学研究委员会(Medical Research Council,简称MRC),跟它下属的研究部门签署了包含里程金和市场提成的合作协议,希望得到该抗体的人源化版本,为进一步开发做准备。首创抗体人源化技术的MRC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不负众望,在2007年成功地向欧加农团队交付了高活性、高专一性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也就是后来成为帕博利珠单抗的抗体分子。
但是,欧加农还没来得及对这个人源化的PD—1抗体做任何实质性的研究,先灵葆雅制药就在当年以140亿美元并购了欧加农,将PD—1抗体项目归入了自己的名下。在整合这两家公司的时候,公司高层对所有的在研项目都进行了重新的评估和排序,但遗憾的是,当时先灵葆雅也没有什么人看好PD—1抗体项目,先灵葆雅肿瘤研究部的领导担心调节T—细胞活性的风险太大,一旦触发了患者的细胞因子风暴(Cytokine storm),后果将是致命的,这不是个别专家的偏见,它其实代表了当时肿瘤免疫学领域的主流观点。
虽然不是重点项目,但是公司还是专门组织了团队,按照正常的开发流程设计了PD—1抗体临床研究的计划,并开始讨论如何实施。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就在先灵葆雅犹犹豫豫,拿不定主意是不是应该大笔砸钱,把这个项目推上临床的时候,自己就被默沙东兼并了。2009年,又一次兼并后的整合,又一轮项目评估和排序。这次PD—1抗体就没那么幸运了: 该项目的前期开发团队被解散,抗体分子被束之高阁,而且还贴上了“可认领”的标签,哪家公司愿意出个价就可以领走。
近几十年来,在前任总裁瓦杰洛斯的领导下,默沙东从以研发抗感染药物为主成功转型为以研发慢性病药物(降血压的依那普利2、降血脂的辛伐他汀3、降血糖的西格列汀4等)为主的制药巨头,抗肿瘤药物的研发一直都不是默沙东的主攻方向。所以说,默沙东决定终止这个当时还有很大争议的抗肿瘤项目并不出人意料,反倒是那些以研发抗肿瘤药物为主攻方向的制药公司,对这个在不久的将来马上就要价值连城的抗体分子视而不见,眼看着它静静地摆在货架上等着被贱卖,痛失良机。
弯道超车,看谁赢在终点线上
时机决定了一切。不早不晚,就在2010年,施贵宝制药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首次发表了伊匹单抗(Ipilimumab,商品名Yervoy)安全有效的临床研究结果。伊匹单抗是另一个免疫检验点(T—细胞活性调控受体)CTLA—4的抑制剂,与PD—1抗体有些类似。这一结果预示了“检验点抑制剂”的可行性,改变了当时肿瘤免疫治疗领域的主流观点。同时,有消息称,施贵宝制药的另一个检验点抑制剂PD—1抗体在临床一期也已初见成效。
默沙东决策层及时调整策略,把货架上还没有被贱卖的PD—1抗体拿回来,迅速重组了项目团队,在2010年底向FDA提交新药申请(IND),并在2011年初开始为第一项临床试验招募患者。一架高效的新药研发机器转眼之间又开始转动了起来。
默沙东面临的挑战是十分严峻的。根据当时的信息推断,施贵宝的PD—1抗体在2006年已提交新药申请,比默沙东领先4年,想要赶超几乎是“不可能的使命”。但默沙东的团队没有轻言放弃,他们制订了一个积极的临床开发计划,试图把握时机弯道超车,一场你追我赶的竞争开始了。
2011年,帕博利珠单抗如期进入一期临床试验,令人惊喜的初期结果大大增强了默沙东赶超施贵宝的信心。他们开始扩大一期临床的规模,最终增长到包括655例转移性黑色素瘤患者和相似数量的肺癌患者,成为有史以来肿瘤学最大的一期临床试验。
默沙东专注于转移性黑色素瘤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想要缩小与施贵宝的差距,这也许是最好的机会。如果默沙东能够证明帕博利珠单抗对所有标准疗法失败,包括伊匹单抗治疗失败的患者仍旧有效,则可以在单臂试验中开发该药物,而无须比较组,很有可能会获得快速的批准。
想要完成不可能的任务,没有一点运气是不行的。2012年,FDA计划实施了一种称为“突破性疗法认定”(Breakthrough designation,简称BTD)的政策,旨在使新药的批准更加合理和快速,而默沙东研发部在第一时间就获得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在这项新政策被广为宣传之前,凭借其在晚期黑色素瘤方面的出色成果,率先申请并于2013年1月获得了帕博利珠单抗的BTD资格,成为BTD政策推出以来,第二个获此殊荣的实验药物。默沙东没有立即公布这一事实,因为它不想过早地提醒自己的竞争对手。
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帕博利珠单抗终于成功实现了弯道超车,于2014年9月4日被FDA批准上市,成为在美国第一个被批准用于晚期黑色素瘤治疗的PD—1抗体原研新药,比施贵宝的同类抗体纳武单抗(Opdivo)早了3个多月,赢在了终点线上。
初见成效,有望对抗多种癌症
在这种快速有效的监管机制下,拥有强大临床开发团队的默沙东可以放手一搏了。2013年新上任的研发负责人罗杰·佩尔穆特(Roger Perlmutter)博士充分意识到了帕博利珠单抗的巨大潜力,指示大家停下手里的其他工作,不计成本,全力以赴做好帕博利珠单抗的所有临床研究。原来应该按时间顺序进行的临床试验,现在改成了同时进行的平行试验。根据默沙东2017年6月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会议上的报告,帕博利珠单抗已在80多个国家获批,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超过500项5,其中包括300多项联合用药的试验,涵盖30多种不同的癌症。
巨大的投入,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带来的则是巨大的回报:
2014年9月4日,获批用于晚期黑色素瘤患者;
2015年10月2日,获批用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二线治疗;
2015年12月18日,获批用于治疗晚期黑色素瘤患者的扩大适应证;
2016年8月5日,获批用于治疗复发性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状细胞癌;
2016年10月24日,获批用于某些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一线治疗;
2017年3月15日,获批用于治疗经典霍奇金淋巴瘤;
2017年5月10日,获批用于转移性非鳞非小细胞肺癌的一线联合治疗;
2017年5月18日,获批用于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的某些患者;
2017年9月22日,获批用于治疗复发性局部晚期或转移性胃或胃食管连接癌;
2018年6月12日,获批用于治疗复发或转移性宫颈癌;
2017年6月13日,获批用于治疗原发纵隔大B细胞淋巴瘤;
2017年5月23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FDA批准帕博利珠单抗可用于具有特定遗传特征的任何实体肿瘤的治疗,成为首个可以治疗多种癌症的药物。6
因为帕博利珠单抗不是针对癌细胞本身的,所以从理论上讲,只要是能被免疫T—细胞有效识别的癌细胞,而且这些癌细胞用于逃脱免疫反应的“障眼法”主要是通过PD—L1与PD—1的结合,那么帕博利珠单抗就应该是有效的。
虽然帕博利珠单抗这一类“检验点抑制剂”药物并不是对所有癌症病人都有效的,但是它肯定能被更广泛地用于多种癌症的治疗,而帕博利珠单抗与其他抗癌药物的联合治疗更是被业界普遍看好。
严格把控: 利害兼备的“双刃剑”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系统来杀死癌细胞,非但不是万全之策,而且有相当大的风险,实属利害兼备的“双刃剑”。除了上文提到的细胞因子风暴的风险之外,还有其他可能的副作用。
前面提到,免疫系统里存在这个信号反馈回路(“后门”)一定有它的道理,PD—1在免疫T—细胞的表达也绝不可能仅仅是为了给可能出现的癌细胞留一条活路。当免疫系统被PD—1抗体人为地激活后,很有可能带来一系列免疫和内分泌系统的失调,这是肿瘤免疫疗法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动物实验显示,PD—1基因敲除的小鼠很容易出现自身免疫性疾病,脑下垂体分泌失调等不良反应。在人体临床试验中,这些与免疫系统相关的副作用在少数病人身上也有出现,如不及时治疗,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好在现代医学对免疫系统失调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通过严密的跟踪监控,医护人员可以尽早发现少数患者因免疫疗法而产生的副作用,及时调整免疫治疗的强度与周期,并通过药物缓解患者因免疫失调而引起的不良反应。
尽管免疫疗法将在癌症治疗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它绝不是打几针就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检验点抑制剂”药物的使用必须在专业医师严格的控制之下进行,否则后果难料。
共同努力,我们一起对癌症说“不”
据美国癌症协会发布的《癌症事实与数字》(2019)预计,2019年美国将诊断出1 762 450例新的癌症,死亡人数可达606 880例!根据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提供的软件7,美国癌症协会对2013—2015年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显示: 一个成年人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候会被诊断为癌症的可能性已经接近40%。
2015年8月12日,九十高龄的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对外界透露: 在接受肝脏手术时,医生在他体内发现了癌症。进一步的消息是,前总统卡特的黑色素瘤已经转移到了大脑和肝脏。
美国第39任总统卡特自1981年卸任以来,一直活跃在世界政坛。他创立的卡特中心长期致力于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和健康水平,其中就包括与默沙东合作的伊维菌素捐赠项目,对彻底根除河盲症做出了很大的贡献。8
不幸的是,卡特家族有癌症的病史,他的父亲和三个兄弟姐妹都死于胰腺癌,他的母亲则死于乳腺癌,因此他本人属于癌症的高危人群。值得庆幸的是,帕博利珠单抗已经被批准用于黑色素瘤的治疗,所以他的医生在进行手术和放疗的同时,也使用了帕博利珠单抗。
奇迹出现了,仅仅几个月后,卡特总统在2015年12月6日对外声称,最近一次的磁共振脑部扫描“没有显示任何原始癌症斑点的迹象,也没有任何新的斑点”。
在全社会的大力支持下,在医药界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有理由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越来越多的癌症患者都能像卡特总统一样,对癌症说“不”。
——摘自《新药的故事》,译林出版社出版
作者:梁贵柏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徐坚忠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