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1年夏,郑文林(左二)参加北京大学为季羡林先生(左三)80岁寿辰举行的庆祝会。
1987年的一个早春夜晚,我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几位同仁,应季羡林先生邀请,到北京友谊宾馆餐叙,商谈北大南亚研究所和我社的合作问题(那时季先生还是南亚所的所长)。这是我第一次和季羡林相识。
季先生是一个大学者,我在上中学时就知道他的大名,读过他的散文。和这样一位知名学者见面,我开始有点忐忑不安,不知这位大学者是否有架子,是否好相处。谁知见面后,他竟是这样朴实、随意。他穿着随意,穿一身社会上早已过时的中山装(后来印象中在所有场合他都是中山装,没有见他穿过西装);说话也随意,他说:“说是商谈合作,实际是我们求你们来了。南亚问题研究在我国是一门‘冷学’,一般出版社都不愿意出版,我们就想到你们社,你们出版了不少学术著作,是我们学术工作的后盾。”我说我们做的还不够,但我社既然是一家学术出版社,就一定要为学术界服务,做好学术成果的出版工作。接着我们商谈了具体的合作事宜。席间,季先生一再说:“我是一个随意的人,不会劝酒劝菜,请大家随便自用吧。”告别时,我问季先生:“今后我怎么和季先生联系?”话里意思是要个他家的地址和电话——我知道有些大学者是不肯轻易将自家的地址和电话示人的。季先生一听马上叫我掏出小本,他随意在上面写了“季羡林 北京大学朗润园”多少号,还写了电话号码,他说你以后可以随时和我联系。这第一次见面,他的“随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自此以后,我和季先生的联系多了起来,我对他的“随意”感受更深了。他的“随意”,不仅表现在他的着装、谈话、对人亲和亲切上,而是他的一种做人“哲学”。它包含真诚、实在、老实、率真以及率性而为等等。
1989年,季先生的学生、社科院研究员赵国华出面联络了他当年北大梵文班的几个同学和老师,准备翻译印度古代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季先生很支持;但因部头大又直接从梵文原文翻译,难度很大,时间要很长、因此投资也大,当时无一家出版社愿意承担出版。赵国华找到了我,我考虑到此书的极大学术价值,就立即应承了下来。可是当第1 卷交稿正在出版之际,主持人赵国华却突然意外英年早逝了。这使我既悲痛又着急,这项大工程如何进行下去?我只有去求助季羡林先生。季先生看我很急,说话也快,说:“看来你是个急性子,不要着急,随意点,事情总会解决的。”他说“古人说‘泰山崩于前而不惊’我们做不到,但遇事不慌、不着急我们还是可以做到的。”他说他去帮我联系一下,叫我下星期再来一次。一周后我去了,季先生给我开了一个名单,说可以找这些人搞这一工作。后来,这一大工程在他的另一学生、社科院研究员黄宝生主持下又开始上马了,期间又经过艰难曲折,前后经历15年,终于完成在我社出版了。此套大书后来获得了首届政府大奖。
季先生自己为人“随意”,他也喜欢实在和真诚随意的人。1991年某一天,季先生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北大东语系的郭应德教授写了一本《阿拉伯史纲》在我社出版,但好久未出来,他请我过问一下。他说:“郭应德可是个老实随意的人,他的书是我国首部阿拉伯史的著作,也有价值。”我过问后,该书很快出版了。一天晚上,这位郭教授不知从哪打听到我家地址,提了两瓶酒上门致谢。他说:“我要来感谢你,但孩子们说不能空手去,现在时兴送礼,他们给了我两瓶酒,我就拿来了。”我对他说:“现在是时兴这一套,但我还没有学会这一套规矩,请郭先生还是拿回去吧,心意领了。”于是这位实在的郭教授又把酒拎了回去。
又有一次,季先生打电话给我,邀请我去北大参加一个东方文化成果的发奖会,说英籍著名女作家韩素音也参加,他要介绍我和韩素音认识。我一听韩是个名人,就问季先生我和她见面,要带点什么礼物?季先生说:“韩素音是个很随意的人,你也随意点,带两本你们社新出的书就可以了。”
上世纪90年代中,季先生主持的《东方学术文库》要出版了,他邀请了我社一位女美术编辑担任此书的装帧设计。她去见了季先生之后,回来对我说:“季先生夸你了,对我说‘你遇到了一位好领导,他是个实在的人。’”我领导工作做得并不好,但季先生却以他的做人“最高”词汇“实在”来褒扬我,使我受宠若惊;也督促我更要努力,终身要做一个实在的人。
此事不久,季先生的学生、北大张保胜教授要搞一套《宗教与文化》的丛书,季先生任主编,他为副主编;还请我也任副主编。我打电话给季先生,力辞这副主编。我说:我对这一课题没有研究,加之我在出版社工作,我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就是从不在作者的成果上挂什么“主编”“副主编”之类的名义。季先生电话中又叫我“随意点”,说还是任副主编,只负责出版;他叫我去他那里一起谈谈。去后,我们除谈了这一课题的内容和重要性外,还谈了“主编”这一工作和名义的事。我说:“有些大学者对自己的名声很爱惜,从不肯轻易去挂名担任什么书的主编。”我话中另一层意思没有说,即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季先生曾在多部大书中担任过主编,学界有人对此颇有微词,不知季先生对此是怎么想的?季先生听出了我话的意思,说:“主编就是‘主持’,有的人有研究,策划和组织一切,为主持人;有的是‘支持’,支持和帮助这一工作。找我当主编,我看这一工作对文化学术建设有益,我支持,应当给以帮助,我也就当了。我这个人很随意,从不在意个人名声,只要是文化好事,我都支持。”
这次谈话到了吃午饭时间,张保胜和有关人士也在座,我说:“过去季先生请我吃过饭,今天我做东,请大家一起吃个便饭。”我一再请季先生提一个他满意的饭馆,他反复说“随意吧”,最后去了北大附近一家普通的饭馆。我请季先生点菜,问他有什么忌口的,他又说“随意吧”。张保胜说,季先生不忌口,什么都吃,还爱吃红烧肉呢。我听了吃一惊,问季先生:“季先生不怕胆固醇吗?”他说:“我吃东西很随意,自己爱吃的就吃,不在乎什么禁忌。拿红烧肉来说,你爱吃,说明这东西你身体需要它,对你有好处。”季先生后来高寿98岁辞世,说明食物对人还是因人而异的。
然而,季羡林的“随意”,随着他的名声日隆而受到了“限制”,他慢慢地不能“随意”地生活了。1990年代后期,我为社科院科研局策划组织一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其中分别总结社科院老学部委员和一级研究员的治学经历和经验,请这些大师的亲密助手和学生来撰稿。鉴于大师在世的人已不多,我规定这些在世的人的撰稿人一律由这些在世的大师自己来指定。季羡林先生是其中一位。我拨了季先生的电话,谁知接话的是一位女士,她问我有什么事?我说请季先生接电话。她说你有事可和我讲。我说你是谁?他说她是季先生的助手。我说明了意思,她说问了季先生后再答复我。后来久未答复,已到了交稿时间,我等不及了,就自己约了季先生的一个亲近学生来写。后来遇到季先生的其他门生,都有类似经历。原来,上世纪90年代后,季羡林的名声越来越大,各种人物怀着不同目的像走马灯似地来拜访他,求他办事,而季先生的“随意”又使他们“有求必应”,严重影响了他的工作和生活,于是学校就给他配备了助手,为他档驾。这是必要的。然而,这也影响了他和外边的“随意”接触;我们这些门生故旧也不能“随意”地去看他了。
到了季先生晚年,我们这个日益发展的市场社会,给季羡林戴上了种种桂冠,把他高高供起来,他离我们更远了,而政要、大碗、甚至房地产大鳄却能不断拜访他,有的真诚向他请教,有的则是站在他的光环下以提高自己的身份。我想,这和“随意”的季羡林是背道而驰的。果然,他辞世前不久,写过一篇文章,要求去掉戴在他头上的三顶帽子,即“大师”、“泰斗”、和“国宝”。然而,他始终未能如愿。
现在,季羡林已经驾鹤西去了,我想,在那遥远的天国里,他大概能去过他那“随意”的生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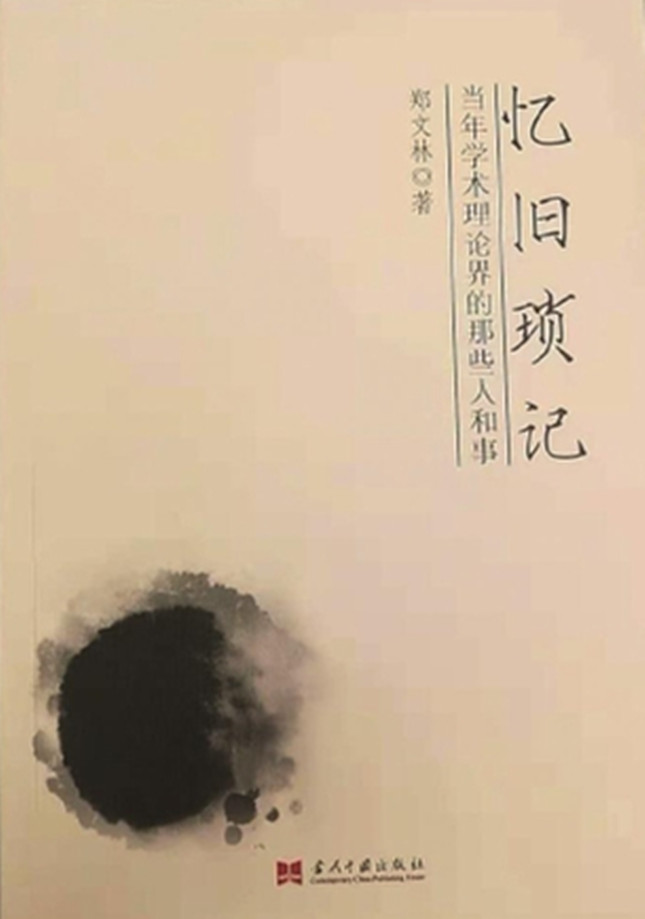
▲本文摘自《忆旧琐记:当年学术理论界的那些人和事》,郑文林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郑文林,曾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作者:郑文林
编辑:朱自奋
责任编辑:张裕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