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伯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近照
李新伟:您对中华文明探源的一些研究大家都挺关注的,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李伯谦:中华文明以历史悠久、光辉灿烂著称于世界,但中外学者公认的历史年代只能上推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这与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很不般配。这是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注: 以下均简称“断代工程”)最初的想法。断代工程结束之后,我们就开始筹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注: 以下均简称“探源工程”)。我主持起草了《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几点设想》送呈国家领导人,建议国家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开展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随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获批为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我是主持人之一。其实当时大力支持开展断代工程的宋健本来是想从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入手,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他很关注文献中关于黄帝的记载,找了一些学者梳理研究,希望能找到考古证据,但发现难度比较大。后来才决定先开展“夏商周断代工程”,确定一些关键年代,这个可能容易一点。
我们都讲中国五千年文明没有中断过,但是具体去想,中国这么大,好多文化谱系也不一样,是不是走的路都一样?是不是都是一个模式?我想这个可不一定。良渚文化跟红山文化就不太一样,跟仰韶文化也不太一样,所以就提出了社会演变的两个模式,不管对还是不对,这是我的一种看法。很高兴能引起大家的关注。
我后来又思考,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模式呢?我把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的演变梳理了一下。崧泽文化出现社会分层是比较早的。如东山村墓地,它的年代最早是距今5800年左右,东边是一般的墓葬区,西边是大墓区,有五个大墓,都随葬石钺,有的有四五个之多。这说明那个时候它就有一些分化和社会分层了。钺在随葬品中很重要,说明当时的社会上层走的是军权、王权这个路。凌家滩文化跟崧泽文化时代差不多,宗教气息就比较浓。红山文化和凌家滩文化有密切交流,宗教气息也很浓。崧泽文化的后续者良渚文化就发生了改变。良渚墓葬里钺很多,但与神权相关的东西也特别多。我觉得良渚社会中神权可能具有支配地位。反山墓地出土的那件“钺王”,上面刻着神鸟,还有一个神徽,如果是一般的兵器,不太可能有这些图像。仰韶社会就比较单纯,墓葬中兵器很少,玉器也不多。
但是红山文化以后的小河沿文化,慢慢就衰落了,良渚文化渐渐也衰落了。衰落原因很多,有环境变化、气候变化等外因,但有一个重要的内因,就是将社会财富大量地浪费于宗教事务,最后失控了。

▲李伯谦2013年在“中国考古学论坛”上点评文峰塔墓地。
李新伟:您是如何认识最初的“中国”这个概念的?
李伯谦:“中国”的概念是发展的,“中国”这个词最早见于西周成王时期的何尊,当时这个词的含义似乎还不是后来理解的国家,而主要是指从地域出发考虑的“天下之中”的意思。周人的老家在陕西关中一带的周原,文王时为了东向灭商把政治中心迁到了丰,武王时又迁到镐,灭商以后,又想把都城建在洛阳。为什么周人要把洛阳作为都城呢?周人可能觉得周原的岐和丰镐太靠西了,殷墟又太偏东、偏北,而洛阳恰在至少从夏代就形成的“天下之中”,掌握了这一中心,才能够掌握全国。文献上讲“周人尊夏”,在他们的观念中认为夏的都城所在地才是真正的“天下之中”。
这种以中原为天下之中的观念可以追溯到龙山阶段,甚至还可能再往上追溯到仰韶时代晚期。我觉得这个地区的发展是中国发展道路的核心,有仰韶文化、陶寺文化、王城岗文化、二里头文化这个发展主线。周围的文化区是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逐步加入到这个洪流和发展主线当中来的。我觉得目前开展的探源工程应该描述这一过程,勾画出中华文明发展的主干和支脉,勾勒出她是如何发展成参天大树的。

▲李伯谦2013年观摩禹会村遗址出土器物。“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是极有可能的。
李新伟:安徽蚌埠禹会村遗址发掘颇为引人注目,激发了大家对古史记载与考古资料结合的新思考。您对禹会村遗址的资料和“禹会诸侯”的记载有什么看法?
李伯谦:看了这个遗址我感触很深。第一点,就是淮河流域考古学的重要性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古代文献讲,江、淮、河、汉谓之“四渎”。这四条水都很重要,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与这四条水有密切关系。黄河流域的考古工作开展得比较早;长江流域晚一点,后来紧紧跟上了,可能还要超越;汉水流域也做了不少工作。而淮河流域的考古工作起步最晚。1982年我曾经带过一些毕业班学生到安徽实习,着眼点就是淮河流域,特别是江淮之间,当时在霍丘扁担岗、寿县斗鸡台、青莲寺,六安众德寺、西新城等地点做了一些工作。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了禹会遗址,安徽省考古所和蚌埠市博物馆发掘了双墩遗址,还有安徽省考古所发掘了侯家寨遗址,这些年,淮河流域的考古终于出了一些成果,这是非常可喜的事情。

▲李伯谦2013年为禹会村遗址题词。
第二点,禹会遗址和文献记载能不能加以对应。这首先是怎么看待文献记载的问题。《左传》上讲,“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尚书》《诗经》也有关于禹的记载。而且我还注意到,武王灭商以后,急急忙忙分封了很多国家,其中特别追思先圣王,如《史记·周本纪》所言,把他们的后代加以分封,神农之后封于焦,黄帝之后封于祝,尧之后封于蓟,还有舜之后封于陈,禹之后封于杞。
从这个史料上来看,至少商代晚期和西周是相信禹的存在的。还应提到的是西周中晚期的遂公盨,明确记载了禹平水土的事迹。过去,因为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潮,把许多古代文献否定了,使得我们变得非常谨慎,对古代文献总感觉不太敢用。正如我前面所说,对于文献应该以科学的方法加以分析、研究,合理利用,一概排斥怀疑不可取。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个记载就应是可信的。
禹会村遗址既然叫禹会,是不是文献记载中“禹会诸侯”的地方呢?这要看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有没有契合之处。
先看文献中的大禹时代,那是尧、舜、禹禅让的时代,也是邦国联盟的时代。从仰韶文化晚期以来,社会发生重大转型,此时这些地区已经迈入了早期文明的门槛。禹当政的时候,治理淮河,在涂山召开了一个各路诸侯都参加的盟会,没什么不可思议的地方,这是顺理成章、极有可能的。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件,过去只见于文献记载,现在通过考古发现和发掘知道此事件应该有真实的背景,禹会村遗址可能与此有密切的关系。
看看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我们就会清楚这个事件的意义。盟会加强了部落之间密切的联合、文化的融合、感情的加深,为夏王朝广域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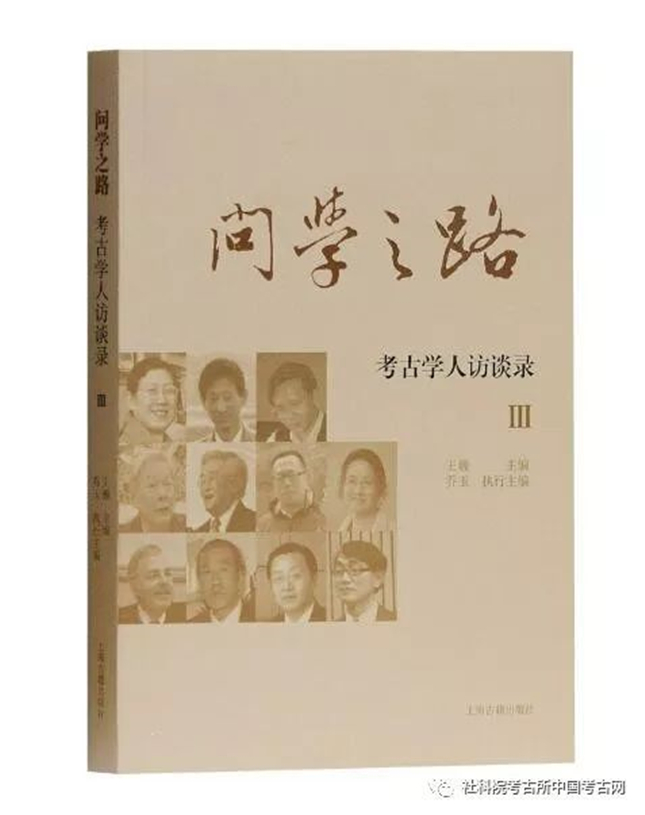
▲本文摘自《问学之路:考古学人访谈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作者:李伯谦 李新伟
编辑:朱自奋
责任编辑:朱自奋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