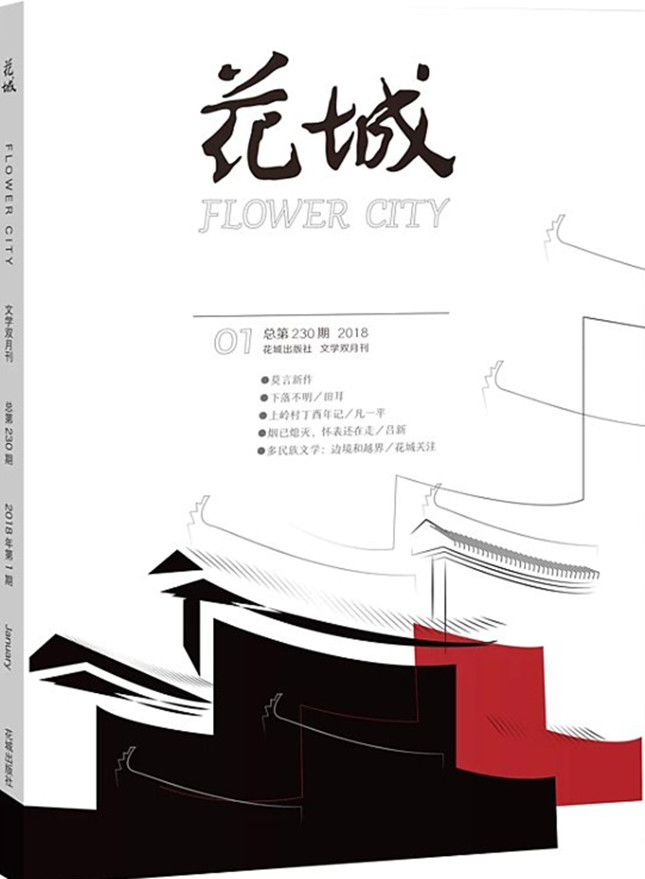
刊发于《花城》2018年第一期的田耳新作《下落不明》近期即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小说讲述了一群文艺青年对理想的坚守以及最后理想破灭的故事,具有一种独特的孤独气质与自传性质。田耳的身份标签很多,青年作家、少数族裔、大学教授、孤独写作者等,他的创作题材也十分宽泛,甚至在一部作品中也是小径不断分岔。《下落不明》就是如此。故事的外衣是一桩凶杀案,但中间穿插了家族叙事、文学青年的成长、青春的回忆、理想的坚守与破灭、形式各异的情爱故事等,既有刑侦悬疑的通俗性,也有理想信仰的灵魂探析,既有个体另类的成长史,也有一代人共通记忆的追寻。
《下落不明》描写芸芸众生,各色人物相继出场,笔墨不均情感却无差别。田耳对成长与理想的讨论首先从人物的生存环境开始,耿多义、耿多好、齐虎、失足小姐、被人包养的女性等,都如蝼蚁般苟活于世。小说特别塑造了具有病态气息的作家耿多义这一形象,通过其独特的创作模式与生存方式来书写青年的成长。田耳的创作有一种代入感,即进入他人的痛苦中去,与人物共呼吸,使得他的小说读起来有一种切肤之痛,这种痛苦扑面而来,毫无膈应感。《下落不明》表现得尤为明显,有一种自传性质,同时,小说还回归文学与作家本身,具有元小说的意味。
田耳自诩《下落不明》是一部关于成长的小说。小说中有大量的人物不断出场,有些贯穿始终,有些昙花一现,但几乎每个人物都面临成长的尴尬,在成长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受到阻力,这种阻力来自多方面,既有家庭的因素,也有大的时代背景。比如耿多义成长期间受到同胞哥哥的欺压,甚至被打傻了脑袋;莫小陌的家庭分裂,父亲与自己的闺蜜纠缠不清,她本人的成长则受到母亲明总的干涉,连自己对文学的爱好也被控制,被硬逼着写武侠;欧繁则出身于重男轻女的家庭,因超生的原因东躲西藏。总之,这些人物后来的不幸或悲剧与这些尴尬的成长环境不无关系。当下有很多小说以成长为主题,而且内容大多是负面的、尴尬的,进而影响个体的一生,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成长小说似乎大都是“青春祭”,《下落不明》虽然也有大量的童年与青春记忆,但是并不落俗,而是通过回忆为成长做铺垫,为理想唱挽歌,通过成长的复杂写出人性的丰盈。成长通常意味着理想的消亡,但小说还是留下了诸多光明的尾巴:耿多义仍在坚持写作,欧繁与老莫相依为命,耿多好改邪归正,过上了正常安定的生活,只是耿多义苦苦追寻的莫小陌仍旧下落不明,这似乎是理想失落之隐喻。
文学评论家谢有顺指出:“田耳的伦理观,有齐物之想,无善恶之差别,以平等心、同情心、好玩之心,批判一切,也饶恕一切,正是这样的创作伦理,使得其作品无明显的善恶对立,而是在善与恶的纠缠中展现生存的艰辛与艰辛中的温暖。”田耳的平等思想和齐物伦理观使得他的作品中善恶并不截然对立,而是写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丰盈性。他钟情刑侦与犯罪一类的通俗题材,借助善与恶的暧昧性来深掘人性。他似乎秉持一种审丑美学,对人性的恶进行深入挖掘,这种恶说到底与人性有关而非与阶层有关。田耳解构了阶层的划分,以平等之心对待每一位个体,书写了每一个人的生存困境,如何应对生存、世界、自我,如何成长,是每个人都需要思索的问题。
田耳的《下落不明》有一种去价值判断、去阶层划分的意味,可谓自我和解与原谅之作,原谅一切,最终原谅自我。芸芸众生的生存空间、奋斗打拼、情爱婚恋、精神面貌等,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精彩的呈现,是文学拉近与现实的距离,深度介入生活的最好例证。也正是通过这些描摹,作者书写了人性的复杂与丰盈,为众生带去些许的慰藉。
作者:刘小波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周怡倩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