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黄寺清净化城塔(油画)曾一橹 作于1935年
1.
关于北京的书写,我起步很晚,最早于1995年。当时,浙江人民出版社约我写一本叫《北京人》的小书。尽管这本书后来翻译成韩文,在韩国出版;又在我国台湾出版了繁体字版,有一定的影响,但我自己知道,这本书写得匆忙,很是单薄,有很多值得写的东西,都没有写到。一直想有时间好好新写。只是那一年,即1995年的夏天,我调到作协,参与办刚刚复刊的《小说选刊》,工作一时有些紧张,以后的写作兴趣又未完全集中在这里,便把这计划拖了下来。
一直到2003年的年底,有一天,到人大会堂开会,会议结束,忽然想这里离我小时候住的大院不远,往南,过前门楼子,再往东拐一点儿,就走到了小时候一天恨不得跑八趟的西打磨厂老街。便走回老街,一直走到老院。我已经有十多年没去那里了,老街变化不大,和我小时候几乎一模一样,但看到满街贴着拆迁的告示,很多老房子的外墙上,用白灰涂抹着大大的“拆”字,还是有些触目惊心,心里暗想,幸亏来了,要是再晚一点儿,恐怕就看不到童年的老街老院了。
写作北京的念头,像飘飞的风筝一样,又被牵了回来。我想,得抓紧时间写了。
2004年初,在西单砖塔胡同旁,每天上午有半天的脱产学习。吃完午饭,带着笔记本和照相机,还有一杯水,开始往前门这一带跑。西单离前门不远,坐22路公交车,几站地,我父亲当年的工作单位,在西四新华书店旁的税务局,小时候,找父亲,常坐22路公交车,算是轻车熟路。
我并不是出生于北京,而是生于河南信阳。不过,刚刚出了满月,母亲就抱着我到了北京。说来有些惊心动魄,1947年之春,正值战乱,火车站上的人非常多,转车的时候,母亲抱着我,没有挤上火车,只好等下一趟。这趟火车开到离北京很近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说是前面那趟火车开到丰台,突然爆炸了。如果母亲抱着我挤上了那趟火车,可能也就没有我了。
来到北京不久,我们一家便住在西打磨厂粤东会馆里,从落生不久到童年到青年,一直住到1975年,才搬家离开了老街老院。除了1968到1974年去北大荒六年,其余时间里,我都居住在北京,应该算是一个老北京人了吧。因此,对于北京,尤其是前门外的城南地区,非常熟悉,充满感情。重回老街老院,如见风雨故人,一切依然那么熟悉。
那时候,拆迁虽然日隆,但并未大面积地展开,很多地方,老街老院老店铺老门联老门墩老影壁老树,连大门前的房檐上当年元宵节挂灯笼的铁钩子,生了斑斑铁锈,都还在。尽管访旧半为鬼,毕竟老街坊还健在一些。回顾前尘往事,旧景故地,仿佛并未远去。他们熟悉我,即使以前不认识的,架不住我常去那里,他们也都认识了我,甚至连拆迁办的人都知道了我。有的人,见到我,老远就和我打招呼。无论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老街坊,还是素昧平生的陌生者,他们给予我很多帮助,让我知道了很多以前我不了解的事情,对这些自以为非常熟悉的一切,有了新的体认。我常会想起他们,只要想起在那些老院落里,他们和我攀谈的情景,心里就会充满感动,也会有些许的伤感,十七八年过去了,那些当年八十多岁的老人,不知道如今还在不在。
我感谢他们。他们是真正的老北京人,比有些坐在会议室或主席台上夸夸其谈却不断大拆大建的人,对老北京更具感情。
2.
那几年,我常常游走于城南这些大街小巷,完全像一个“胡同串子”。也遇见不少逛胡同的人,他们都很年轻,成群结队,背着专业的相机,拼命地为这些即将消失的老北京景象拍照留档,他们有自己的网站,可以将这些照片传到网上,让更多关注北京的人看到。有一次,我被邀请参加他们的队伍,到草厂二条的一个小四合院,一边吃着他们做的炸酱面,一边听他们串胡同拍胡同的见闻和体会,能感受到他们对老北京的热爱和探寻的殷殷之情。
有时候,也会碰见外国人,记得在新开路和南孝顺胡同,我碰见的那两拨外国人,前者骑着自行车,后者背着旅行包,他们不会说中国话,我们只能相视一笑。那些破旧甚至破败的胡同和院落,让他们觉得还像老北京。有一次,在前门新开通的东侧路,我碰见一些来自美国的大学生,都是学中文的,会说一些中国话。他们正在看刘老根大舞台,我和他们攀谈起来,他们对我说,以前门楼子为中心,东西两边的胡同,他们都去看了一些,觉得西边拆得少,更像他们读过的老舍《骆驼祥子》里的老北京,东边不像了。他们指着刘老根大舞台新建的金碧辉煌的牌坊,这样对我说。
游走在这样的老街,碰见这样的新旧朋友,我的心里五味杂陈。有一种仿佛在往昔时光中穿越的感觉,回忆和现实、幻觉和错觉,交织一起,碰撞一起,常让我感到似是而非而无所适从。我想起梁思成先生1947年写的《北平文物必须整理和保护》一文;北平和平解放以后,他又多次陈情:北京城的整体形制,既是历史上可贵的孤例,又是艺术上的杰作,城内外许多建筑,是各个历史时期的至宝,它们综合起来,是一个庞大的“历史艺术陈列馆”。他特别强调,承继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一笔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遗产,需要做的是整体保护这一文物环境。
如今,我们却在迫不及待地进行拆迁,破坏这一整体的文物环境。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值得吗?在破旧立新的城市建设伦理指引下,将旧的胡同和院落拆掉,建立起的新楼盘和宽阔的马路,就一定更有价值吗?
就这样,我边走边看边记边写,尽管我的笔头赶不上拆迁的速度,这十多年还是陆续写了《蓝调城南》(2006年)、《八大胡同捌章》(2007年)、《北京人(续)》(2013年)、《我们的老院》(2017年)、《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2020年)和《天坛六十记》(2021年)几本小书。面对北京这部大书,写得远远不够,只能算是完成了我的一点儿心愿吧。
3.
书写北京,一直有众多人前仆后继,各类书籍异常丰富。这些前辈,一直是我的榜样。不谈明清两代,民国时期,陈宗蕃、张江裁、李家瑞和侯仁之四位前辈的书,一直置放在我的案头和床头。
陈宗蕃先生1930年出版的《燕都丛考》,已经被我翻烂,几经贴补,伤痕累累。这本书所书写的京城历史与地理之沿革与变迁,其丰富与翔实,不仅超出清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也为后来者所少有。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如今所有书写或关注老北京的人,尤其是关注老北京城池与街巷的人,都不能不读这本书。
张江裁(字次溪)对北京风土民俗的关注,在那一代人是很突出的。张江裁一生所编纂出版的书目,让人叹服。其中有他挖掘、重新出版的《帝京岁时纪胜》《一岁货声》《燕市百怪歌》等多种,为今天研究老北京留下宝贵的资料。迄今为止,我没有见过有哪一位学人肯如此下力气,单凭一己之力,孜孜不倦致力于北京民俗风土志一类书籍的钩沉、挖掘与出版。不仅如此,他还有过身体力行,年轻时在北平研究院工作,参与北京庙宇的实地调查和文字记录工作。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天津文化街买到李家瑞先生的《北平风俗类征》,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根据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的影印本。全书分上下两册,有岁时、婚丧、职业、饮食、衣饰、器用、语言、习尚、宴集、游乐、市肆、祠祀及禁忌、杂缀共十三类,构成一幅老北京的风情画长卷。是书为李家瑞先生自1931年至1935年,历时四年,翻阅上至周礼下至清末民初的报刊书籍共约有五百种,先后抄录了40余万字所得。这两册书,对我了解老北京的风土人情以及习俗旧礼帮助很大,百看不厌,每看有得。
侯仁之先生的《北平历史地理》,我读到的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出的书。此书是侯仁之先生在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博士论文。从早期的边疆之城,到元明清的王朝之都;从蓟城,到金中都城、元大都城、明清都城;侯仁之先生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北京这座古城政治历史与地理地位的变迁。他以人文地理与历史地理相结合的现代治学理念,写出了我国第一部关于一座城市的历史地理的专著。其占有材料之丰富,实际田野考察与研究的功夫之深厚,并有自己精确的手绘制图,尽管已经过去了近七十余年,仍未能有一部书可以超越这本著作。而且,迄今所有关于北京历史地理方面林林总总的书籍,所论述的观点,所涉及的材料,所引用的典籍,都未能出其右,实在叹为观止。
这本书的引言,记述了侯仁之先生1931年读高三时第一次从山东乘火车到北京的情景和感受:“那数日之间的观感,又好像忽然投身于一个传统的,有形的历史文化洪流中,手触目视无不渲染鲜明浓厚的历史色彩,一呼一吸都感觉到这古城文化空气蕴藉的醇郁。瞻仰宫阙庙坛的庄严壮丽,周览城关街市的规制恢宏,恍然如汉唐时代的长安又重现于今日。这一切所代表的,正是一个极具伟大的历史文化的‘诉诸力’。它不但诉诸我的感官,而且诉诸我的心灵。我好像忽然把握到关于‘过去’的一种实感,它的根深入地中。”
这一段话,最让我感动不已。这座城市给予他感官与心灵的冲击,他说了一个词叫做“诉诸力”。北京这座城市有这样历史与文化的“诉诸力”,才会让我们把握住这样的历史与文化,让这样的历史与文化有了一种实感。七十余年过去了,北京城还会给予我们这样的“诉诸力”吗?我们还能够把握住这座古城的历史与文化的实感吗?
上述四位前辈的书,一直是我写作老北京的范本。囿于学识和阅历,我感到自己写得实在是单薄,只能驽马加鞭,争取写得好一些,有进步一些。
4.
这本《燕都百记》,与以前我写的那几本关于北京的书,有些什么样的区别,是我在写作之前想的问题。我不想重复以往惯常的写作方式,而且,关于老北京的历史与文化,我写得够多了,已经无话可再说,希望这本新书能够写得稍微新鲜一些,让我自己多少有些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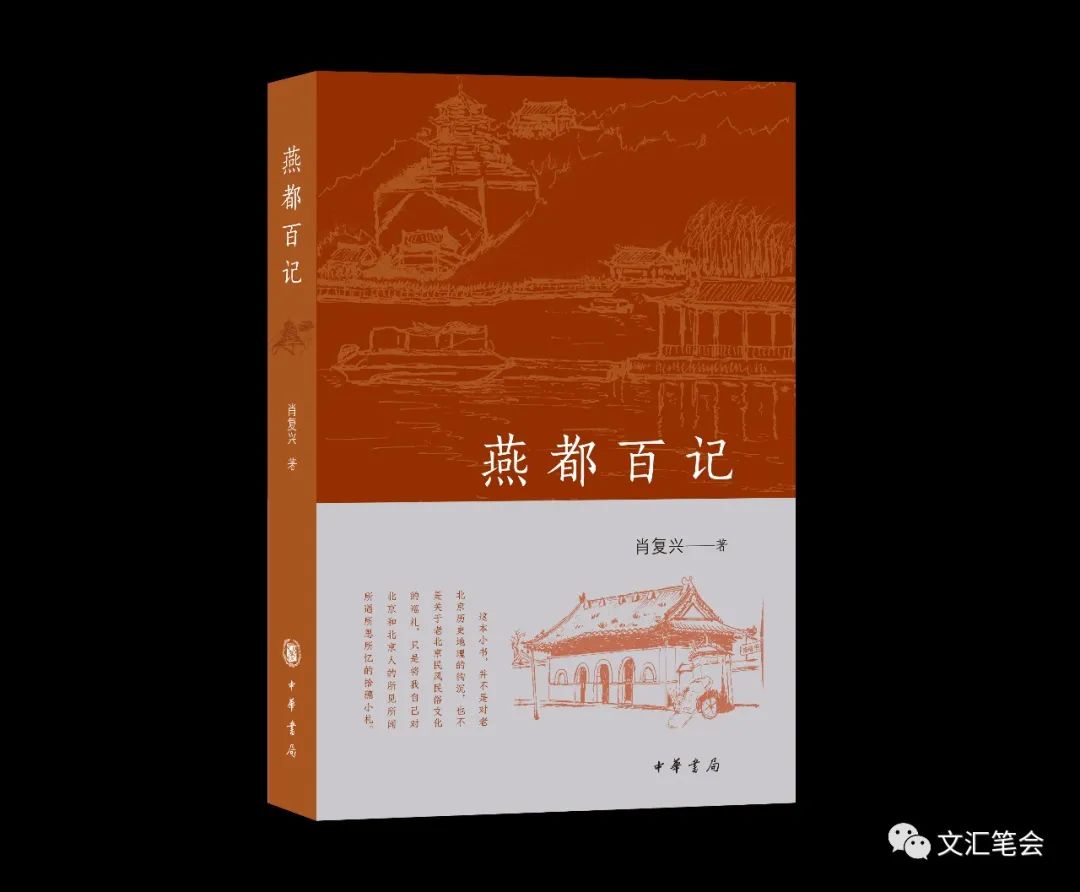
这一次,我这样要求自己:一要尽可能的写短;二将历史的部分,引用典籍的部分,尽可能删汰;三要加强亲历性、现场感;四不止于城南,蔓延至城北更多的地方。
因此,这本小书,并不是对老北京历史地理的钩沉,也不是关于老北京民风民俗文化的巡礼,只是我自己对北京和北京人的所见所闻所遇所思所忆的拾穗小札。在写作方式上,学习的是布罗茨基所强调的那种创作原则,即“意识中所产生的自然法则”,“也可以这么说,这是粘贴画和蒙太奇的原则。”同时,他还强调:这是“浓缩的原则,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倘若你开始用类似浓缩的方式写作,全都一样,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写得都很短”。
我喜欢这种创作原则,在我的上一本书《天坛六十记》的写作中,曾经尝试运用的就是这种原则。如今,在被资讯焦虑与生活快节奏所簇拥裹挟下的大多数读者,已经没有足够的耐心读长篇巨制。布罗茨基曾经一言以蔽之:“纯文学的实质就是短诗。我们大家都知道,现代人所谓的attention span(意为一个人能够集中注意力于某事的时间)都极为短暂。”
这本小书,尽管有一百篇,但每一篇都很短,最短几百字,最长不过两三千字而已。感谢中华书局,感谢本书的责编董邦冠先生,是他们的青睐和鼓励,才有了这本小书的出版。希望读者能够喜欢,在简短的篇幅中,看到北京的新老风貌,看到你自己。我们也能在书中相逢——正欲清谈逢客至,偶思小饮报花开,正想找个人交谈,我们正好在这里碰见,谈谈我们都热爱的北京的前世今生。
2022年春节前写于北京
作者:肖复兴
编辑:钱雨彤
责任编辑:舒 明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