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档案】夏禹龙(1928—2017)理论学者。浙江杭州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土木系。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1949年从事进步学生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主要从事共青团、社会科学研究和出版工作。曾任上海人民出版社哲学编辑室主任、上海科学学研究所副所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世界科学》主编等职。出版著作二十余本(包括单独撰写、主编和第一撰稿人),论文二百余篇(单独撰写和合写),并选辑《夏禹龙文集》。在邓小平理论、科学学、领导科学研究等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观点和有影响力的对策建议。2016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2017年获首届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终身荣誉奖”。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敢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也正是作为理论学者的夏禹龙身上最鲜明的学术标签。他是一位“非典型”的人文社科学者,与一般学者追求“专而精”不同,夏禹龙的知识结构非常广博,兼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他的研究也不受传统学科的限制,在科学学、领导科学、区域经济和邓小平理论等领域都有原创性贡献,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开风气之先”,而且其中的一些创见至今仍深刻影响着相关领域的前沿研究。
创见迭出的学术生命力与不断开辟新域的学术勇气,源于夏禹龙对时代的关切和与时俱进的思考——他从不安守书斋,而是将自己的研究与实践紧密相连,正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方松华所说,“夏老是名老党员,少年时期就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运动,这种心怀天下的使命感贯彻于他的学术生涯。他始终关注国家的前途和兴衰,将眼光投向现实的需要,求索‘中国道路’的学理性模式,这也是其学术生命长青的秘密所在。”
兼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
夏禹龙出生于1928年,祖籍浙江杭州。其父是大通煤矿的襄理,大通煤矿是一家私营企业,抗战爆发后被日军占领。尽管家境殷实,但夏禹龙一家思想进步,拒绝当亡国奴。他的姐姐夏孟英和大哥夏禹思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相继入党,也是解放前上海青年运动的骨干。在家庭的熏陶下,中学时代的夏禹龙接触到了许多进步书籍,受到很大影响——斯诺的《西行漫记》丰富了他对共产党的认知, “我相信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而国民党的抗日是消极的、敷衍的”,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让他对社会不公有了深切体认,而对他影响最大的则是鲁迅,“当时我几乎读遍他的杂文,实现民主自由、个性解放也是我追求的目标。”
就这样,1945年,年仅17岁的夏禹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是其当时所就读的南洋模范中学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入党后,夏禹龙在南模建立了党支部,成为首任支部书记,并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成绩斐然。但也是因为参加学生运动,他屡被开除,就此开始了一段颠沛流离的求学生活——在四年多的时间里,他念了五个学校,换了三个专业:继南模之后,他转入复旦中学;抗战胜利后,又先后就读于大同大学电机系、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机械系、圣约翰大学土木系。因为一心革命,原本成绩不错的夏禹龙实际上被迫放弃了学业,但他并不后悔,“当时一心所想的是只要革命成功,一切问题便都可解决,因此没有怎么考虑个人的事情。”尽管后来转向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但始于南模的这段理工科教育,还是对夏禹龙留下了终生的影响,“我很讲求逻辑一贯性,不要存在自相矛盾”。这种讲究严密逻辑的理工科思维,始终贯穿于他后来的社会科学研究中。
上海解放后,夏禹龙离开圣约翰大学,参加了青年团的工作。1956年3月,他调往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从事党史研究。1960年起,先后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哲学编辑室、《自然辩证法》编辑部担任编辑。后来那段动荡艰难的岁月里,夏禹龙长期处于 “靠边”状态,但他并没有就此一蹶不振,而是初心不改地坚守着那份对国家的真诚与担当,始终关注并思考着前沿的理论问题——他将研究重点转向“自然辩证法”,并利用可能的空隙时间,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理论名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资本论》、黑格尔的《小逻辑》、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他都广泛涉猎并认真做了读书笔记。“文革”后期,他还曾发挥土木背景的优势,作为《桥梁史话》的责任编辑,与作者共赴全国各地考察,合作完成了这部对中国后来的桥梁建设与保护起到一定作用的著作。
回过头来看,这段编辑时光看似杂乱,但也为夏禹龙兼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两栖”知识结构打下了地基——晚年他曾这样自我剖析:“我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道路与一般人的情况不大相同。我没有受过社会科学知识的系统训练,凭自己个人的兴趣爱好,长期坚持自学、思考、研究……与受过正规专业训练的大多数社会科学学者不同,我在专业知识的系统性和深度上与他们有差距,但是我的跨学科的知识结构,在研究问题时会形成一些新的视角。”
改革开放后,夏禹龙重回岗位从事理论工作。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他,终于迎来了自己学术人生的“黄金期”。
将眼光始终投向现实的需要,为改革开放鼓与呼
伴随改革开放进程,日新月异的变化使得实践对理论的需求“如饥似渴”,而与实践要求相适应的新理论却显得“供不应求”。为回应时代需要,上世纪80年代,一股“新学科热”在上海兴起,一批理论界的“开路先锋”活跃在思想舞台,一系列为改革开放和为决策服务的应用学科就此应运而生,其中,夏禹龙、刘吉、冯之浚、张念椿四人所提倡的“科学学”和“领导科学”在当时的上海理论界异军突起,成为典型代表,四人的合作成为一段广为流传的学术佳话。
四人的合作始于1979年——那年初夏,夏禹龙去武汉参加“全国科学技术史”讨论会,会后与同为上海代表的刘吉、冯之浚、张念椿乘轮船返沪。几天的航程里,四人一拍即合,并合作完成了第一篇文章《要重视科技史的研究》,发表于1979年8月30日的《文汇报》。以此为起点,开启了他们合作研写达十年之久的学术生涯,期间,以4人名义发表的论文达100万字,著作达100万字,涉及的内容范围看似庞杂,但都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为改革开放鼓与呼,“改革开放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我们就讨论什么问题。”
最初,他们关注的是自然辩证法和科技史。这两门学科原先都是抽象的基础学科,在回应现实问题上显得颇有距离。为此,他们提出 “广义自然辩证法”的概念,将自然辩证法从纯科学哲学引申到管理、社会领域。此时,从国外引进的“科学学”与他们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他们全力投入对“科学学” 的研究。1980年,在他们的建言下,上海成立全国首家科学学研究所,夏禹龙任副所长。在出版于1983年9月的《科学学基础》(与孙章合写)中,他们对“科学学”进行了理论建树,该书出版后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成为当时从事科技、社会科学和现代管理工作的广大人员和干部的指南。

《科学学基础》
但很快,现实中遇到的新问题又让他们将研究延伸至新的领域。随着商品经济的出现,面对新的经济环境,无论是企业还是地方政府的领导,刚刚从“计划经济”时代走来的他们都显得不知所措:“当时厂长、经理们只关心局部的管理问题,如生产管理、技术管理、财务管理等;而对于全局性的问题,如市场营销等,则基本不加关注,也不需要他们进行战略决策。”于是,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以把握、决策实施全局性问题为研究对象的领导科学——1983年5月,四人合作撰写了《领导科学基础》一书,这是全国最早的领导科学专著。有学者评价,该书“第一次把领导工作当作一门科学,进行了系统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现代领导工作的客观规律。”该书出版后在全国引起领导科学的学习热潮, 《领导科学基础》先后共出版了15版,印数达140万册以上。

《领导科学基础》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时的创作模式是“不拘一格”的——正如夏禹龙在自传中所提及,“我们4个人的合作方法,主要是采取不定期、不拘形式聚会的方式。在碰头时,大家来一场‘头脑风暴’,天南地北,畅所欲言,彼此交换信息、想法,在这个过程中确定新的研究方向……”这样谈话中诞生的一个典型“著作”,是出版于1986年7月的《现代化与中国》,这本书的灵感来源,正是始于当年他们利用元旦假期相约在一个旅馆的畅谈。然而也是这样“不拘一格”的创作模式,让他们能够“吸收众长、补己之短”,共同完成那些具有 “宏大叙事”的时代课题,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大量原创性的理论资源。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里,参与咨询工作、为地区战略和上海发展出谋划策,也是夏禹龙学术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夏禹龙的区域经济研究——
1983年初,夏禹龙等四人发表了《梯度理论和区域经济》一文,文中指出:根据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不能“一刀切”地搬用“中间技术”,应自觉地形成技术梯度,让一些有条件的地区首先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然后逐步向“中间技术”和“传统技术”地带转移。他们还指出,长江三角洲最有条件建设成为一个“先进技术”的经济区。一开始,“梯度理论”并不完全为人们所认同。但其实,“梯度理论”和邓小平“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先富带动后富,达到共同富裕”的思想是一致的。以此为基础,1994年,夏禹龙出版专著《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中国地区发展战略与布局》,根据当时的形势对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布局进行了构想。其中的一些见解,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家东中西部区域发展战略布局的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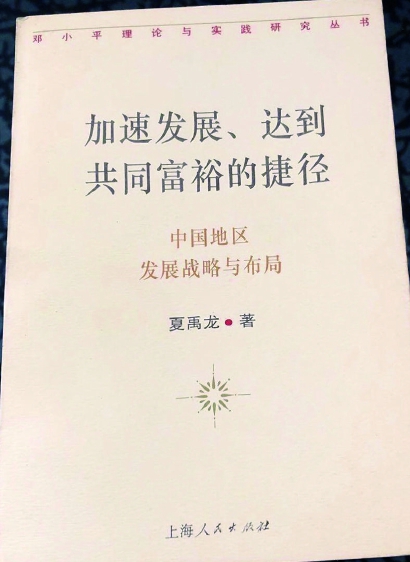
《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中国地区发展战略与布局》
在决策咨询方面,夏禹龙的另一个主要贡献是助力推动举办世界博览会及浦东开发开放。早在1984年,时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他便参与了这方面的咨询工作。
事实上,推动举办世博会与浦东的开发开放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上世纪80年代,上海狭小的市区面积严重阻碍了上海经济的发展,扩大市区成为 “燃眉之急”,但关于选址仍有争议,夏禹龙等人从区位因素及经济实情考虑,认为开发浦东比较切合实际,并希望通过世博会的举办来带动浦东的开发开放。关于未来浦东的发展定位,夏禹龙等人坚持认为,应优先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而不是仅仅为浦西的工业服务。回过头来看,这些当时的意见,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1990年,国家实施开发开放浦东战略,浦东从此驶入发展的快车道,这里崛起了全国第一个保税区、第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学者在主流意识形态研究时,要有自己的创新见解”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中国已经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先发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的特色之路。然而,正如夏禹龙所说,只有“从学理上回答‘什么是当代社会主义、在中国怎样建设这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形成和完善依据其内在逻辑联系展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才能真正增强理论自信,从而为增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打下扎实的理论根基。”于是,思考当代中国的理论自信如何建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添砖加瓦”,成为夏禹龙晚年孜孜不倦的探索。
“学者在主流意识形态研究时,要有自己的创新见解”。正如他一直所强调并身体力行着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上,夏禹龙同样是“敢为天下先”——他挖掘出邓小平当年很多有价值的重要论断,较早采用“邓小平理论”这一提法。1992年,夏禹龙与李君如合作发表《邓小平的管理思想与领导艺术》一文,获得了“五个一工程”论文奖。1993年6月,中宣部在上海召开了全国性的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议结束后成立了全国 “五大中心”,分别位于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防大学、教育部和上海社科院。其中,上海社科院的“邓中心”是唯一在地方设立的研究中心。在筹建这个中心之后,夏禹龙等人又积极创办《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杂志,极大促进了邓小平理论研究的发展。
在生前接受的一次采访中,当被问及“如何评价当前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时,夏禹龙认为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应重视基础理论的创新,“不仅要重视自然科学的、科技的创新,更要注重制度创新,而只有理论自信才能建立制度自信和远大理想。”事实上,这也是夏禹龙晚年致力最多的方向——他始终在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化的问题,正如他所说,“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被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而应该是当代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于是,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他着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当代中国条件下如何具体应用及其创造性地发展;在担任上海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和顾问期间,他曾通过与他人合著《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国家的角色和作用》《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支撑》《发展在中国的理论和实践》,以及单独撰写论文,对发展、阶级、国家等基本原理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应用及其发展作出自己的阐释。
夏禹龙还强调,要营造鼓励基础理论创新的学术环境。因为基础理论的研究,肯定不会一提出来就正确,答案的正确与否、有无价值,需要不同意见的讨论与长期实践的检验。如果一开始就把一些问题化为研究的禁区,就无法取得后续有价值的创新成果。
因为始终保持着这样对真理的赤子之心,夏禹龙被誉为学界的“不老松”。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与时俱进的学术生命力,也是因为他老而弥坚的学术毅力——在1998年离休后,夏禹龙仍笔耕不辍地发表了一百多万字论文、文章和著作。与他共事将近20年的上海社科院《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常务副主编曹泳鑫曾回忆,“夏老的学术生涯比一般的人要长。夏老退休后,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就离开科研,而是依然不间断照常上班,坚持研究,快80岁的时候还申请到一项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课题。”2015年,他还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提纲》的长文,为学界贡献着最后的思想之光:“由于我已年届九十,体弱多病,来日无多,又限于一己的知识和能力,没有可能担当起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艰巨的理论基础建设任务。只是期待引起同道者关注,大家能够群策群力,经过长期研究和探讨来完成这一任务。”2016年,夏禹龙获得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从颁奖典礼后媒体的采访可知,他还是没有停止思考,“能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继续贡献自己的看法,或许是我现在少数还力所能及的事情之一。”
2017年,夏禹龙因病逝世,享年90岁。同年,他的自传《思想之自由乃我毕生不渝之追求:夏禹龙先生口述历史》出版,书中记录了他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糅合了他的人生经历与治学道路,包含着他对历史的总结与反思。夏禹龙谦逊地说,“研究科学学、领导科学和邓小平理论,都是为了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只是对于中国进一步实现现代化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些看法。”这是他对自己学术道路的总结,也道出了一位学者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
作者:陈瑜
编辑:陈瑜
责任编辑:杨逸淇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