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汪师,不由想起初见他的情形,那是在一个满是阳光的冬日下午,复旦某阶梯教室座无虚席的文博讲座上。先生戴一呢帽,系着围巾,指间夹一支粉笔,滔滔不绝讲了两个多小时。他讲陶瓷史,从陶瓷的烧制工艺讲到各大名窑的特点,那口“苏式普通话”,那神采飞扬的神情,形象生动的比喻和随手拈来的引证,令大家如听说书般着迷。文博系列讲座多由上海博物馆专家担纲,组织讲课的朱维铮老师怕内容艰深、学生坐不住,曾预先打招呼:“博物馆的专家不是吃开口饭的,遇到枯燥乏味的地方怎么办呢?——听下去就是了。”可是,我们听汪老师的讲座,非但用不着下“听下去就是了”的决心,而是欲罢不能,如痴如醉。
后来,我很幸运地按分配去巨鹿路上的市文化局报到,再具体“落地”到中汇大厦里的上海博物馆,从事图书文献整理。在上海博物馆新领导班子组成后,汪庆正先生和马承源先生及其他领导一起,改组部门,听取意见,规划未来。其中,业务部门的重新划分对今后工作影响很大。原来的陈列研究部,集中了青铜、陶瓷、书画、工艺等许多专业人员,现改设青铜器研究部、陶瓷研究部等各部,形成按学科分类的研究、管理体系。对图书文献这一块,汪馆长亲自兼管,明确提出要深入钻研版本目录之学,重视碑帖整理。他查看善本、拓本,边看边讲;看到董其昌、改琦的稿本,连声说“阿拉真的有弗少好物事”,勉励我们予以查考,还特别介绍了陶湘《涉园丛书》的价值,嘱咐一定保护好并加以利用。对于古籍版本,他要求年轻人将《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烂熟于胸,对四库未收、丛书未见的书,又须熟知怎样查;对于碑帖中的草书,他要我们克服畏难心理,并介绍说:“拿一部《阁帖》,对照释文多看几遍。”为加强业务学习,还安排由部门内的文献专家沈宗威老先生定期开设讲座,专讲古籍版本目录,又由沈先生主持翻检古籍,将够善本标准者升格为善本,同时给我们讲解版本特征。从此,图书资料被正式纳入馆内文献学学科建设的范围,整理研究的头绪也就清晰起来。
全馆重业务的气氛也渐渐浓厚。室内老同志曾经说,“沈(之瑜)馆长对我们的要求是‘拿得出’,要做到很难”;图书资料室前主任丁义忠先生被指定负责新成立的文化交流办公室,他也说过,“老早我们做点业务就被人家说不务正业”——所说的“业务”主要是指室内主持整理出版的《上海碑刻资料选辑》和康有为手稿。记得当时主管文管会和博物馆的方行副局长,还曾经在我们根据馆藏整理的《康有为遗稿》出版、署名时,特地起了“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文献研究部”一名,写在作者栏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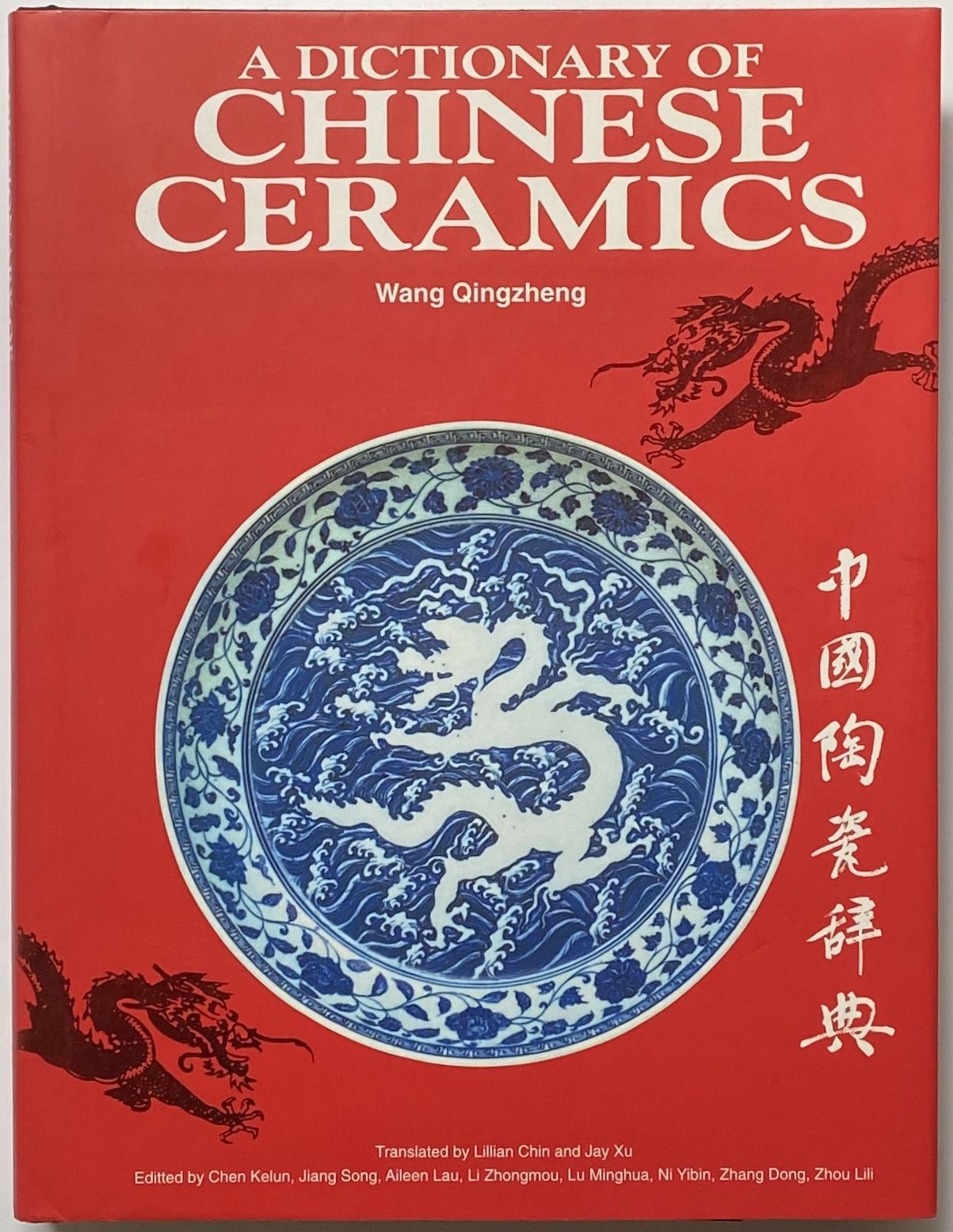
汪庆正《中国陶瓷辞典》
上海博物馆在人民广场新馆建成前的十年间(1985—1995,同人称作“马、汪时期”),对内狠抓业务,对外诚交朋友,广结善缘,经历了许多重要事情,促使全馆有了空前发展。最终,另建新馆的要求呼之欲出、顺理成章。现在说来一气呵成,当时则是“无一日无事情”(汪馆长语)。
其中,图书文献部门再次得到强化和规整。当时,从西安调来的王仁波副馆长接手分管图书文献工作,他也是爱书人,自己藏书读书数量颇巨,他常说“一个博物馆学术水平要上去,藏书就要多”。就新馆图书文献这一块功能,汪、王两位师长很早就作了规划定位。汪馆长说,国外许多重要公立博物馆都设有一个图书馆,我们新馆也要有,一方面是馆内研究需要,另一方面,图书文献是门学问,对我们来说还有个传承,就是徐森老自己是文献版本专家、碑帖专家,这个特点、这门学科我们要接下去,以后有条件的话还要向社会开放,但是要有我们的特色。这番话后来实际上成为新馆图书馆工作的中心思想:研究、特色、服务。上海博物馆要有图书馆了,这不是过去内部图书资料室的简单升级版,而是全新的、有收藏和研究特色的现代化文博专业图书馆。后来的经历证明,当时的决定有多高远,因为图书馆有一定数量的收藏,有一定特色的服务,有专业的团队特别是做出了许多整理成果,结合馆内新征集到的一批古简(即“上博简”),上海博物馆由此获得国务院颁发的首批“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称号。
新馆各主要陈列室的装修费用要靠海外收藏家、实业家捐赠,马、汪两位领导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图书馆的装修赞助费最后由香港著名收藏家社团——敏求精舍提供(故建成后对外亦称“敏求图书馆”),即是汪老师联络的结果。

汪庆正(1931—2005)
建立馆内的图书馆,首先要有特藏,即有一批属于自己特色的“镇馆之宝”。敏求图书馆之所以应该建立、也能够建立起来,就是因为历史形成的特殊馆藏条件——不是有了招牌去建个馆,而是有了藏品、有了顶层定位之后,去盘活、利用而成馆。上海博物馆曾经聚集大批文物、历史等相关学科的专家,曾经接受许多藏家的捐赠和其他机构的移交,上海博物馆还曾经是上海市文物保管(管理)委员会的所在机构,承担社会文物(流散文物)的管理职责和出口文物的检查职责(海关文物检查站),因此有大量图书文献得以聚集,其中包括与青铜、古陶瓷、字画、工艺品、考古、古文字、历史、古典文学等相关的内容。这些专业图书文献的原收藏者,名家及其后人居多,主要有徐森玉、吴湖帆、冒广生、李荫轩、钱镜塘、徐懋斋、龚心钊、丁福保、叶恭绰、郑家相、孙伯渊、孙鼎、戚叔玉、秦康祥、罗伯昭、康保庄、朱孔阳等,他们原是为治学、收藏研究而藏书,因而在捐赠文物时顺便也捐赠了相应文献。馆藏从古代青铜器名著《宣和博古图录》元刊本,一直到现代青铜器名家名作;从古代陶瓷名著《景德镇陶录》,一直到现代陈万里等撰写的专著,还有吴湖帆的书画鉴定笔记、邓之诚流传一时的名作《骨董琐记》稿本,地方文献可以豫园主人潘允端的《玉华堂日记》原稿为代表,钱币拓本可以罗伯昭《沐园四十泉拓》为代表,印谱钤印本中更有大批精良制作。这些都是既体现特色又服务于上博各学科的宝藏。
有了收藏还须有合理管理和专业团队。汪老师特地关照要通过电脑著录,鉴别好版本,发现新善本、弥补旧信息。老的图书登记卡片大多不够规范,作者、版本信息缺失颇多,不少还查不到相应依据,几乎是“死无对证”。这时候去问汪老师,他往往很忙碌,说“侬夜里10点钟以后打这个电话”(指他家中一个号码),每次电话求教,汪老师总能言简意赅,解决问题。经过大家努力,刨根究底,居然“起死回生”,一些古籍、文献的来龙去脉、版本特征获得解决。在进人问题上,汪老师基本是先看一下应聘人员的文章,再找机会问些问题;有时在文章下写“甚佳”以鼓励,有时拿篇复印的某公手稿让释文标点。图书馆后来渐渐聚集起古籍文献专业毕业的多位研究生,出了许多成果,尤其是完成了冒广生、吴湖帆、戚叔玉等名家文献的整理,给捐赠者以交待,也共飨社会人士。另外值得一说的是古籍文献的修复,敏求以专门岗位招聘专人主持,目前已和上海图书馆共同取得古籍修复非遗传承人的资格,这应该是汪老师料想不到的喜讯了,而“前人栽树”之功,我们永不会忘记。
除了馆内服务外,敏求还对外接待专家、学者,为学术交流提供一方乐土。阅览室中专设若干小间,原想提供短期研究之用,结果在对外交流中也派上了大用场。芝加哥大学教授夏含夷在此用功数月,完成了《古史异观》的写作;哥伦比亚大学东语系李峰教授介绍其研究生尼古拉来此,完成了有关碑刻方面的博士论文;还有许多专家学者来此查过资料,“有功”而返。
作为上博的一个部门,敏求图书馆“埋头故纸堆”,做了这些应做之事;我想,也只有孜孜矻矻,才能告慰汪老师,不辜负前辈们的期望,当得起上博的声誉。


左2为上海博物馆敏求图书馆馆长顾音海、左3为上海博物馆汪庆正副馆长、右2为饶宗颐先生
作者:顾音海(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馆员)
编辑:陈韶旭
责任编辑:李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