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子曰诗云,尚属旧式文人之积习,那么,王尘无还有超越同侪的另一特长,不可不提,此即从事长篇通俗小说的创作。唐、王的共同好友陆小洛即“常读尘无所辑之报,”且以其长篇小说《江湖艳史》为上,而另一长篇小说《欲海鸳鸯》则等而下之。唐大郎评论道,“尘无所作乃于江湖欲海之间,亦使此公啼笑皆非矣。”并作怀尘无一诗:“记从马路见芳踪,一件大衣像斗篷,无复能诗偏作影,却因相骂颇怀公。江湖艳史双肩上,欲海鸳鸯一望中,不尽沧桑人事也,尘无竟似有尘封!”(《怀尘无》)慨乎言之。而近现代长篇通俗小说的创作,固然受到西洋翻译文学的影响,更导源自中国漫长的说部传统,尤其明清白话长篇小说传统;其作者亦多属与古为徒的旧式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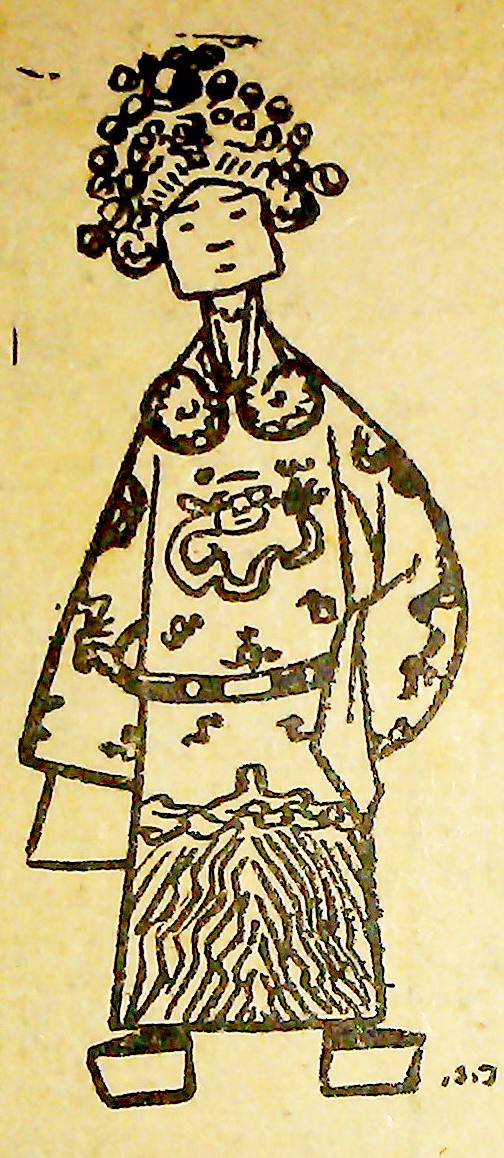
唐大郎漫画像
与王尘无日常酬酢者,除上文提及的唐大郎、邓钝铁、陆小洛,至少还有陈灵犀、施叔范、王小摩、李培林、薛白雪、蔡兰言、曹聚仁等人(《诗书画三绝荟萃一堂》《酒令》)。有一次施叔范自华北归沪,适值王尘无返自杭城,诸人宴饮,“席上行口字令,各人念一句古诗,或现成名词,或成语皆可,惟其字中须有口字,或字之构造中,附有口字者”,如唐大郎“诵‘一辆汽车灯市口’,则顺次而数,第五人与第七人皆饮酒,又如灵犀言‘皆大欢喜’,则第三与第四人,各饮两杯,盖欢喜二字,乃有两个口字也。于是有人念浑浑噩噩一语,噩噩两字,每人各吃四杯,而座上杨君,忽念一人名曰‘沙不器’,于是第三人亦饮四杯,一时谑浪笑傲,喧然并作。当入席之始,各人座上,皆有名单,惟并不直写其姓名,而作类如廋语之文句”“愚号大郎,则书曰‘且问郓哥儿’,直以愚为三寸钉矣。又如灵犀曰‘一点通’,蝶衣曰‘金粉’,尘无则曰‘玉洁冰清’,胥出粪翁之手”。(《酒令》)
1938年夏,早已归乡的王尘无,以病犯沉疴、咳血而死。对其死状、死因及此事如何播闻至沪、友人如何不胜痛悼等情事,唐大郎亦有相当亲切之记述:
战后,兄养疴里门,至上月始闻其将避地来孤岛,吾人方欣慰故人之重来,讵顾望久之,而踪影杳然。昨日粪翁先生得海门朱公羊君来函,谓尘无于上月二十六日晨七时,以咯血过多,致溘然作古。粪翁得书,遂告灵犀,灵犀以电话询培林,培林复以电话询尘无介弟。其弟尘笠,执事于本埠某钱肆,初问尘无如何矣,则谓不久且得家报,三哥虽在病中,然无大碍也,因告以公羊之书,其弟大恸,陡忆一二日前,有乡人来,初未言尘无已死,曷往觅之,一询究竟,以是更觅乡人,乡人固言,尘无已病死,惟渠离乡时,王家人嘱其勿传尘无噩耗,使尘笠伤心也!自是尘无之死且证实,尘笠乃复踵灵犀许,白以乡人之言,尘笠已泣不可仰矣,朋友闻者,无不怆然,今将由至友若干人,为之开一追悼会,又为之延高僧追荐。读吾报者,亦有佩尘无之清才绝调者乎?读此文竟,又岂可不临风雪涕,以吊此凄凉绝世之才人哉!(《尘无以呕血死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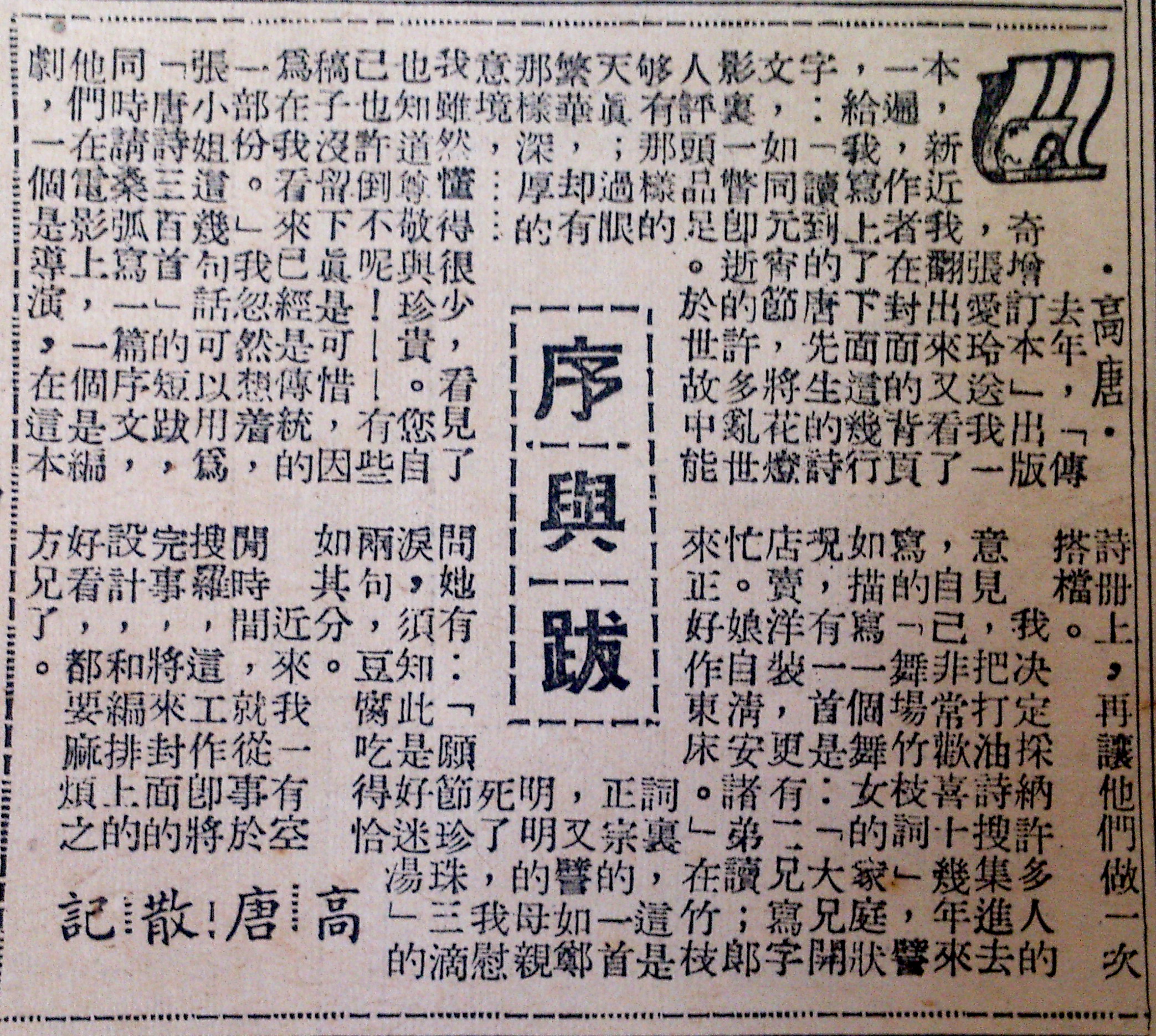
唐大郎(高唐)《高唐散记-序与跋》版面
三年之后,尘无遗著《浮世杂拾》乃由长城书局梓行。此书系“长城文艺丛书之一”,由桑弧特为搜集、整理、编辑,以纪念亡友。全书收其《寂寞的街头》《三和尚的死》《卖笛的老人》等抒情散文26篇,另有《小引》、柯灵序言、桑弧所撰《校印后记》。据柯序可知,这些文章是王尘无生前亲手从各报上剪存,“还在稿端注明‘改’或‘大改’字样,预备重加饰润”。但桑弧《校印后记》则称之为“中国文坛”“最优秀的散文作家中的一个”,还与陆小洛异口同声、咸谓其为“鬼才”,似不免过誉甚矣。
《浮世杂拾》一集,未及王尘无之旧体诗文、通俗小说、影评作品,但影评、杂文方面此后尚有《王尘无电影评论选集》(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编,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可作补充。该书末编,另收不少关于王尘无的回忆资料,唐大郎的大量论述当然被遗漏在外,而王氏的诗文、小说之什,至今仍未见结集出版。
其实,桑弧曾有意将王尘无诗集及《吞声小记》两种、施叔范之《酒襟清泻录》及诗稿、钱梯丹之《陇上语》《西征闻见录》及《破家赘录》(均为连载作品),“亦并付欹劂”(《纪念集》误作“欹厥”),“然纸价日增,印刷费复极昂贵,使为其友者,欲偿素愿不可得,即此《浮世杂拾》之产生,盖亦耗桑弧之绝多心力矣”。(《亡友尘无》《桑弧拟印书》)此后终未见下文。印证了唐大郎这番颇有几分预言色彩的甘苦之言。
从唐大郎关于王尘无的这些记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另有一个作为旧式文人、小报文人、通俗小说家的王尘无,已悄然浮出历史地表。更重要的是,这多重身份、面相的王尘无,不仅与左翼影评人王尘无同在,而且同为一人,令人殊感意外。此一点,我们不读《纪念集》,或恐难以知悉。不止此也,正如前引拙文所论,二三十年代的左、右翼文人、影人之间,也并未如我们想象得那样势如水火、老死不相往来,而在形形色色的都市空间、公私场合晤面,且在报章杂志、言论空间多所互动(“论争”何尝不是一种互动?),恰恰是其常态,至今犹然。
作者:王贺
编辑:刘迪
责任编辑:任思蕴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