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居室求学(二十七)
上海徐文堪先生,我在以前仅知其名,知道他供职于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在王元化主编的《学术集林》丛刊扉页,他的名分是“主编助理”,与主编的青年学生傅杰的名字并列。业内人都清楚:名分不重要的人,往往干的是实际编务,是扛着具体、细微、繁杂的组稿、编辑、出版工作的。
昨晚读报,读到荣新江教授的《悼念徐文堪先生》,总算了解他的生平和学术贡献,知道了他在编辑工作之余,还在“吐火罗语及吐火罗人的起源”这个冷门绝学领域有专著,且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荣新江教授在悼文中回忆,他在1986年去苏州参加中亚文化研究会时认识徐先生,亲见因小儿麻痹造成腿脚不便的他,虽然还没出过国,“却对欧美各种西域语言研究情况了如指掌,说起来如数家珍”。算起来,那时的徐文堪先生才三十几岁,他对国际学术领域里的研究动态,已令专业人士感到吃惊。
自从季羡林先生最早在北大东语系奠定几种冷门绝学的基础后,中国学者对西域古文明的研究代不乏人:已病逝的段晴教授;多年在新疆从事野外考古调查,已编辑出版多种著作,又遭车祸不幸去世的杨镰研究员,就是这个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徐文堪先生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但他的本职工作是编辑。他是著名的文献学家徐森玉先生的哲嗣,究竟有没有家学的传承?我不得而知。我只从荣新江教授的悼文里,看到了他的为学精神和学术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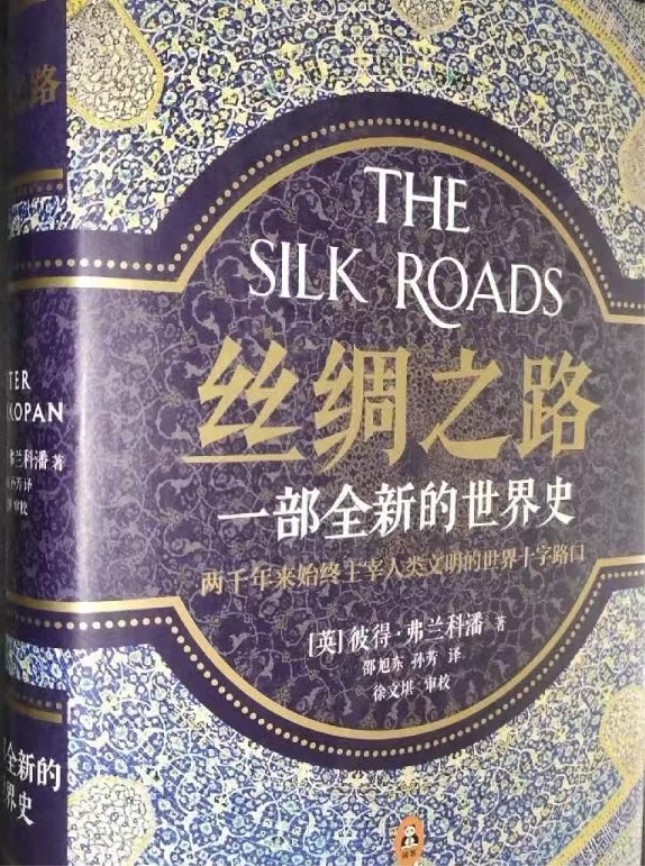
按我的习惯,天天读报,读完就摞在旧报上,不再想它。但是,昨晚读罢荣教授的悼文,对徐文堪先生在国外学术会议上的一次遭遇,心有不平之气,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荣教授回忆他和徐先生共同参加的一次国际性的会议:
一次是2000年3月8日,我和徐文堪、林梅村、水涛一起飞往洛杉矶,转圣迭戈,在Quality Resort旅馆住下,我和文堪先生同室,问学兼照顾他。3月10日正式参加美国亚洲学会的年会,整个会有两千多人,分成几个时段,每个时段有若干分会场,随个人所好,打游击式地听讲或报告。我们参加的是3月11日梅维恒主持的圆桌会议,题目是新疆古尸对中国史前史和历史时期研究的重要性。梅维恒开场白后,丁爱博(Albert E.Dien)首先发言,他对梅维恒的看法有所批评。然后依次是水涛讲甘肃和新疆史前文化的关系,林梅村讲新疆的史前石堆墓,我讲吐鲁番的三种葬俗,最后是爱尔兰皇后大学的马洛瑞(James Msllory)讲新疆古尸的学术意义和限度。各位发言后,梅维恒让徐文堪提问并讲述自己的看法。其实文堪先生对这个会议主题最有发言权,但他身份是编辑,按照美国学术会议的不成文规则,发言者一般都是来自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人,他们不认为编辑能做学术研究。文堪先生一时兴起,讲的时间有点长,在座的许多人想发言质疑梅维恒的观点,结果袁清教授起来打断了文堪先生的发言。会后我赶紧把两位拉到一起解释,一位是原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袁同礼的公子,一位是北图善本部主任徐森玉的哲嗣,可惜他们这次才得相识,于是也就一剑泯恩仇了。
荣教授没有讲述这次学术会议上徐文堪先生发言被打断的细节。我猜测,当发言被无礼打断时,可能发生争吵。总之,现场是尴尬不愉快的。按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规则,发言者是有时间限制的,一般情况下,发言者都遵守规则,在规定的时间内讲完自己的观点。看荣教授的讲述,这次会议只安排徐文堪先生提问,并没安排发言。这就是说,提问者像记者一样,只能提问题请发言者再阐明他的观点,提问者是不可反宾为主的。不料,“文堪先生对这个会议主题最有发言权”,他就忍不住滔滔不绝,以致引起发言被打断的难堪。我想,假如徐文堪先生是个聪明机灵的人,在国内时就给自己头上戴几顶放光的学术帽子,如此,到了并不怎么了解他的会议场所,“先声夺人”,同行也会对他另眼看待。哪怕是在号称“自由民主”的美国,您只以“编辑”的身份出席学术会议,您还是个身有残疾的学者,就这样不受待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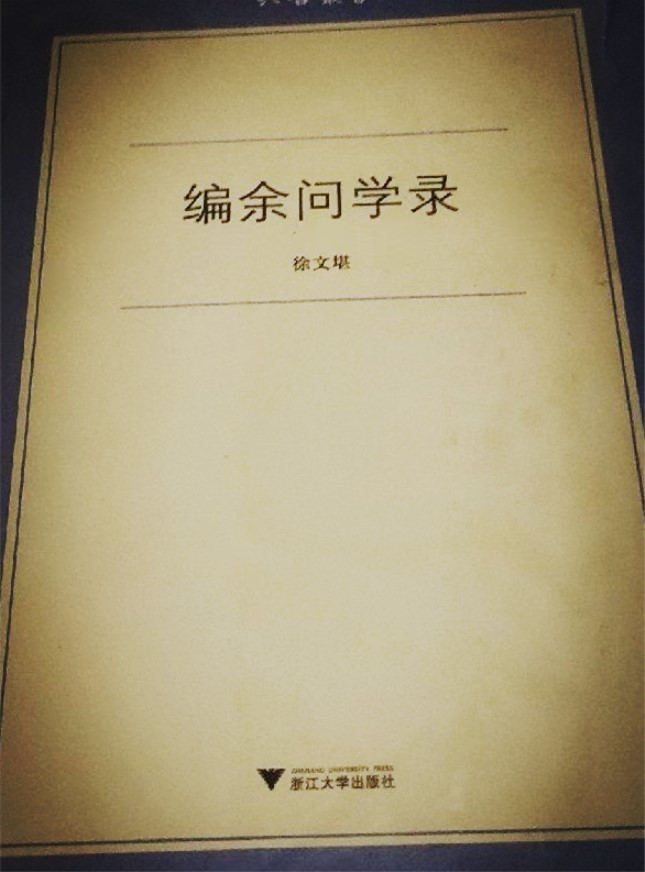
我国近代出版业,是以开启民智、文化教育救国为己任的。因此,各个时期的出版行业,都不乏学有专长的饱学之士:远的,如张元济,进士出身,早有功名;近的,如杨伯峻、周振甫,术有专攻,都有著述;现在的,如钟叔河、朱正,编辑、著述都卓越。他们的职业都是“编辑”,他们的学术成就绝不比在大学里、学术机构里那些专门搞研究的人差。
多年前,有一位在报纸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约了正在走红的张中行先生的一篇稿子。按稿件的审批程序,分管领导不同意发表。朋友反复对领导说张先生多么有名望,领导却说:“什么名人啊!我打听过了,他就是人教社的一个老编辑。”领导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就对张中行“人肉搜索”,已知他是“编辑”且成色“老”。我的朋友于是无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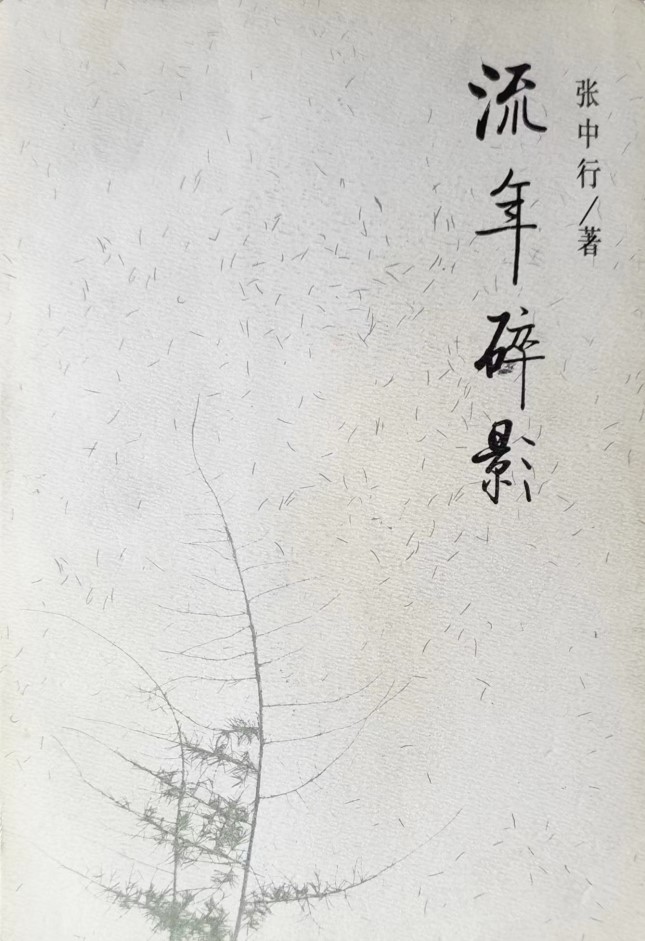
>>作者简介:
卫建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审,著有散文随笔集《寻找丹枫阁》《陈谷集》等。
作者:卫建民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朱自奋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