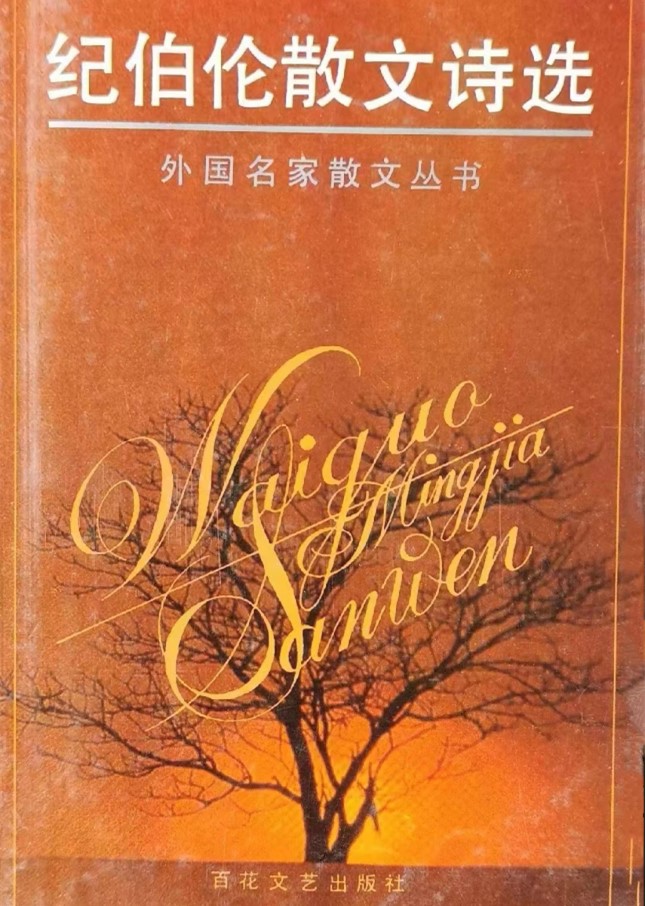
前一段时间,线上举行的“世界图书生命指数学术研讨会”,引起了我的兴趣。
书籍的生命,并不是今天才提出的话题;不过,以北京外国语大学何明星教授领头研究世界图书生命,有组织、有计划、有方法的正式作为课题项目研究,我是第一次知道。书籍在世界上的存活时间,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书籍本身的价值决定的。不管是死海古卷,还是流沙坠简,一旦被人发现,它们的价值就显现。我们在今天读2000年前的孔子、老子、庄子,读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并不觉得难懂。这些中西贤哲的著作和言论活到了今天,在四海传播,早已成为世界文明遗产,进入不朽之域。
据介绍,何明星教授团队,是以图书的再版次数为核心数据,以1920—2020年这100年间再版500次以上的图书共511种,结合著者的国籍,构成世界图书的生命数的。线上的研讨又引起我注意的,是黎巴嫩作家纪伯伦的《先知》,研究团队据OCLC数据库检索,发现其再版929次,是统计中图书再版次数最高的。我早知道,纪伯伦的作品主要是《先知》,在1931年时就被译成18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OCLC数据库包括多少种文字?已经发行到多少国家?我没再进一步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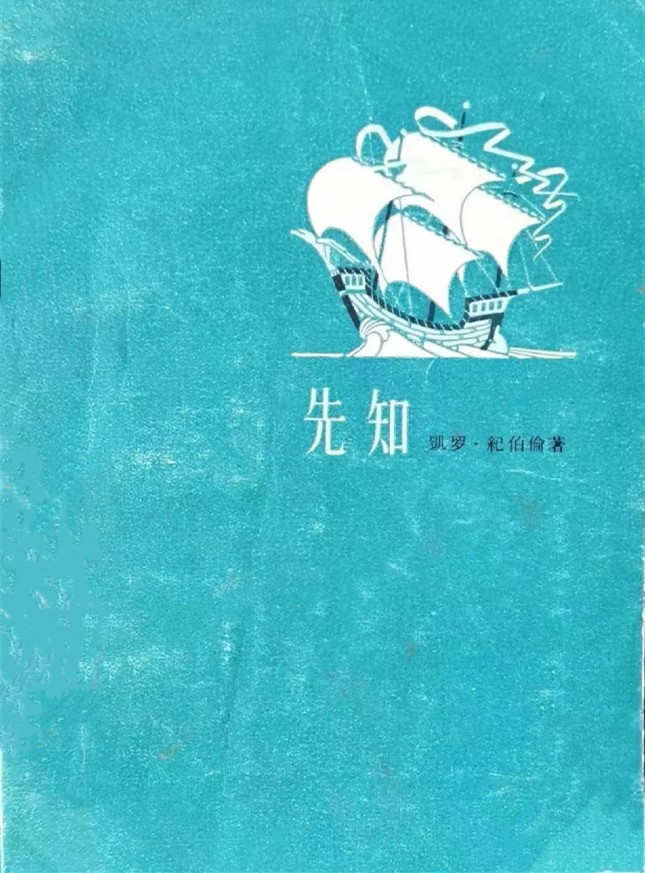
看了线上研讨会新闻,我取出自己的几种纪伯伦著作,又翻阅一遍,旧书旧藏又使我回到了过去的读书生活。
我最早读的《先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冰心译,书中有纪伯伦自己的美术作品。这本小册子,来自机关图书馆的处理品,品相如新。这本书在1957年被机关图书馆采购,图书馆工作人员登个记,盖个章,长睡馆内40年,最后被“剔除”到我手上。
198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先知》,还是冰心的译本,是我在书店买的,译本收入新的内容。湖南人民出版社还出过以“泪与笑”为书名的纪伯伦作品集,由多人翻译。
吴岩先生译的《流浪者》《纪伯伦散文选》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是编者谢大光兄送我的。在《流浪者》译后记里,吴岩先生有一段话令我感动,他说起翻译的过程:“首先是每天清晨继续译一点,以求得美学上的享受;接着是把译稿搁一搁,然后再进行冷处理,即逐字逐句校订一遍。”在一天的开始,在晨光里翻译纪伯伦富有哲理、诗意盎然的美篇,再精心打磨,是翻译家工作时的自我写照。

纪伯伦是中东人,在美国受教育,又去巴黎学绘画,曾与罗丹有交往。他以阿拉伯文、英文创作文学作品,以箴言或诗篇的形式写出隽永、优美的散文诗,以不多的作品赢得全世界读者的热爱,成为著作再版率最高的世界性作家。看来,书籍再版的次数,并不决定于书籍的字数。纪伯伦早就知晓精神产品的寿命,在《两首诗》里,他曾写道:
许多世纪前,有两个诗人在到雅典去的大路上相遇,彼此见面,很是高兴。
一个诗人问另一诗人道:“你最近在写什么?你的七弦竖琴如何?”
另一诗人自豪地回答道:“我刚写完我的最伟大的诗篇,也许是迄今用希腊文写的最伟大的诗篇。这是一首向至高无上的宙斯神祈祷的诗篇。”
于是他从斗篷下取出一卷羊皮纸,说道:“喏,你瞧,我把诗稿带来了,我很高兴读给你听。来吧,让我们坐到那棵白色丝柏的树荫下去。”
诗人便朗读他的诗。那是一首长诗。
另一个诗人友好地说道,“这是一首伟大的诗篇。这诗将世代相传,你将因此扬名千古。”
第一个诗人平静地问道:“那么你在最近的日子里写了些什么呢?”
另一诗人答:“我写得很少。只写了八行诗,纪念一个在花园里玩耍的孩子的。”接着他就背诵了那八行诗。
第一个诗人说,“不赖,不赖。”
于是他们就分手了。
如今二千多年过去了,那八行诗仍在每个人嘴里吟咏,大家喜爱它珍惜它。
那首长诗虽然也确实世世代代在图书馆里、在学者的藏书楼里传下来了;虽然记得这首诗,却既没有人爱它,又没人读它。
纪伯伦这首散文诗,谈到了文学作品的体量、价值和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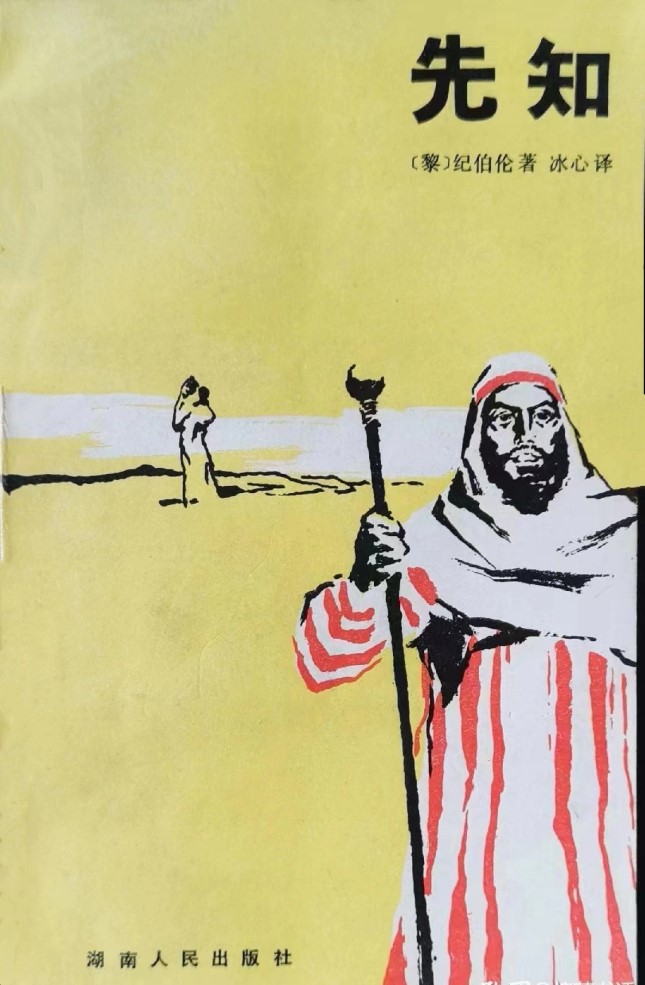
湖南版,冰心译《先知》,有一部分是纪伯伦的短句《沙与沫》,是诗人灵感一闪的痕迹:
* 只有一次把我窘得哑口无言,就是当一个人问我“你是谁?”的时候。
* 奇怪得很,对某些娱乐的愿望,也是我的痛苦的一部分。
* 当两个女人交谈的时候,她们什么话也没有说;当一个女人自语的时候,她揭露了生命的一切。
* 一个女人可以用微笑把她的脸蒙了起来。
* 树木是大地写上天空的诗。我们把它们砍下造纸,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空洞记录下来。
* 和你一同笑过的人,你可能把他忘掉,但是和你一同哭过的人,你却永远不忘。
纪伯伦的这些智慧短句,在泰戈尔的作品里也常见。可见,东方的哲人和诗人,从不是那些喜欢饶舌、把话痨当才情横溢的名人。
我的几种纪伯伦作品集,读过后就常年放在书柜顶层,多年没动,因看到线上讨论书籍的寿命涉及到他,就取下来翻阅并写一段书话。对惜墨如金、吐金唾玉的纪伯伦来说,我的话还是多了,远远不如他写的那位只写过八行诗的诗人。惭愧!
>>作者简介:
卫建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审,著有散文随笔集《寻找丹枫阁》《陈谷集》等。
作者:卫建民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