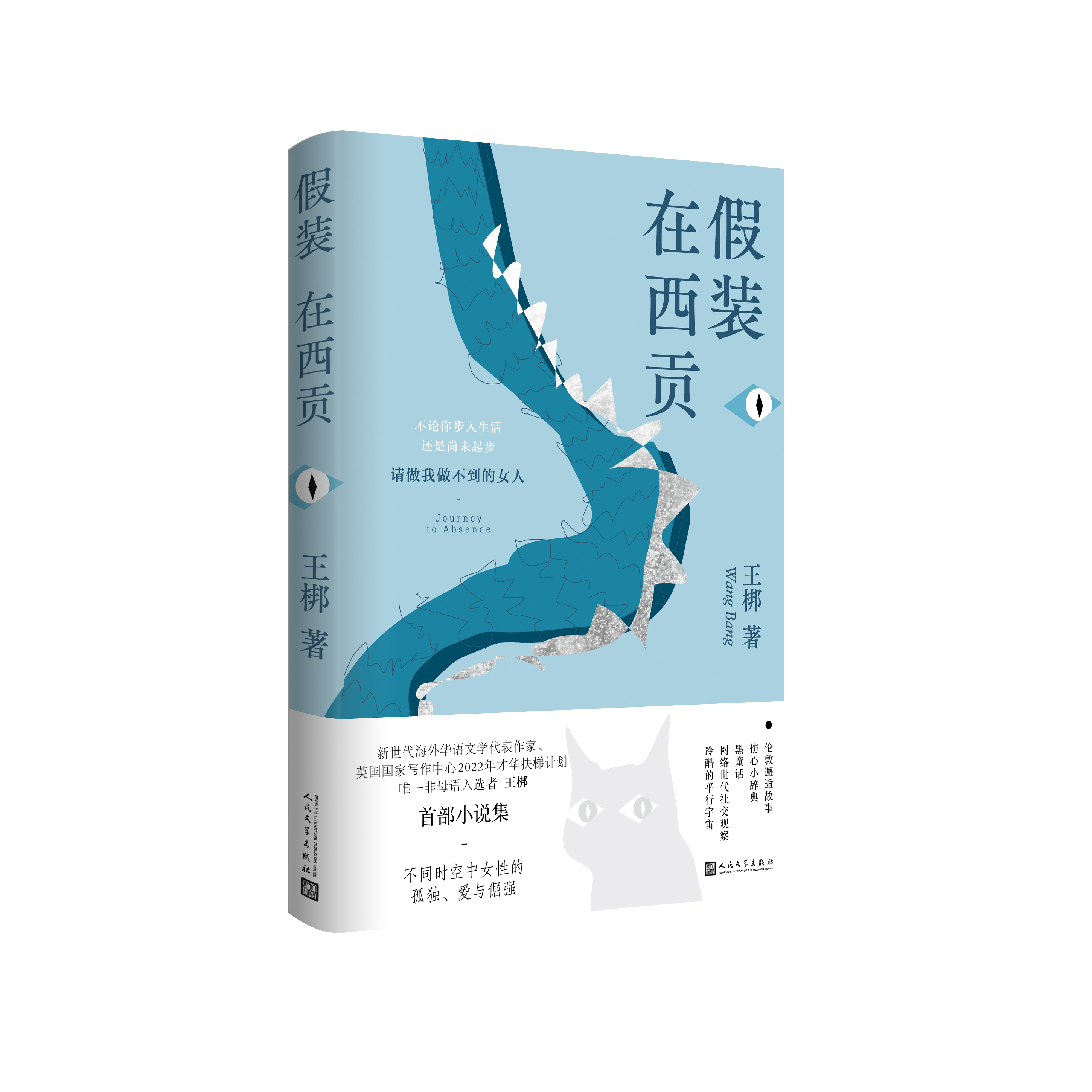
《假装在西贡》
王梆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王梆首部小说集《假装在西贡》十个短篇小说,讲述了不同时空中女性的孤独、爱与倔强。她们不论脚踩南方故土、英伦他乡还是未来废墟,都敢赤脚蹚入生活的泥塘,活出自己的生机。这本书写尽当代女性爱莫能助的向上的冲动,以及低头踟蹰间猛一昂首的振奋,同时又和盘托出网络世代的精神流浪、颅内风暴与悲欢遭际;兼采中文和英文语感的优势。
文学评论家戴瑶琴称王梆的写作超越了海外华语小说的视野:
王梆是社会观察者,创作融入了她对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复合思考。王梆耐心走进城市各个角落,先亲身接触不同阶层生活后,再关怀底层人群。“底层书写”拓宽了海外华文小说的视野及题材,她面对来自东亚、东南亚、东欧的广义“新移民”群体,统称其为流浪者,写作不再局限于中国“新移民”圈、不再追索身份认同问题。他们被不安定和不安全所裹挟,“不确定感浮游在他的宇宙中,构成他自己的弱小宇宙”。
>>创作谈
我的原生地是一枚维奥尔琴
维奥尔琴自出生起,就是一种忧伤的乐器。它有六根弦,每一根都比另一根更更幽暗沉郁。十五世纪那些失去自由的女人们,将身体贴在石墙上,倾听它那跌宕起伏的复调,像倾听流水蚀刻一座伊甸的钟乳岩。但法国作曲家Sainte-Colombe依然觉得它不够悲伤,为了与他那过早离世的爱人通话,他在它的琴身上又加了一根弦,它就像一根十六世纪的电话线,承载着由此刻通往另一个世界的语言。
我的原生地也是一枚维奥尔琴,自离家的那一刻起,我就背着它四处旅行。海平线上船帆般升起的新大陆,异国的钻石和珠蚌,对移民生活的展望……任何新鲜事物都无法斩断我对原生地的眷念。每当深夜在清冷的月光下醒来,我就会看到我和过去的我身影重叠,而我的原生地,一枚隐身在墙角的维奥尔琴,就会兀自拉奏,一如布罗斯基那无处躲藏的母语。此时,我多渴望我也有属于自己的第七根弦。
我找到小说,我任由教堂的敲钟人劫持我的睡眠;我学习和黑暗相处,锻炼我的听觉;在黑暗中,我用松香打磨每一个句子;我期待我的小说变成我的第七根弦。唯有如此,我才能更充分地表达我对原生地的感受。我的感受是如此复杂、纠结,包含着一个汉语笔行僧所有的艰辛,有时需要借助阿特伍德式的想象,更多时候,必须倚赖女性的体验才能抵达真实。那是一种有别于男性作家书写家园的经验,他们的疏烟明月、微雨落花和落叶归根,对她们来说,很可能就是茨维塔耶娃的涅瓦河。在这个层面上,我更像一个倾诉欲茂盛的吉普赛女人,我的故事,既关乎我的原生地,亦关于世上的其他地方——归根到底,关乎女性的挣扎、抗争与坚持。
我笔下的女性都十分决绝,不善媚术,从根本上,缺少某种容纳父权主义的润滑剂。她们和英国小说家苏菲·麦金托什(Sophie Mackintosh)的女主人公们是如此相似,全身上下都是硌人的骨头,触感有如锋利的燧石。比如《女巫和猫》里的“少女女巫”,在被施行“切除记忆”的手术之前,像守卫着她的宠物猫一样,坚定地守卫着她的记忆;《钩蛇与鹿》中的女病人,无视康复医院的规定,即使遭受着各种肉体和精神惩罚,也势必要私自外出。在写《天青》那个小说时,我犹疑再三,最终还是让女主人公选择了自杀。一方面是出于“宁为玉碎”的那种古典美学的考量;另一方面,正如乔治桑在她的小说《Mauprat》(莫普拉)里的箴言:“我们不能将我们人生的活页一页页撕掉,但我们可以把一整本书扔进火堆。”
《假装在西贡》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小中篇,它也是我向加缪致敬的一个作品。我喜欢加缪那种漫不经心,绝望,像天气那样出其意料、反复无常的语言。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穿着这套语言盔甲,游走在变质的,冷漠的城市空间里,用最消极的姿态,不合作地,与乏善可陈的(为女性量身定做)社会生活对峙。
去英十年,我只写了一个关于海外华人的短篇,它的女主角是一位底层华人女性,在伦敦唐人街鱼龙混杂的地带讨食。去掉异国那块布景,舞台上再现的,其实还是原生地的丛林。在丛林里,生长着一种与神谕无关的异卉,无论周遭环境如何芜杂,龌龊,无论她的枝干被压得如何低微,她都保持着一种唱诗般的、上扬的姿态。《伦敦邂逅故事》里那个罗马尼亚女清洁工,《奶牛》里的送奶工,《巨岛海怪》里那个穷困潦倒的小提琴女教师……我笔下的大部分女性,都秉持着这样一种姿态生活。

>>作者简介
王梆,旅英作家,著有非虚构作品集《贫穷的质感》、电影文集《映城志》等。
作者:王梆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