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一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十四节气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上古农耕文明,其源远流长比得上檀公簋、后母戊鼎这些“物质文化遗产”。不过,和青铜器一经铸成便万古不易不同,二十四节气的成型之路却十分漫长——不妨将其视为由二十四个成员组成的“天团”,这个组合萌芽于西周时期,其后经历了多轮扩招与裁汰,终于在数百年的岁月中打磨成如今的阵容。成员之间的竞争可想而知地激烈,因此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名单:比如战国时期《管子》记载的“三十节气”,其中“地气发”这一节气至今还能在青海河湟一带寻到残存的风俗印记。
霜降不是最早被确定下来的节气,但从《礼记·月令》中的“霜始降”、《诗经·七月》中的“九月肃霜,十月涤场”中不难发现霜降悠久的“家世渊源”。比起“四立两分两至”,霜降的标识性似乎也不算分明,但进一步观察就能发现,这一节气有着独特的分野:霜降,是一年之中昼夜温差最大的时节。时间大约在农历九月,太阳到达黄经210度,万物毕成,毕入于戌,阳下入地,阴气始凝——如果要为北半球的渐寒之路找一个起点,那这个起点便落在霜降。
“霜降”是主谓短语。“霜”是名词,“降”是动作,短短两个字,其实包含了丰富的情节。秋季夜晚散热快,温度会降零度以下,空气中的水蒸气会在地面或植物上直接凝结形成细微的冰针,这便是霜。大约周秦时期的古人以为霜由天而降,因此将初霜时的节气取名“霜降”,这种看法虽然不甚科学,却无疑更加浪漫。
从气象学的角度来看,霜的形成是因为巨大的昼夜温差,因此霜降中的“降”不妨移风易俗地理解为气温骤降。不过古人却用了一个故事来对此进行解释——恰如《淮南子·天文训》所言:“至秋三月,地气不藏,乃收其杀,百虫蛰伏,静居闭户,青女乃出,以降霜雪。”也就是说,霜降之所以寒冷,是因为主管霜雪的青女于此时出关。不少文人为此对青女颇有微词,如寒山的“屡见枯杨荑,常遭青女杀”,姚鼐的“今年青女慵司令,九日黄花未吐枝”——杨的枯萎和菊的晚开,都成了青女的罪过。倒是李商隐的《霜月》豁达一些:“初闻征雁已无蝉,百尺楼高水接天。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
霜降初到,豺正开始捕获猎物过冬。古人认为“祭天报本也”,喜欢将动物界罗列食物的行为视为祭祀,七十二侯中有獭祭鱼、鹰乃祭鸟,连同豺乃祭兽,分别对应着初春、初秋和深秋时节,也映射着古人对天人合一这一理念的朴素认知。接着,草木继续黄落、万物逐渐凋零,深秋的凛冽之气也一日浓过一日。再后来,蛰虫进入冬眠状态,天地开始岑寂,经历了春耕夏耘和秋收,人们跟随大自然一道休眠敛藏,以迎接下一个春天。
四季轮回是天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但霜降在千百年中华文明的浸润下,却在人们心中留下色彩鲜明的文化印痕。“霜降杀百草”,那是农人对一年收成的质朴期待。“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向咸阳”,那是诗人对因霜降而起的念亲之感的文学概括。而盛行千年之久又最终消亡的旗纛祭祀,则是军人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对将士们独有神祇表达敬畏的行伍礼仪。这三种截然不同的霜降意象,让深秋的凌冽有更深沉的内涵。

【农人的草木】
对于农人来说,露与霜的变化直接影响着田地里的生计。
中原地区谷雨断霜、霜降见霜,这段没有霜出现的时节被称做无霜期。在无霜期,热量资源丰富,大自然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着丰富的物质基础,因此霜降的到来也预示着农人们一年劳作进入收尾阶段,可以准备冬休了。这种休憩不止于农人,《礼记·月令》有言:“霜始降,则百工休。”霜降之后百工停止劳作开始休息的作法,既是顺时,也是因为天冷不便于工程或手艺制作。
关键的时间节点自然会孕育出众多的农谚。关于霜降的农谚,大多带点说教意味,比如“寒露不算冷,霜降变了天”“霜降霜降,洋芋地里不敢放”“霜降不出菜,冻坏你莫怪”。在云南宣威,旧时还有“霜降卜岁”的习俗以有霜无霜来判断来年的收成,所谓“霜降无霜,碓头没糠”“霜降见霜,米谷满仓”——如果霜降这天没有降霜,用来捣米用的碓头都不会沾上米糠,若是见了霜,来年的米谷则能填满粮仓,这与另一句流传更广的农谚“瑞雪兆丰年”倒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霜降霜降,降了霜则百工休,不降霜又有“碓头没糠”之虞,所以这劳作的休止符还是划上为妙。或许是为了补偿农人们的辛劳,霜降却以另一种方式准备了礼物:经历了霜降考验的农作物,往往口感更为出彩。早在西汉,氾胜之便在其农学著作《氾胜之书》中记载了“芸薹(萝卜)足霜乃收,不足霜即涩”的现象。农谚里说得更直接:“霜打的蔬菜分外甜。”
其实何止是蔬菜,柑橘、甘蔗等不少水果都是被霜打过之后更为甜美可口,因为这些果蔬启动了“防冻保护模式”,用糖水冰点低来保护自己。比如青菜——青菜本身含有淀粉,淀粉既不甜也不易溶于水。霜打后,青菜里的淀粉会降解,转化为蔗糖、葡萄糖和果糖等。糖分能增加青菜的抗冻性,使其不易被冻坏。北方人钟爱的大白菜、南方人青睐的小油菜、莴笋、白菜薹等都属此类,经霜打后口感更好,而且容易煮软。王景彝《琳斋诗稿》有句:“紫干经霜脆,黄花带雪娇。”民间亦有“梅兰竹菊经霜脆,不及菜薹雪后娇”的民谚,霜打后的果蔬居然能卓然凌驾于花中四君子之上,却不知吵嚷着“无竹令人俗”的苏轼做何感想呢?
放下了锄头,农人们方才有了丰富的时间准备各种仪式活动。作为秋天最后的节气,霜降受到了百姓普遍的重视,各地如祛凶、扫墓等习俗林林总总,祈求的则是殊途同归的来年风调雨顺、生活幸福安康。
明清时期,霜降习俗品类丰富且颇有趣味。广东高明一带,霜降前有“送芋鬼”的习俗。村民们会聚集起来,用瓦片垒成一个梵塔,然后点燃堆在塔里面的干柴,柴火烧得越旺越好。直至大火将瓦片烧至通红时,人们推倒梵塔,然后将芋放置在烧透的瓦片下,称为“打芋煲”,待芋被烤熟后,便将瓦片都丢至村外,即称之为“送芋鬼”。明人将重阳与霜降结合,在深秋时节吃“迎霜麻辣兔”、饮菊花酒;清人还有在霜降期间吃迎霜粽的习俗。当然,霜降的氛围也可以很热烈——在京城、苏州等大都市,霜降后斗鹌鹑赌博则广为流行。将鹌鹑藏于彩色袋中,如果天气过于寒冷,还要外加皮套,笼于袖中,聚而斗阵。好斗的鹌鹑显然奇货可居,正如陆启泓《北京岁华记》描绘富家子弟所说的那样:“霜降后,斗鹌鹑,笼于袖中,若捧珍宝。”当然,对于这些市井顽主来说,霜降背后的耕作之苦就显得过于遥远了。
似乎大自然也了解到了霜降对于寻常百姓的重要,于是通过一封特殊的“函件”提醒人们这一时节的到来,这封“函件”文人们称为霜信,信中的“字句”则是鸿雁南飞的轨迹。元好问《药山道中》诗云:“白雁已衔霜信过,青林闲送雨声来。”毛晋《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的解释写实些,提到北方的白雁“秋深方来,来则降霜。河北谓之霜信”。从劳作需求的角度来年,农人们一定比文人更在意这一暗示,但“碓头没糠”“米谷满仓”之类的俗语,到底是不如霜信一词来得雅致。这其中的不同,也牵引出霜降的另一番风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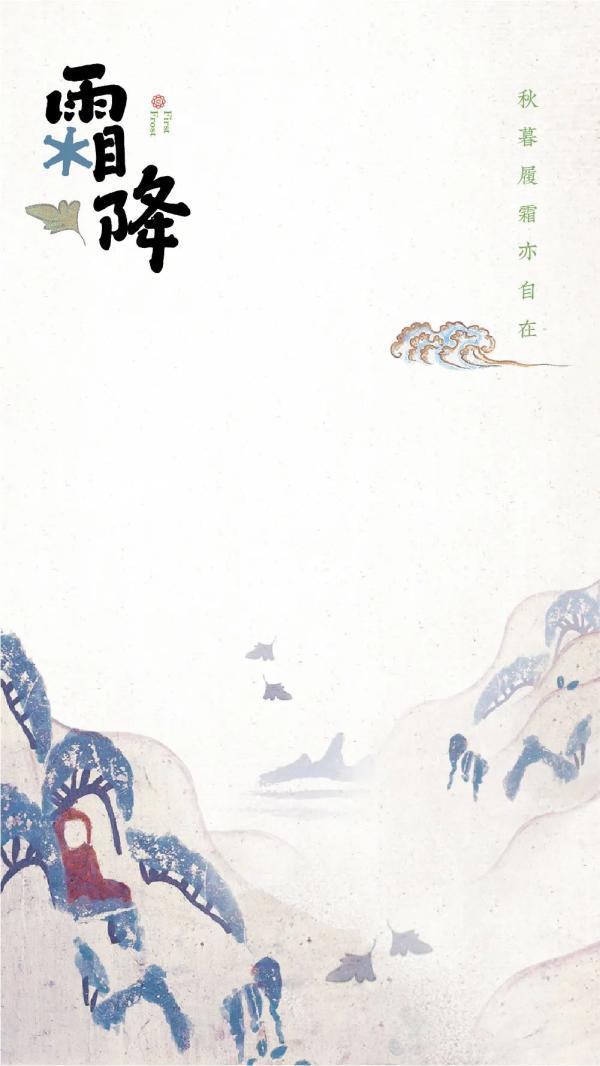
【诗家的歌赋】
一切景语皆情语,诗人眼中的霜降,当然也是诗性的。
霜降的前一个节气是寒露,《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云:“九月中,气肃而凝,露结为霜矣。”《二十四节气解》云:“气肃而霜降,阴始凝也”。季节由秋入冬,阳气由收到藏,露也凝结成了霜,这种浪漫的转化,赋予了霜降与生俱来的文学气质。因此,诗人笔下的深秋,露与霜往往结伴而行:曹丕的 《燕歌行》有“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左思《杂诗》有“秋风何冽冽, 白露为朝霜”,皆是露霜并用。
古人眼中,露是液态的霜,霜是固态的露,但露是润泽,霜却有了更复杂的意味。《礼》云:霜露既降。郑玄为“霜露既降”一句作注道:“感时念亲也。”这种念亲之感一经点破,遂成为后世文人对霜降的普遍感知,乃至于在无霜的季节也不免联想到霜,并由此联想起万里之外的故乡与亲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李白 《静夜思》写道:“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哪怕只是“疑是”,也足以勾起诗人的思乡之情。而在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中,“受降城下月如霜”,依然只是“月如霜”,却不由得不使“一夜征人尽望乡”。元稹亦在“咏廿四气诗”的《霜降九月中》里写道:“秋色悲疏木,鸿鸣忆故乡。”
游子见霜降而思乡念亲,亦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古代中国,“学而优则仕”几乎是唯一正途,而参与科举、求取功名,在农耕社会里造就了数量众多的游子。在唐代,经过县、州两级考试合格的士子应在十月集中到京城应试,离京城较远者就必须在秋季八九月间出发,霜便成了游子诗中最常见的歌咏物之一。
游子的霜诗,最著名的莫过于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枫桥夜泊》的传唱度无需赘言,然而从霜的视角来看,这首诗却多少有些无理。霜是附着在物体表面所形成的水汽凝华,绝不可能漫天飞舞,恰如王充《论衡》所言:“雨露冻凝者,皆由地发,非从天降。”张继眼中满天的霜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大约只有诗人自己能回答了。
从空间维度来看,霜降能够跨越千里,勾连起游子与故乡亲人的情感联结;而从时间维度来看,一岁一度的霜降,也令霜成为可以用来计算时间的尺度。如贾岛《渡桑干》:“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向咸阳。”范成大《赠书记归云山》:“一枕清风四十霜,孤生无处话凄凉。”汤显祖《刘君东下第南归》:“漠漠蒹葭映夕阳,同人秋鬓十三霜。”十霜即是十年,只是“年”一旦成了霜,这悠悠岁月就显得格外漫长了。

【行伍的旗纛】
如果说霜降在农人眼中标记着劳作的节奏,在诗人眼中渲染着思乡的情怀,那在军人眼中,这个节气则代表着一年一度专属于行伍的浩大典礼。
张怀瓘《文字论》中有一名句:“文也者其道焕焉。日月星辰,天之文也;五岳四渎,地之文也。”依据这个标准,二十四节气中的“四立两分两至”以太阳运行为参照,当属“天之文”;而霜降与雨水、惊蛰、谷雨、白露、寒露、小雪、大雪八个节气以山川大地为参照,当属“地之文”。而在这八个“地之文”节气中,唯有惊蛰与霜降安排了国家祭祀:旗纛祭祀。
《明会典》中载:“春祭用惊蛰日,秋祭用霜降日……若出师,则取旗纛以祭;班师则仍置于庙。”所谓旗纛祭祀,是一种军中专祭之礼。《礼记·王制》云:“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祃于所征之地。”这里的“祃”即为旗纛祭祀,郑玄在注中解释道:“祃,师祭也,为兵祷。”大约是旗纛祭祀之礼在东汉时期已经式微,因此郑玄紧接着又加了一句“其礼亦亡”。明朝建立后,对历代礼仪多有继扬,旗纛祭祀也由此焕发了新生。
或许是因为以武为国,明代没有采用宋代以文抑武的政策,相反大幅度提高武官级别,旗纛祭祀的兴盛也成为这一时代洪流中一道小小的注脚。明代立国之初,旗纛祭祀极为频繁,洪武三年七月之前每月朔望日均行祭祀旗纛之礼,后方改为每年春秋两次祭祀。
张以宁《翠屏集》中记载了明代旗纛祭祀的发韧:“洪武纪元之四月,公总率大军建牙于广。是月平三山贼,七月平山南龙潭诸寨,十一月开广东卫,岭表咸靖。越明年三月,有旨大都督府即所治后立旗纛庙,有旗有帜,悉庋于中,岁春惊蛰、秋霜降祀以大牢。天下守镇官于总卫各立庙,视京师典礼如之。”
从明代大量的地方志中能够看出,凡有卫所的地方,基本都能看到旗纛庙和旗纛祭祀的记载。如《嘉靖邵武府志》:“旗纛庙,在卫署西,所祀军牙六纛之神,卫所守御官皆得立庙致祭。旧典春祭用惊蛰日,秋祭用霜降日,今惟霜降日。”祭祀的神祇也颇为复杂,有“旗头大将、六纛大将、五方旗神、主宰战船正神、金鼓角铳炮之神、弓弩飞枪飞石之神、阵前阵后神祇五昌神众”等,可以看出明代的旗纛祭祀盛极一时。
随着承平日久,明代各地卫所的旗纛祭祀大约在嘉靖之后开始减少,后逐渐定为每岁霜降日祭祀旗纛诸神一次,依托旗纛祭祀发展而来的节庆活动也依然热闹非凡。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载:“旗纛庙,洪武三年建于都督府后,以祀军牙六纛之神。每岁惊蛰、霜降祭之。八年,都指挥使徐司马改建于普济桥东。诏停春祭,岁霜降。先一日,本司以所制军器绕城迎之,鼓吹殷作,谓之扬兵,至日乃祭。”到了祭祀的正日,诸种技艺纷呈,迎神赛社,热闹异常,“霜降之日,帅府致祭旗纛之神,因而张列军器,以金鼓导之,绕街迎赛。谓之扬兵。旗帜、刀戟、弓矢、斧钺、盔甲之属,种种精明,有飚骑数十,飞辔往来,呈弄解数,如双燕绰水、二鬼争环……” 旗纛祭祀,在江南俨然便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节日庙会,也由此沾染上了浓浓的世俗色彩。
明清易代后,旗纛祭祀的礼仪依然得以保留。《康熙建宁府志》载:“故址,本主题曰:‘旗纛庙在行都司后,在宋云榭台军牙六纛之神’。岁霜降日行都司官率其属戎服以祭,祭物于本府库支官钱办祭,仪与府社稷同。今祀守备司主之。”每年霜降前夕,各地的校场演武厅的武官们都要身穿铠甲、手持刀枪弓箭,列队前往当地的旗纛庙举行收兵仪式,期望能拔除不详之事,以求天下太平。届时,武官们在庙中集合,向旗台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礼毕,列队齐放空枪三响,然后再试火炮、打枪,称之为“打霜降”,此时的百姓则如潮般聚集在周围围观。当然,随着岁月流逝,一定程度的移风易俗不可避免,清代的旗纛祭祀中混杂了满族竖纛而祭的旧俗,而明代旧有的仪式和用乐则渐渐不为人所知了。
作者:安颜颜
编辑:范昕
策划:范昕
责任编辑:黄启哲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