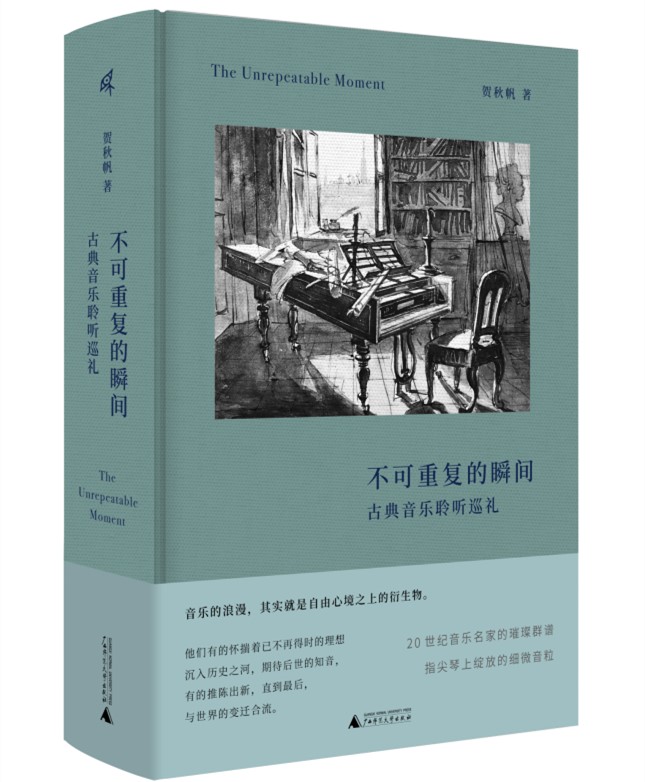
《不可重复的瞬间:古典音乐聆听巡礼》
贺秋帆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
本书谈及的音乐家遍及世界各地,其中不乏国内鲜有推介的名家。作者结合音乐家生平介绍其风格特色、重要作品,以及其在相关音乐流派传承中的地位作用,着重评析比较诸唱片版本,为爱乐人士提供了一份丰赡的音乐指南。
>>内文选读:
天外飞石,掌中闪电(节选)
1934年,初到伦敦的西蒙·巴雷尔(1896-1951)在一个酒会上,奉上了一段恩师费利克斯·布卢门菲尔德写的左手练习曲,不料引来失明的爵士钢琴家亚力克·坦普尔顿的不满——他坚信刚才听到的演奏绝非单手能够搞定,甚至把满堂喝彩视为对盲人的戏弄。为了证明自己并无任何不敬,巴雷尔引他坐到琴边:“请握着我的右手,我为您再弹一次。”曲终,坦普尔顿激动难耐,心悦诚服……
键盘之殇
最早知道巴雷尔,是通过一个出处不明的钢琴大师“历史”系列。那个40碟的套装中,基本上一位钢琴家占据一张篇幅,但也有几位钢琴家是混搭的,巴雷尔现身的那张,有弗里德曼、莫伊塞维奇、列维茨基、布雷洛夫斯基、阿施巴赫,“一时多少豪杰”。巴雷尔的三首曲子分别是20 世纪30 年代录的肖邦《第三谐谑曲》、李斯特《西班牙狂想曲》和音乐会练习曲《轻盈》。因为录音古旧,当时也没有太在意,却不知道在20 世纪上半叶,他的手上功夫曾经独步天下,其疾如闪电的指法,被认为是着了符咒。
西蒙·巴雷尔1896年生于敖德萨的一个犹太大家庭,幼时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先后师从安娜·叶西波娃和布卢门菲尔德,成为涅高兹的师弟和霍洛维茨的师兄。从学生时代起,他就以非凡的演奏速度和手指灵活性称雄,院长格拉祖诺夫称他具有李斯特的左手和安东·鲁宾斯坦的右手,并且在沙俄时代的反犹浪潮中予以多方关照。毕业后,巴雷尔得到基辅音乐学院的教职。1928年,他经由里加,迂回逃往柏林,但是德国的形势逼着他另谋生路。后来他在英国和比彻姆爵士合作的一系列演出为他移居美国创造了条件。1936年11月9日,他首次登台卡内基音乐厅,一举成名。

巴雷尔的儿子鲍里斯回忆道:“家里总是宾客盈门,奇怪的是父亲总是抱怨练琴会使他弹得更糟。他是天才,我印象里他只练过李斯特的《唐璜幻想曲》(即《唐璜的回忆》)和巴拉基列夫的《伊斯拉美》的一些乐段。柏林时期生活困窘,父亲曾去电影院为无声片伴奏。我们移居瑞典的一年,他甚至根本没碰琴,到美国后有一次为阿图尔·鲁宾斯坦救场,之前竟然也有两个月没有碰琴。他的最后演出,当时我在后台,他对奥曼迪说‘这是我们首次合作,希望不是最后一次’,但几分钟后……”1951年4月2日,在和费城管弦乐团合作演出格里格的钢琴协奏曲时,巴雷尔因脑溢血猝死于卡内基音乐厅。
巴雷尔的遗产意外稀少。从现在的CD(激光唱片)发行情况看,整个20世纪30年代,他的演出录音被集中在两碟装的《巴雷尔在HMV的录音全集1934-1936》专辑(APR公司转制)里,其中的精华,被集中在珍珠公司的一张专集里。巴雷尔20世纪40年代中晚期在卡内基音乐厅的演出,则被APR公司分成一套五张发行,但市面上难以觅得;这些录音都是应其子鲍里斯的要求,音乐厅方面的录音室在谈妥价格收费后录下的,但遗憾的是鲍里斯所托非人,“因为录音间看不到舞台,所以录制的时候常常因为不知道曲子何时开始而缺少了开头部分,加上这些母带在转台上挪来挪去总不对劲,许多就这样莫名其妙地丢失了”。

金石之声
即使是从有限的这几张唱片来看,不同时间段的巴雷尔的曲目安排也屡有重复,李斯特改编的《唐璜幻想曲》和巴拉基列夫的《伊斯拉美》就一弹再弹,而《巴雷尔在HMV的录音全集1934-1936》专辑里,舒曼的《托卡塔》就有1935年10月10日和15日的两个录音版。巴雷尔的保留曲目之少,一定程度上,也跟其录音寥寥互为因果。
巴雷尔秉承俄国学派的浪漫风格,专长于晚期浪漫派曲目,致力于在舞台上赢得喝彩,其令人眼花缭乱的刺激弹法,最合适李斯特。上述20世纪30年代的专辑,收有1934年1月31日和1936年同日的两版《唐璜幻想曲》。此曲为李斯特1841年自莫扎特的歌剧《唐璜》改编,因为难度过甚,一直鲜有演奏者,到1877年李斯特又将其改成双钢琴版。20世纪唱片史上,录下此曲的人除了巴雷尔仅有霍洛维茨等少数几个。巴雷尔的1934年版费时15分25秒,1936年版短了10秒,都是令人窒息的演奏。他的强,主要在于快速乐段能照常展现钢琴的颗粒感,即使再快的过渡,也没有显现一丝含混。根据速度,无法想象最难的一段右手小三度半音阶行进加左手的符点伴奏,以及整个键盘层出不穷的双手跨越是如何完成的,更惊讶的是这样的疯狂运转中,他竟然仍旧能让那段改编自唐璜和采琳娜的咏叹调《我们携手》的旋律,朴素真挚地唱出,飞沙走石之中,兀自引出一注清泉,真是匪夷所思。

推进中保持珠落玉盘的快意,转瞬即逝而又形神兼备的另一个例子,数巴雷尔演奏的李斯特的三首音乐会练习曲,一为《轻盈》,一为《侏儒之舞》,一为《被遗忘的圆舞曲》。巴雷尔在其中铁了心炫技到底,掌中风雷指尖闪电,的确罕有追随者。不过他也有诗意迷离的另一面,录于1934 年1月30日的李斯特《旅游岁月》中的《彼特拉克十四行诗第104首》,就全靠了精心雕琢的音色组合,来唱出深沉而富生机的古调,其色块的金属光泽之动人夺魄,为他演奏的李斯特作品所仅有——早年间的霍洛维茨,手下功夫可与之匹敌,音色和力度甚至更胜一筹,但流动感和歌唱性稍逊。
巴拉基列夫自己也无法演奏的《伊斯拉美》,到巴雷尔手里,纯以技巧的飞动著称,中段小行板到结尾段急板的过渡,有排空而来滚滚而过的杀伤力。同一张唱片里,有他1935年10月15日和1936年1月31日两版录音,前者耗时8分19秒,后者8分2秒,当年正式发行的是后者。不过横向比较,霍洛维茨就曾留下6分47秒的录音,音色锻造还有过之,阿劳手慢,也留有一版8分10秒的演奏,手快的齐夫拉,留下四版录音,均在8分30秒到9分30秒之间。当然,音乐不能只讲速度,普列特尼奥夫(一译普列特涅夫)8分30秒的卡内基音乐厅演出,排除录音的因素,整体结构的谨严和情感的凝练,显出了超越前辈的丰满度。
布卢门菲尔德的左手练习曲,巴雷尔有一版1935年10月的录音,本文开头的惊诧,读者自可验证,不过此曲像是他的独门秘籍,未见有别人录过。舒曼的《托卡塔》,他的两版录音都显得过于追求速度,尽管那些艰难的双音、八度片段,都保留着出色的颗粒感。关于此曲,鲍里斯回忆道:“唱片制作人抱怨它不能录在一张SP(粗纹唱片,每面可录五分钟左右)上,列文涅和霍洛维茨都是录了两张,父亲发誓他能录在一面里……他后来对我说,‘你相信么?我的双手简直累死了’。”《巴雷尔在HMV的录音全集1934-1936》专辑里值得一提的还有斯克里亚宾的两首练习曲(Op.2-1和Op.8-12),就是霍洛维茨常奏的那两首,巴雷尔此版大约是音效太差,气韵折损不少。
作者:贺秋帆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