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学权力》
[法]巴尔迪纳·圣吉宏 著
骆燕灵 郑乐吟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
在梳理和分析朗吉努斯、伯克、康德等人的美学思想的基础上,巴尔迪纳·圣吉宏借助精神分析重建了美与崇高概念的谱系,将传统的美和崇高的两难问题转化为美、崇高和优雅的“三难困境”,从而建构了一个关于“美学权力”的三元化理论。
>>内文选读:
译后记(节选)
在《美学权力》里,作者巴尔迪纳·圣吉宏延续了她一如既往较为激进的美学风格,希望从“美学权力”的内部言说,从思想的沉默里言说,从而构建一种有批判意义的“概念的美学”,作为consilium(决策)的理论、行动的理论,以确定美学与伦理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直接关联,并不断完善美学行动的主体作为参与者身份的要求。这是美学能够成为生活的有效力量而不是某种外部意志操控的根本。作者在这里所关注的重点,不仅仅是感性的创造力量,也是美学介入权力和公共领域的能力,或者说感受力和审美经验介入“决策”并恢复人们行动的自由。美学作为一种从感性本身出发所产生的力量,因其自身的认知能力而向人们提供生活形式的具体路径,让人们重归实存。
作者对美和崇高的词源学考察追溯至其在希腊文明中的“显现”,并将哲学思考集中在崇高作为一种独特的美学经验在18世纪伴随美学的诞生而兴起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崇高并非作为美最完美或最高级形式而在哲学史中出现。相较于历史上那些曾为美与崇高两个概念的阐述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哲学家们,她更在意的不是两者在形而上观念上的区分,而是在经验的原始状态中就已出现分道扬镳的蛛丝马迹,这让我们有可能意识到,它们并非客观存在,而应被视为作用在我们身上的一种力量和效果。巴尔迪纳·圣吉宏在她的第一本书《要有光:一种崇高哲学》中已经开始对崇高和美进行严格的区分。受到以柏克为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和以弗洛伊德、拉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美学的影响,她对崇高和美的区分始于经验性的心理学层面:崇高与可怖、恐惧等心理经验相关,崇高感只有在生命受到恐惧的威胁,个体感受到存在的痛苦时才产生。主体和实际的危险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它没有成为恐吓和暴力真正的“受害者”;相反,恐惧激发了主体自我保存和自我防卫的激情,迫使主体实施强制性的力量来超越自我。因而,恐惧战栗在危险、恐怖和痛苦的边缘变成愉悦和胜利感。与此同时,恐惧可怖被规定为“去实体化”的崇高哲学的原则。

另一方面,作者回归朗吉努斯在《论崇高》中从诗学修辞的角度来重新赋予崇高作为“精神的伟大所带来的回声”的至高无上的价值,并把作为“内在的视觉”的想象(phantasiai)重新界定为诗人和演说家使用语词来呈现灵魂内在图像的能力。在崇高哲学的视域下,天才、想象与激情本身带着卓越的理念,让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自我超越并上升,在崇高中神驰物外,催生话语的呈现和在场。康德《判断力批判》里的官能理论和超验形而上学为崇高美学提供了认识论层面的辩护:想象力在理性的要求之下统摄直观表象,即使想象力尽其全力也无法抵达直观现象之本体,但它向感性统摄最大值的努力本身却体现了想象力与知性的自由和谐,符合理性的目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先验论使得崇高美学真正成为具有普遍性的一门独立的科学。
在这个理论构架之上,作者思考了崇高、美和优雅三者的关系,以及崇高的风格、美的风格和优雅的风格等一系列问题,将传统的美和崇高的两难问题转化为美、崇高和优雅的“三难困境”,实际上建构了一个关于“美学权力”的三元化理论。美、崇高和优雅是美学权力的三个原则:美取悦,崇高启发灵感,而优雅魅惑打动我们。与之相应的三个创造性策略是:模仿、创造和适应。作为三种“权力”,它们有着各自的局限性,并且其中一方的弊端可以与另外两种权力和谐共存。审美三难,实则是政治和伦理行动中的策略选择问题。“美学权力”这一想法的提出,提醒我们日常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存在着无处不在的对抗,并向我们提议在面对这些不同状况的交锋时如何选择相应的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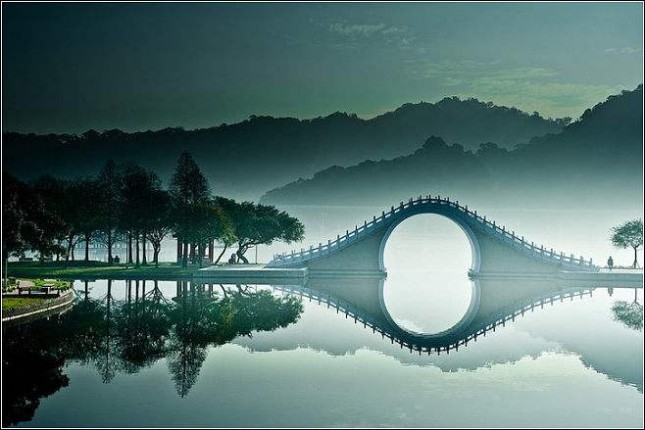
美作为一种内在的修养,抵抗畸形与不和谐。从风格上来看,崇高毫无疑问是最为激进的美学风格,崇高对抗平庸和卑微,与崇高哲学一同流露出来的,是一种介入存在的行动主义的美学态度。崇高对抗平庸和卑微。作者引入优雅来对抗崇高有可能带来的暴力和迷狂的风险,从而构建多元化的美学三重奏。在作者看来,优雅是更人性化的权力,这正是当下西方社会最需要的。因其联合能力,“优雅在人与人之间架起了桥梁,并允许他们彼此相投。根除仇恨及其破坏性的暴力,这是一种感觉,而培养它对生活来说至关重要”。这充分地显示了巴尔迪纳·圣吉宏作为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情怀。因而,美学权力不必然是不正当的操控,作为一种宇宙疗法,把“我们暴露于宇宙之中,让宇宙在我们身上产生回响,这是我们理解它的最好方式之一,我们来源于此,我们属于此,我们也将消逝于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巴尔迪纳·圣吉宏具有某种时代的敏感性。与皮埃尔·阿多和福柯一样,她的美学思想代表了向哲学与行为合二为一传统回归的一种潮流。20世纪的政治、种族和社会形态的巨变,以及媒体技术的发展都毫无疑问地对这一回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当下的我们正置身于法国学者居伊·德波所说的《景观社会》里,影视图像、互联网、传统媒体或新媒体共同建构了一个光怪陆离、同义反复、重复堆积、无所不在的普遍的世界表演景观。现代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附着于这一美学体验。影像的泛滥和拥堵遮掩了自觉的、凸现差异的个体意识的表达和本真存在,被动的接受成为了一种最普遍的生存状态。视觉美学的日趋喧嚣反而带来了自我的涣散、平庸、迟钝乃至麻木,成为现代诗人的一种生存困境,而对于接受了世俗化和现代化之后的资产阶级而言也徒增荒诞感和虚幻感。这是巴尔迪纳·圣吉宏这样的西方知识分子的基本语境,也是行动的美学要面对的主要问题,美学的主体作为思考和行动的主体需要对个体的意义进行探寻,并赋予生存意义。

对于译者来说,翻译巴尔迪纳·圣吉宏并不轻松。她的文风繁冗迂回,极少进行抽丝剥茧、层层渐入的论证,尤其喜欢借助强烈的情绪对照为她的文字笼上一层“权力”的光晕。她善于从一种现实生活中最强烈的情绪或情势里抽取暴烈而戏剧化的表达,借助于其所仰慕作者的权威力量让语词“崇高”,让它凌驾于实在和读者。因此,译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倾向直译,也相对地保留了一些较长的欧式句子,希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作者在写作时内心的激烈情绪、矛盾的冲突以及对崇高的向往。
假若如作者所说,恐惧和痛苦的原则远比快乐的原则更加深刻有力,那么它所催生的书写很有可能热衷于创作一个暴力的、令人恐惧的、正在毁坏的世界,而人类的温柔与爱将永远地被遗忘或牺牲于死荫的幽谷。
巴尔迪纳·圣吉宏的思想深受精神分析、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等思潮影响,理解作者需要梳理更多的西方哲学传统的思维构架、辩证关系和回归错综复杂的历史语境和创作氛围。思想史和语境涉及不仅作为知识分子也作为独特个体的巴尔迪纳·圣吉宏与西方社会的基本意识形态、审美经验和社会生活的诸多问题。当然,作为中国读者,我们可以把作者的思想仅仅当成一家之言,也完全可以有自己的阅读角度。我们从《诗大序》开始就有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悠久的美学传统和诗学传统,在漫长的美学实践和诗学实践里我们也积累了完全异于西方美学传统的审美经验,而这些丰富的文化遗产还有待于我们在当下的理论写作和实践中进行新的发掘、阐释和创作。
作者:巴尔迪纳·圣吉宏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