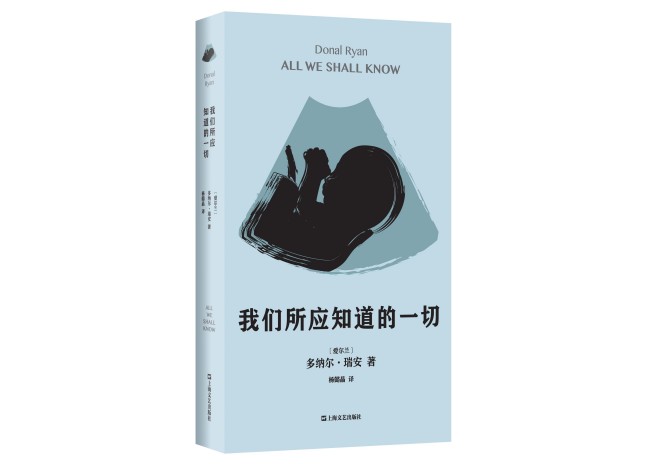
《我们所应知道的一切》
[爱尔兰]多纳尔·瑞安 著
杨懿晶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
孕期第十二周,梅洛迪·席伊感受到了体内的翻搅,但她的丈夫帕特愤怒地抛弃了她。她试图留在当下,摆脱痛苦的过去,但未来即将来临,过去却依然攫住了她。小说以梅洛迪的情感为线索,胎儿为基点——前者成为后者的羊水,子宫则如同幽灵,召唤又汇聚了所有冲突和感受,达成精神性的反刍,输入,直至救赎。
>>内文选读:
十四周
我第一次看帕特打曲棍球当天就爱上了他。那场比赛他被罚了下去,离开场地的时候,他指了指我,像是在说,那都是为了你。那个挨了他揍的男孩还倒在地上,围绕着裁判和摔倒的球员爆发了一阵小规模冲突。几个月前,我和这家伙在弗洛吉的舞会上跳了一支慢舞,后来在回家的公车上,他忽视了我,转而向别人献殷勤,周一又在学校里说了几句贬低我的俏皮话,不过迄今为止我都不知道他说了什么。帕特快步走着,同时摘下头盔,前额汗湿的头发往后捋了上去,阳光打在他的脸上,他炽热的蓝眼睛对上了我的目光。他点了点心脏的位置,穿过傍晚微凉的空气,大步朝边线走去。我的双腿发软,我觉得自己要昏倒了,布丽迪·弗林还在旁边说,噢,上帝啊,梅洛迪,他指的是你,她捏紧了我的手臂。我是多么爱他,是他,只有他。
帕特是我第一个接吻和牵手的对象,直到十三周多一点之前,他还是我唯一吻过的男人。我从没感受过另一个男人的手抚弄我的脸颊,或是在另一个男人眼里看到仿佛洞穿一切的渴望。岁月把我们逐渐揉成了一个人,这是我的感觉,而对自己残忍并不太难。现在我们已经正式分居了,我也终于能把我和他区分开来。就算是在过去充满恨意的几年里,我们也总是紧密相连。

我母亲和父亲不是很好的一对。她比他高一两英寸;他们的手一个纤长,一个粗短。她是一个崇尚经典、注重审美趣味的人,而他压根儿不知道这些词是什么意思。她想投身学术界,可从没做到过。他是市政服务机构的工头,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奔波。我母亲身上总是散发着法国香水和昂贵皮革的味道,而我父亲总是一身汗味,混杂了某种尖利、沉重东西的气味,可能是沥青吧,或是别的让他整天忙碌的黑色柏油质的玩意儿。我父亲不像是她感兴趣的类型,也不能让她兴奋。她不会厌倦他,换一个男人她也许会,一个能读懂她的沉默、洞悉她复杂心绪的男人。她就是那么看他的。这是我的看法。
一天早上,我听到她对他说,你到现在也该当上经理了吧。
我的能力干不了那样的事,他说。
我听到她轻蔑地哼了一声,然后是一阵漫长的沉默,我听到一张椅子从桌旁被拉开,又听到我父亲轻柔地说,好啦,好吧。接着我听到他拿起钥匙,然后她说,那你能干什么呢?你干什么呢?你干什么呢?你能干什么呢?你能有什么用呢?有什么用呢?迈克尔?
我听到我父亲说,我不知道。好啦,晚点见。他走后门出去了,他从来不摔门,厨房里没有动静,但我能闻到烟味。我站在走廊里偷听,感到周身发冷。
那天晚上我父亲回家的时候看起来不一样了。我还不到十岁,对他的一切想象都是以爱为出发点的。某种孩童的美好憧憬消散了,我眼中始终包裹着他的光晕变得暗淡,忽闪着消失了。我打量着他,不带一丝情感。他有什么用呢?

如今回想我当时看待事情的方式,想到我让母亲对他的怒气渗进我的心里,我迫切地想要道歉,弥补我的疏远给他造成的伤害。我让另一个女人的冷漠玷污,侵蚀,瓦解了我对他完美的爱意,我甚至并不真心喜欢那个女人,却又迫切想要变成她的样子。
那天晚上,我没有扑进他怀里,于是他知道有些事情变得不一样了。我走到门口去迎接他,我们对彼此的态度变得僵硬又尴尬。我突然长大了,不再是个小女孩,他肯定感觉到了;我成了房子里的另一个女人,成了原本就在那里的女人的附属品和衍生品。那个女人,她看起来既需要他又鄙视他,有些时候,很多时候,她还恨他。
他震惊于我的改变,但没有表现出来。我能从他看我的样子里感觉到。他的眉头皱紧了,伸直双臂搭在我肩上,他从我眼里认出了与我母亲如出一辙的冷硬,那是他每天都会看到的。他笑了起来,好像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但他早该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我想他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堕落的,从我们开始疏远的那一刻起,一路变成了一个不中用的普通老头,一个安静、无聊的人,满足于自己的存在,支撑他的只剩下责任,要把这件事情做好的责任,养大一个孩子,照顾一个妻子,支付一连串的账单,最终什么也没得到,没有柔软的床铺可以躺下,枕畔没有表达谢意的温言,做完所有的工作后,哪怕做得很好,哪怕他为之工作的人都表达了感激和爱慕,他也无法体会到一丝一毫甜蜜的松快。
可他依然爱我,不顾一切地、坚决地爱着我。他也用同样的方式爱着她,要不然他还能做些什么呢?

十四岁的时候,我第一次丧失了理智。是我母亲的手指崩断了我脑袋里的那根弦。看到一串玫瑰经念珠以富有美感的方式巧妙却不自然地缠绕在那十根手指上。不知怎么的,我之前没注意到这一幕,要不就是我看到了却没往心里去。前一晚我们的家庭医生给我注射了某种药剂来帮助我入睡,减轻我的痛苦。我们站在家属的位置上。爸爸和我,如同水星和金星围绕在我们耀眼的太阳周围,妈妈的兄弟姐妹被安排在我们旁边,像是那些距离更遥远的行星。靠近门口的地方站着表亲们组成的小行星带,沿着前厅一字排开。
我说,爸爸,那串该死的玫瑰念珠在那儿干吗呢?她这辈子都没念过《玫瑰经》。爸爸没看我。他用力吞咽了一下,喉咙里有什么在咯咯作响。我记得他苍白的脸色、咬紧的牙关,只有我能看到他脑袋里轻微的战栗,而我情绪激动地站在他身边。
没事的,宝贝,他轻声说,他们都是那么做的,想当然而已。
想当然?我差点吼出来,我看向拱门另一边接待处的尽头,一个比婴儿大不了多少的表亲在前庭里傻笑着。我从近亲的小矩阵里冲了出去,一路推开那些前来履行义务的人,直冲到露天处。近亲、表亲、远亲,所有人都在瞪着我,看着我跑了出去;事情突然变得有点滑稽,没人会预想到这一幕,就像一道闪电撕开了阴沉的天幕。我是冲他去的,而他没看出来,要不就是他看出来了,却没想到我是在冲他发火。我照着那个傻笑的孩子的脑袋,从侧面扇了他一巴掌。我的手打在他头上,发出一记脆响。他只有八岁,最多九岁吧。然后我从他身边飞速跑开,一把抓起弗兰克·多利肉乎乎的胳膊。他像个警察一样站在门口,守着人们放慰问金的盒子。到里面来,把我母亲手上那些念珠弄走。他没动。到。该死的。里面来。马上。
他照做了,冲我父亲点了下头,一脸疲惫的样子。前门暂时关闭了几分钟,那个几乎不认识我母亲的小表亲的脸皱成一团,上气不接下气地哭号着。有大一点的孩子过去抱他,温柔地让他轻声点,并立刻把他带离了房间。吊唁的人流短了一截,邻居、朋友、我父亲的同事,还有不常来往的亲戚们,按照葬礼的秩序排成一列,轮流过来跟我们握手,之后抽身离开这个尴尬的场面。爸爸安静地站在那里,脸色苍白地看着弗兰克·多利强行分开我母亲略显透明的手指,试图理顺那串倒霉的念珠,最终还是把它剪断了。
>>作者简介:
多纳尔·瑞安 (1976— )爱尔兰作家,被誉为“爱尔兰文学新浪潮的王者”,两度入围布克奖。其小说语言节奏独特,融狂野和诗意,黑暗与甜蜜,悲伤与诙谐于一体,呈现对复杂人性和复杂主题的高超驾驭力。作品已被译成20多种语言。
作者:多纳尔·瑞安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