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爱欲》是清华大学教授汪民安深入探讨“爱欲”这一主题的力作。全书分为“爱欲的谱系”“转向”和“爱欲的政治”三个部分。在上篇中作者梳理了柏拉图、苏格拉底、奥古斯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构建的“爱欲的谱系”,从真理之爱、神圣之爱、尘世之爱这三个维度,再现前现代时期人类高贵而神圣之爱。“转向”这部分辨析笛卡尔、斯宾诺莎如何在理性主义的旗号下为爱建立一个科学解释模式。下篇“爱欲的政治”分析黑格尔、海德格尔、拉康、弗洛姆、巴迪欧等关于爱欲的思想,书写人类试图在现代性中摆脱工具理性对爱的驯服,进而实现爱之救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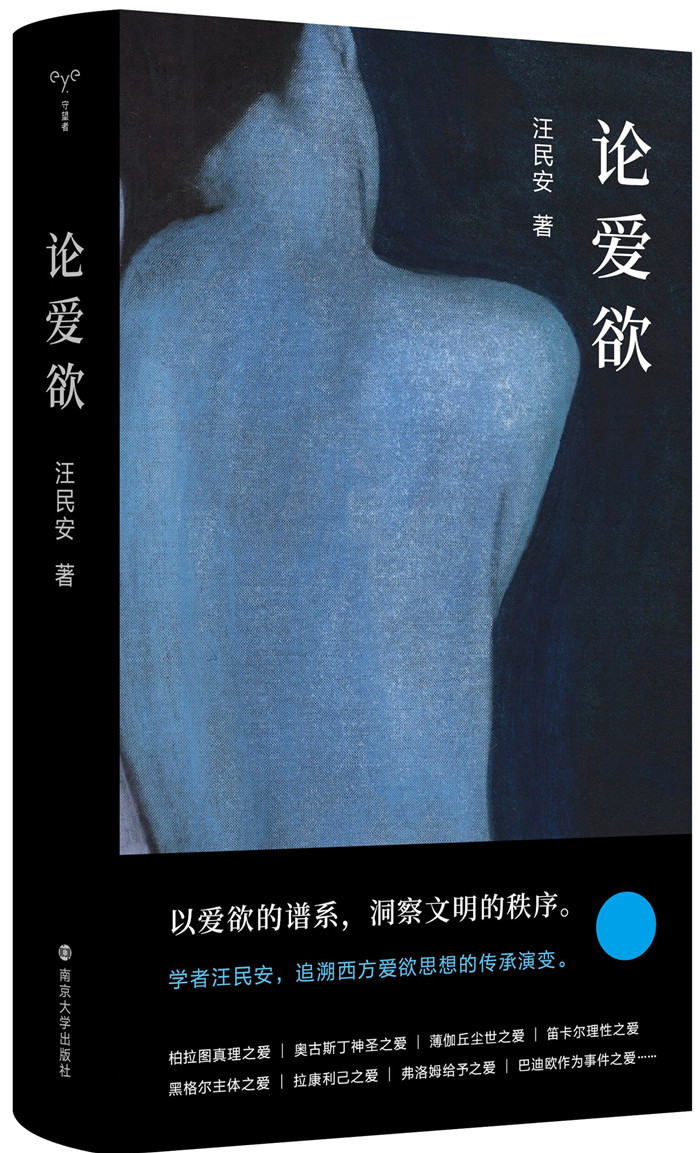
《论爱欲》
汪民安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尘世之爱
薄伽丘开始将肉体之爱引发的快乐引入男女之爱中。这是他对但丁和彼特拉克的偏离。他的《十日谈》飘荡着的是活生生的肉体气味。这本书这种肉体气息来得过早、过于迅猛、过于突兀和大胆了,它不得不被反复当作淫秽的禁书而罚入黑暗之中沉默地流传。我们把它同14世纪的绘画相比就看得更清楚了,14世纪的绘画还非常拘谨,丝毫没有体现身体的狂欢和快乐迹象。乔托正苏醒的绘画此时在雕刻痛苦而不是快乐。正是从《十日谈》开始,现代的出版禁令,总是有一部分套在爱欲身上,直到20世纪,直到劳伦斯和纳博科夫,爱欲作为道德之罪也一直背负了各种各样的书写之罪。
就此,薄伽丘翻开了新的篇章。如果说尘世之爱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但丁和彼特拉克的纯粹的精神性的男女之爱,那么另一种就是薄伽丘的肉体之爱。但丁和彼特拉克小心翼翼地推开了上帝之爱的框架而释放出了人世间的精神之爱,一种削弱了上帝之爱的邻人之爱,而薄伽丘则将他们精神之爱的大门推开,释放出了更物质化的肉体之爱。《十日谈》是肉体之爱的狂欢曲。在这里,但丁和彼特拉克那顽固残存的上帝之爱消失得无影无踪。上帝在这里没有死去,他存在,但只是作为一个反讽性的符号存在于《十日谈》中。上帝不是主宰者,而是被主宰、被利用的木偶。他从来没有真正发挥效用。相反,他总是被轻浮地利用,被各种各样的性爱所利用。一个修士就以上帝之名引诱了一个纯洁少女,上帝和性爱之间并不构成一种严峻的张力,相反,他们之间有一种合谋的勾连。薄伽丘较之彼特拉克更强有力地返回希腊罗马那里,返回世俗之爱,返回人和人之间的爱。不过,这种人间之爱不是简单地回到生育的问题,回到希腊的创造性和永生的问题——苏格拉底对爱的思考(创造和快乐)总是跟生育,因此也是跟生命的延续相关。而在薄伽丘这里,爱和死有关,但是和生育无关。爱和死有关,这并不意味着要像古代人那样因为爱通向永生而拒斥死亡。这是一种新型的爱和死的关系,一种对希腊人和基督徒来说都很陌生的爱和死的关系。
我们可以在薄伽丘的《十日谈》中去理解新出现的爱的问题。这部小说的背景是1348年佛罗伦萨的瘟疫。这是一场来势凶猛的黑死病,也就是鼠疫。一旦感染,死亡的概率极大。当时的城市尸体遍野,死寂凄凉,丧钟乱鸣,一派肃杀。为了躲避这场瘟疫,人们采用了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躲在自己家里和没有病人的地方,远离尘嚣……有节制地享用美酒佳肴,凡事适可而止,不同任何人交谈,对外面的死亡或疫病的情况不闻不问……另一些人想法不同,他们说只有开怀吃喝,自找快活,尽量满足自己的欲望,纵情玩笑,才是对付疫病的灵丹妙方”(薄伽丘:《十日谈》,王永年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这后一种人并不躲避,他们在城中兴之所至,为所欲为,他们活一天算一天,仿佛明天行将死去,仿佛这将临的死亡不可避免,因此,他们抛弃一切私产,撕掉任何面具,毁掉任何习俗和法规而过着声色犬马的放纵生活。死亡令人狂欢。在死亡的冲击下,整个城市陷入瘫痪和无政府的状态。《十日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它的故事。在死亡的黑夜包裹下,十个青年男女聚在一个偏僻的郊野讲述各种各样的情爱故事。他们是为了逃避死亡而聚集的,是为了逃避死亡而讲述这些故事的。每个人讲十个故事,一共持续十天。在此,一方面,他们远离尘嚣,从空间隔离回避他人的角度躲避死亡,这是薄伽丘所说的第一种逃避瘟疫的方式;另一方面,他们通过讲述故事来回避死亡,他们在故事中生活,在故事中度过难熬的时刻,在故事中发出笑声。这是他们独有的通过沉浸在故事中来逃避现实死亡的方式。怎样的故事会让他们沉浸其中并且遗忘死亡的威胁?这都是与爱欲相关的故事。
作者:汪民安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