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觉得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日本作家志贺直哉与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原著难读,那不妨先读一下格非的这本《文明的边界》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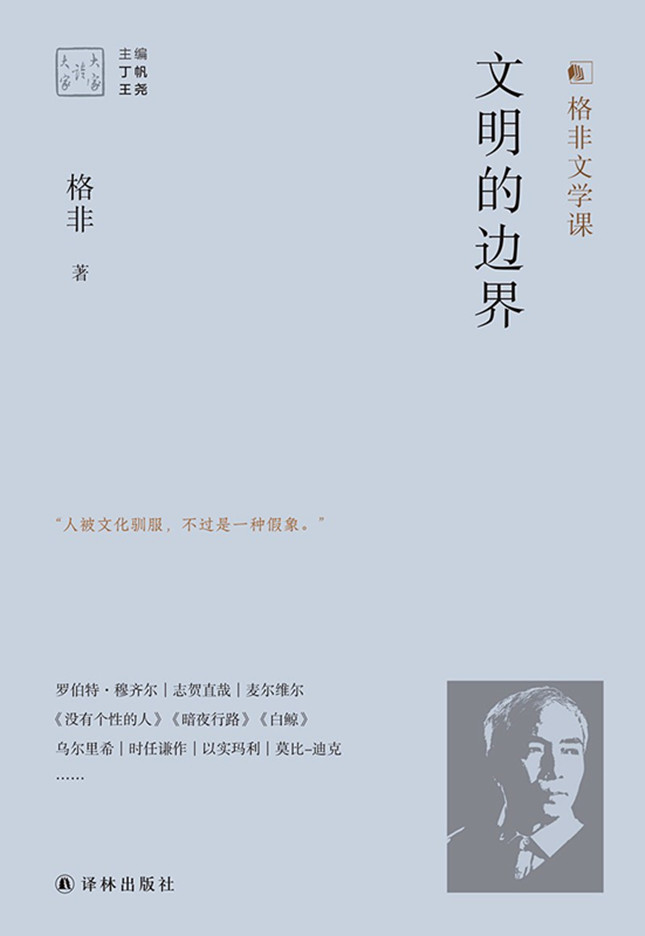
《文明的边界》
格 非 著
译林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2018年至2020年格非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小说叙事研究”课的讲稿。格非之所以选取这三位作家,是觉得三人都是以传统自然过渡到现代文明的居间者视角创作,都将自然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作为自己作品最重要的主题,通过各自的写作都在读图重构现代性的时空关系。本书中,格非以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志贺直哉的《暗夜行路》、麦尔维尔的《白鲸》为主线,从作家个人的人生经历出发,兼顾讨论了作家的其他作品特别是一些不太为人注意的早期作品,从中梳理作家思想孕育的脉络,至而聆听三位“隐士”对文明的沉重叩问:究竟什么是现代文明的边界?它到底要将我们带向何方?
我很喜欢这个标题,准确地概括了三位作家的共同特征,同时也让读者带着问题开启本书的阅读之旅。作为文学课讲稿,格非尽可能拓展知识视野,除了将三位作家投射到所处的时代,还将他们与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等著名作家进行对照。需要指出的是,他并没有对卡夫卡等人一味膜拜,而是辩证地分析各自优长。如在谈到穆齐尔与卡夫卡时,他就认为“穆齐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涵盖卡夫卡的一部分主题,卡夫卡则无法涵盖穆齐尔”。
在序言中,格非一针见血地指出:“对现代文明进程的强烈质疑和反思,是19世纪以来所有伟大小说的共同特征。”工业革命后,欧美以及脱亚入欧的日本均迈入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人类延续数千年的乡村秩序渐被打破,以城镇为中心的新社会秩序正亟待建立。而从全球格局看,大航海时代后,世界新的力量基本形成,同时意味传统世界秩序同步发生蝶变。所有的变化不会波澜不惊,而会转化成一个个具体的事件,飘落到每个社会个体的身上。

《没有个性的人》的故事时间设定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间有着某些巧合,故事里的乌尔里希在“平行行动”中迷失了自我,试图寻找“另一种状态”或“另一个地方”。实际上无论哪种“状态”还是“地方”,均不过是人类寄居的地理符号。当空间环境依然如故,地理意义上的变更并不会产生根本上的意义。《暗夜行路》的作者志贺直哉有着日本“小说之神”之称,他笔下的主人公时任谦作乍一出生便背负着沉重的伦理文明十字架,他曾作过多次尝试,每次以为逃出生天,结果总是碰得头破血流。麦尔维尔写作《白鲸》显然与他的捕鲸经历有着密切联系,当别人在疯狂地捕鲸赚取利润时,他却从中觉察到飞蝇扑火般的文明危机。不过,对于“裴廓德号”船长亚哈,我并不觉得他的全部野心就是为了奔赴一场毫无意义的灭亡——毕竟他以捕鲸为生,万一他成功了呢?当然,如果他成功了,就不会存在这部不朽之作了。亚哈之所以对这头名为莫比·迪克的抹香鲸存在严重的误判,更深处的思想源头,很可能来自于工业革命所取得的那些成就——他坚信人类力量无往而不胜。当然,或正是这种盲崇,才注定了他葬身大海的宿命。
作家思想体系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这一点从作家早期作品便可见端倪。在讨论志贺直哉的《流行性感冒》时,格非结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判现实主义,得出“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并呈现出某种‘病态’的‘地下室人格’”。而在《白鲸》中,格非从麦尔维尔先前完成的《抄写员巴比特》里,“挖掘”出曾经负责“死信”处理工作的巴比特,而捕鲸船上也有不少无法捎带的死信。
格非还导入尼采的孤独哲学,借此指出三位作家的“遁世”不是逃避,而是一种置之世外的超脱。所谓旁观者清,大抵亦是此理。穆齐尔为躲避二战炮火,四处流亡;志贺直哉一生中搬家多达26次;麦尔维尔一直在海洋与陆地、城市与孤岛的生活之间摇摆,缺乏归属感。如果说作品是个人内心的外化表现,那么,他们作品中流露出的“遁世”与孤独,恰恰是他们对现实的态度。
回到本书书名来看,“文明”一词的出现,其实带有鲜明的人类一厢情愿视角:人类夸夸其谈的文明,是否与自然秩序相适应?如果我们从人类最终灭亡的角度观察,今天人类所倚重的那些文明规则又有多少意义?回看人类发展史,不仅人类,地球上所有生命源头均指向茫茫大海。从这层意义上讲,《白鲸》里的“裴廓德号”奔向大海,似乎又寓意一种返璞归真?
文明到底是什么?本书没有给出答案。今天,关于文明的探索依然没有停歇。
作者:禾 刀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朱自奋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