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餐桌和冰雹》,科罗拉多斯普林斯,1980年
图片来源:国家地理
拍摄:萨姆·埃布尔
西塞罗有云:“如果你拥有一个花园和一间书房,你便拥有所需要的一切了。”西哲所说的花园,非我等俗人休闲流连之地,而是孕育思想的摇篮。公元386年的一天,米兰的一座花园里,奥古斯丁完成了灵魂的忏悔,此即著名的“花园的奇迹”,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中对此有精彩的描述,无花果树下面,哲学史翻开了新的页码。
花园是孕育思想的摇篮
在视觉艺术的范畴,花园无疑是艺术家最乐于描绘的对象之一,中外皆然。摄影术诞生后,一个个知名或不知名的花园留在了胶片上,摄影师记录了花木,也记录了人类和它们的联系。《花园里的摄影师》(The Photographer in the Garden,Jamie M. Allen Sarah、Anne McNear,Aperture,2018)脱胎于伊斯曼柯达公司的一个展览,这是一本很厚很重的画册,内容却极为有趣,不同时代的花园、着装各异的园丁,而植物却分辨不出年代,所不同的是摄影师的目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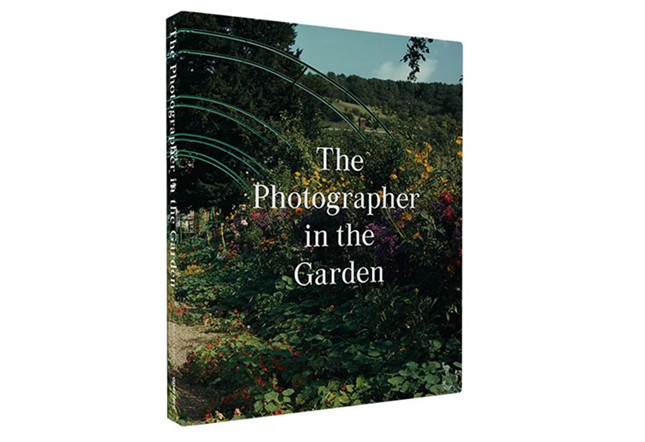
《花园中的摄影师》
(The Photographer in the Garden)
书中披露,园艺与摄影是乔治·伊斯曼(George Eastman)的双重爱好,他在伊斯曼柯达公司内,用巨大的花圃和菜园建造了别具一格的城市庄园,他的露台花园不单是聚会的场所,也是测试新摄影材料的地方,这里光线佳且少有人干扰,说花园孕育了摄影艺术,不算过分。作为工作与休闲、野性与秩序、季节更迭的空间,花园为摄影师提供了探索的沃土,更是其视觉灵感的来源,为独特的摄影瞬间提供了可能。
编者对图片的选择颇具眼光,穿插的文字部分则更具学术价值,其意义在于,没有单纯停留在令读者感到愉悦,而是提供了大量历史与文化信息,扩展了读者关于人类如何与自身建造、培育和欣赏的景观相联系的概念。
相比各种花的特写,我个人更喜欢那些拍摄花园景观的作品,摄影工具便捷的时代,把花朵拍得“好看”似乎并不难,但无论忠实程度如何,摄影作为一种媒介,它的表现力和隐喻能力却需要文化支撑。
人与植物之间的风俗与文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花园里的摄影师》是一本人类学研究著作,尽管印制精美,对一般喜欢花花草草的读者来说却谈不上引人入胜,但《神奇植物志》([法]利昂内尔·伊纳尔、卡米耶·让维萨德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11月版)却完全不同,“这是一份奇异而真实的植物学研究记录”,据称它是法国植物学家伊雷内40年的研究成果,这位勤奋的学者离群索居,行为举止怪异,后来竟然失踪,人们在他的实验室里发现了一份神秘档案,堪称一部奇书,于是将其公之于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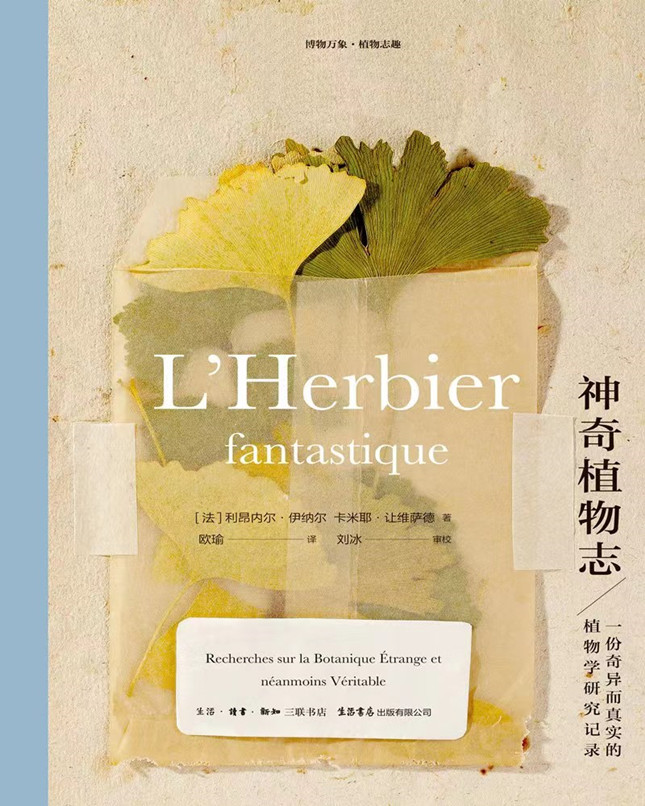
《神奇植物志》
[法]利昂内尔·伊纳尔 卡米耶·让维萨德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老实说,我对此说持怀疑态度,当然也许出于对这一领域的无知。不过,这本极富创意的书的确展示了诸多古老而神奇的植物所具有的奇异特性,满纸冷知识,足助谈资,倒是真的。
从形式上说,整本书就是一本剪贴簿,举凡新闻剪报、往来信函、科学实验、实物标本等等,按照食肉植物、产乳植物、吸血植物、会叫的植物、会走的植物、暴躁的植物等分类,粘贴于一张张卡纸上,许多页上还有手写的笔记。逐页翻看,仿佛可见一位对植物深度痴迷的老者,在昏黄的烛光下,做着剪刀浆糊的营生,全然不理会人事代谢,残漏声催秋雨急。
书中所记录的奇闻异事并不局限于一时一地,时间横跨公元1世纪至19世纪,也就有了许多在现代人看来不可思议的风俗,如钉树,即一种“把疾病转移到树上”的祭祀仪式,剪贴簿上有一份材料,据说是来自于一位侯爵的妙法,内云:
用一颗铁钉在疼痛的牙齿周围绕一圈,再吮吸这颗铁钉,然后把铁钉钉入树干,在钉铁钉的过程中,疼痛感即随之消失。

《黄蜂》,2002年
图片来源:克兰普画廊/乔治·伊斯曼博物馆
拍摄:诺丽·尼克斯
植物学家伊雷内在剪报一侧空白处写道:“铁钉渐渐被树皮包裹起来,就像伤口慢慢愈合。”读之令人忍俊不禁。无独有偶,中国古代也有一位神医,名叫薛伯宗,此人能“徙痈于树”,据《南史》记载:
薛伯宗善徙痈疽,公孙泰患背,伯宗为气封之,徙置斋前柳树上。明旦痈消,树边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长二十余日,瘤大脓烂,出黄赤汁斗余,树为之痿损。
薛伯宗将病人身上的痈疽“转移”到柳树身上,人神奇地康复了,树却元气大伤。这种玄幻式的描述无非用以显示其医术高超罢了,但从疾病史的视角分析,却不是简单的一句“蒙昧迷信”就能够解释得了的。
清人陈淏之《花镜》(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9月版),也是一部奇书,盖于朴学盛行之时,作者“堪笑世人鹿鹿”,将自己朝夕灌园之体验,甚至询之老农的所得,纂成这部了不起的经典。这么说,当然不是贬低乾嘉之学,是想说在一个所谓的盛世,总要有读书人/知识分子做点逆潮流的事情,辛稼轩“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说的是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在他固然是一生的政治悲剧,可是在农业社会,“种树书”岂非经世致用的上佳选择?

《花镜》
陈 淏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花镜》全书共分为六卷,其中,卷一为“花历新裁”,卷二为“课花十八法”,卷三、四、五、六这几卷,列举观赏植物的种类,计花木、花果类百种,藤蔓类91种,花草类103种。“花历新裁”是一年中各月的物候占验与种植事宜,“以便园丁从事”,其结构颇似恰佩克《园丁的十二个月》。文辞优美,令人心醉。如二月事宜的开首:
是月也,玄鸟至,仓庚鸣,桃始夭,李方白,玉兰解,紫荆繁,梨花溶,杏花饰其靥,正花之候也。
其中,虽化用了《礼记·月令》的若干句子,却也可见作者的才情。至于“占验”中,亦有不少神秘主义的说法,如“凡月内值月蚀,粟贱人饥,虹多见于东,主秋米贵;见于西,主丝贵人灾”等。曾见上世纪50年代一份关于《花镜》的学术研究,指出这一部分内容“近乎迷信,无可取材”。其实,全书中类似的“异端邪说”尚有不少,如说仙人掌,“植之家中,可镇火灾”;说凌霄花香,“妇人闻之能堕胎”。
用今天的话来说,《花镜》一书不能说是陈淏的“原创”,而是他博采众说的结果,但若以此观之,《齐民要术》《本草纲目》的“原创”身份都很可疑。《花镜》中近乎巫术的经验,陈淏之前的历代著述便多有记载,传为苏东坡著之《物类相感志》中亦有“日月蚀时饮,损牙”“银杏不结子,于雌树凿一孔,入雄树木一块,以泥涂之,便生子”之类的话。为何我们与植物之间,会生出这么多涉及风俗与文化、科学与玄学、禁忌与文明的话题?
只有蔬果才能表现季节的节奏感
今春封闭在家,高头讲章是看不下去了,恰巧手边有本新出的台湾地区作家焦桐《蔬果岁时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11月版),便懒懒散散、断断续续地读起来。书分两部分:蔬之属、果之属,所记无非青葱、马铃薯、韭菜、毛豆、芋头、草莓、西瓜、龙岩、甘蔗这些东西,但正如炒土豆丝可以考验厨师的基本功,对写作者而言,写这些随处可见的蔬果,看易实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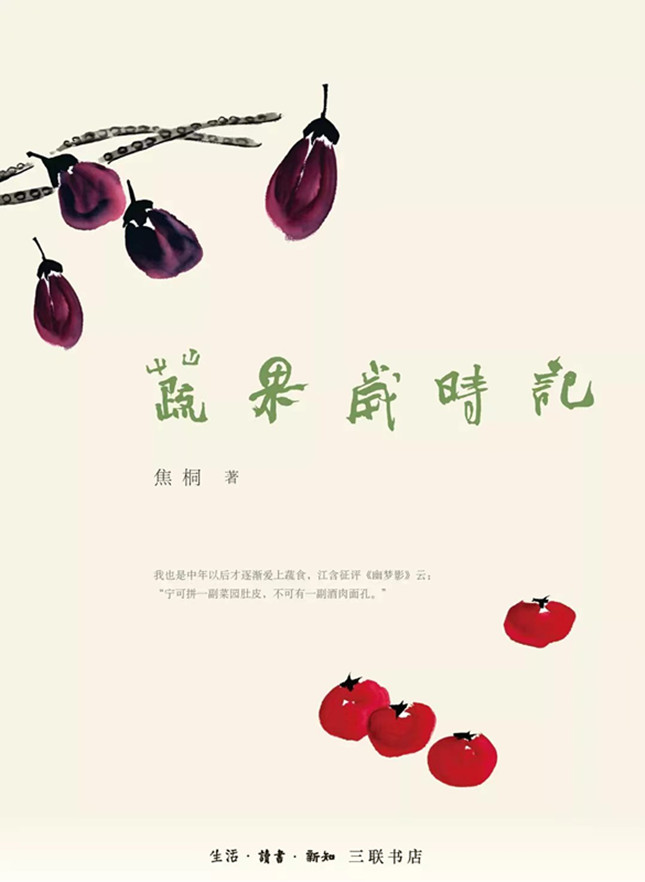
《蔬果岁时记》
焦 桐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焦桐确是高手,他在自序中谈及自己的动机,“只有蔬果才能表现季节的节奏感,肉食难以体会季节性”,此语不同凡响。他写香椿:
香椿的味道含蓄,散发一种内敛的气质,清清淡淡,仔细咀嚼才能领略其滋味,悠长,隽永,像诚恳而不擅言辞的人,深入交往后,才了解那木讷纯真的性格。
他写南瓜:
像我这样的糟老头一餐比一餐肥,像快速膨胀的南瓜,藏身宽阔的叶下,笨拙,觉得什么遭遇都无所谓,什么环境都可以。
这样平常的、萧散旷达的语句俯拾即是,全无时下某些“美食文学”之矫揉造作。齐白石有一则题画记,写在一幅白菜图上:“余有友人尝谓曰,吾欲画菜,苦不得君所画之似,何也﹖余曰,通身无蔬笋气,但苦于欲似余,何能到。”焦文之高人一等,全在他有“蔬笋气”。他还在念中学时,就每天放学陪外婆去种菜,担水,挑粪;人到中年,爱上蔬食,去菜市场成为刻意的、不变的生活方式。所有这些积累,都化为云淡风轻的美学,凝结成《蔬果岁时记》的66篇文章。庄子曰“五味令人口爽”,焦桐叹道“这世界,味觉的喧哗令人沮丧”。

《帐篷成像照片:莫奈花园和手推车》,吉维尼,法国,2015年
图片来源:埃德温·豪克画廊
拍摄:阿贝拉多·莫雷尔
一蔬一饭,本为寻常之事,读《蔬果岁时记》,我每天忙着网上抢菜,曾这样想:写这样文章的人,如果有一天吃不着空心菜、九层塔之属,他会写出怎样不同的文字呢?所幸这样的念头冒出来没有多久,冰箱里的菜就多得快撑开门,颇有暴殄天物之虞。于是,我用旧报纸包好茭白、莴苣,将小葱种进花箱,帕斯卡尔的名言在耳畔响起:“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是,他却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
是的,他在说我们与植物的联系。
(除书影外,本文所有配图都选自《花园中的摄影师》(The Photographer in the Garden)一书)
作者:李 涛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朱自奋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