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紫禁城的物候之芒种(摄影:王琎)
“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陆游所描绘的芒种时节是那样多姿多彩、生机盎然:既有雨后的舒爽,又有夏日的热情;既有田里的稻秧,又有桌上的麦饭;既有农事的忙碌,又有歌声的悠然。也正是这开启仲夏时光的“芒种”,不但是对谷物那旺盛生命力的直观描述,更蕴含着华夏儿女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芒种节气一般于每年公历的6月5日至7日交节,此时的太阳正运行到黄经75°的位置,北斗七星的斗柄则正指向古人宇宙观中“巳”的位置。作为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芒种的到来标志着气温逐渐升高、降雨逐渐增多,对农民来说是开启繁忙“午月”的关键节点。而“芒种”之名的由来,也正是中华农业文明博大精深的体现。
有芒之种与播种之节
“芒种”之“芒”,本义是谷物种子壳上或草木上的细刺;而“芒种”之“种”,则有两种解释——作为名词的“种”(zhǒng),指植物的种子;作为动词的“种”(zhòng),则指播种。所以相应的,自古以来对于“芒种”的含义也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如《农政全书》曰:“芒种有二义:郑玄谓有芒之种,若今黄穋榖是也。一谓待芒种节过乃种。今人占芒种节,则大水已过,然后以黄穋榖,种之于湖田。”也就是说,“芒种”的一种解释是指有芒的种子,即麦、稻等谷物结出果实、长出种芒;而另一种解释则是指应当从这一时间节点开始谷物的种植。这两种说法究竟孰对孰错呢?
《周礼·地官·稻人》曰:“泽草所生,种之芒种”,郑众《注》:“芒种,稻、麦也”。有芒的谷物很多,小麦、大麦的麦穗上有麦芒,水稻的稻穗上也有稻芒,但这两种“芒”的出现时间却是不同的。《农政全书》的作者徐光启从小生长在上海,对他而言,芒种正是江南插秧种稻的好时节;所以对徐光启这样南方稻作区的民众而言,“芒种”应该是指水稻的种植,此时的水稻正移栽入田、等待着之后充沛雨水的滋润,远远没有到长出稻芒的时节。相对的,芒种时节不该种植麦苗,而应该欣赏麦芒的灿烂。《四民月令》曰:“凡种大小麦,得白露节,可种薄田”,中原地区的麦子自古便是从白露时节、即公历9月初开始播种的,等到了6月的芒种节气,麦穗就已经陆续成熟、生出金黄的麦芒,需要抢在多雨季节来临前抓紧收割了,白居易《观刈麦》一诗就形容:“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所以对小麦、大麦种植区的民众而言,芒种就不是忙着播种的日子,而是收获“有芒之种”的时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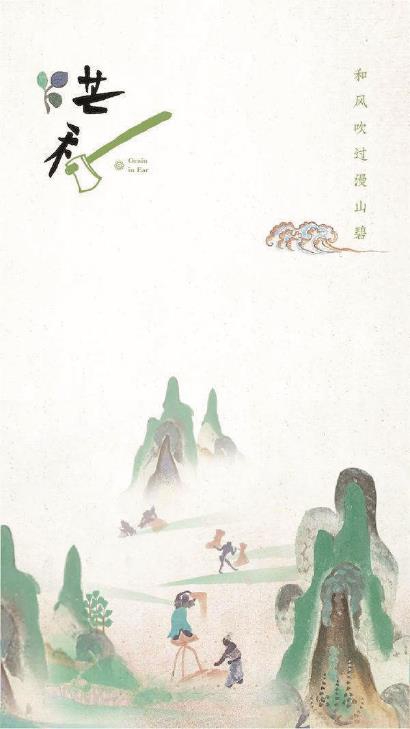
正如南宋马永卿《懒真子》所总结的:“所谓芒种五月节者,谓麦至是而始可收,稻过是而不可种。古人名节之意,所以告农候之早晚,深矣。”芒种既是收割的节气,也是栽种的节气;既是属于麦穗的节气,也是属于稻秧的节气。不过我们也并不能就此判定“芒种”是属于北方的“有芒之种”还是属于南方的“播种之节”,随着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演进,这种“稻”与“麦”、“种(zhòng)”与“种(zhǒng)”的界限是越来越模糊的,这也正是“芒种”之名的由来会引发争议的症结所在。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乱不休,导致大量北方的民众迁居到江淮及其以南地区。这就使得麦、菽、粟等粮食作物,以及北方精耕细作的传统经验,也都随之传入了土地肥沃的南方,直接推动了我国农业种植上轮作复种技术的进步和推广。例如唐朝樊绰的《蛮书》在记述云南物产时曾言:“水田每年一熟,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南宋的《陈敷农书》也说:“早田获刈才毕,随即耕治晒暴,加粪壅培,而种豆麦蔬茹”;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宋时期,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因地制宜地开展稻、麦、豆类、蔬菜等作物的轮耕轮种。除此之外,由《齐民要术》《农政全书》等传统农学著作可知,绵、麻、芜菁、家蚕、蜡虫等的培育,都需要在芒种时节进行特殊的管理。所以说,随着中国农业在轮作复种方面的不断发展,“芒种”的含义已经不再局限于割麦与插秧,而是成为了与各种农作物的收割、播种、管理都息息相关的重要节点了,“芒种”之“芒”也渐渐成为了“忙碌”之“忙”。
《宋书·阮长之传》等史料中还记载着这样一种有趣的制度:在南北朝时期刘宋的元嘉年间,郡县各级官员的俸禄是以芒种为节点计算的,如果地方官员在芒种之前离职,那么该职位一整年的俸禄就归下一位来继任的官员所有;如果是在芒种之后离职,那么这一年的俸禄就归这位离职的官员所有。这种以芒种为节点发放“年薪”的制度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芒种时节在古代农业社会中,有着直接关系到一整年经济收入多少的重要地位。正像民间谚语所说的,“芒种芒种,连收带种”,农民们争分夺秒的“芒种”是夏种、夏收和夏管的决定性时刻,也透射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勤劳与智慧。
送别花香与迎来湿热
天空有斗转星移,地上有花谢花开,感受自然界的草木荣枯、昆虫发蛰、候鸟往来等变化,是古人记录时节迁移、制定生活计划最直接的方式,芒种节气的种种物候、民俗也体现了古代先民对待自然、对待生活的细致与热爱。
《逸周书·时训解》曰:“芒种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鶪始鸣;又五日,反舌无声。”古人注意到,随着芒种节气的到来,螳螂卵逐渐从越冬的卵鞘中孵化出来、成为若虫,而螳螂正是蝗虫、蚜虫、棉铃虫、松毛虫、豆天蛾等害虫的天敌,待到7月后生长为成虫,便能保护农作物、蔬菜、果树、林木等不受虫害。“鶪”指伯劳鸟,俗称胡不拉,作为一种小型猛禽,能够捕食各类害虫和小动物,在各种雏鸟陆续出巢的春夏之交,甚至还会通过模仿其它鸟的声音来把小鸟吸引过来,伺机捕食;古人应该就是基于伯劳鸟的这种特性,依据它的叫声来提醒自己调整芒种节气到来后的田间管理。而“反舌”则指乌鸫,同样也能捕食蝗虫等害虫,它的音域宽广、叫声嘹亮,在春季的求偶期能经常听到它的鸣叫,但到了仲夏时节便进入了忙碌的繁殖期,为了更好地哺育幼鸟,反而会较少鸣叫、隐匿行踪,所以乌鸫的逐渐沉寂,便成为了从芒种到下个节气之间的又一物候标志。正如唐代诗人元稹在《咏廿四气诗·芒种五月节》中所说的:“芒种看今日,螳螂应节生。彤云高下影,鴳鸟往来声。渌沼莲花放,炎风暑雨情。相逢问蚕麦,幸得称人情。”古人对这些益虫、益鸟的关注,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古人在芒种时节及时调整劳作安排、细致规划生活步骤的传统智慧。
当然,芒种的物候变化也会带来些许遗憾与烦恼,比如雷雨、蛀虫等带来的威胁。《农政全书》曰:“(五月)立梅,芒种日是也,宜晴。……畏雷,谚云:‘梅里雷,低田拆舍回。’言低田巨浸,屋无用也,甚验。”芒种节气时,农民们总希望有一段时间的晴天能让他们完成粮食的抢收和抢种;此时就最怕雷雨等强对流天气发生后导致麦株倒伏、麦粒霉变或者淹坏秧苗、影响收成,所以古人把芒种后的半个月称为“禁雷天”。除了雷雨,人们担心的还有湿热环境下滋生的各种蛀虫。比如《四民月令》曰:“芒种节后,阳气始有慝将萌,暖气始盛,虫蠹并兴,乃弛角弓弩,解其徽弦,张竹木弓弩,弛其弦,以灰藏旃裘毛毳之物及箭羽,以竿挂油衣,勿辟藏。”随着温度和湿度的逐渐升高,啃啮衣服、书籍、谷物类的蛀虫也渐渐活跃起来,所以古人会在芒种节气后开始注重各种器具的储存,比如将弓弩的弓弦卸下来、对其加以保养,将用各种鸟兽皮毛制成的衣物或箭羽等用草木的灰烬埋藏起来,用竹竿把油布雨衣悬挂起来,此外还要注意书籍、谷物、薪炭的准备和储存等等。这些自古传承的生活“小贴士”,都是为了应对芒种之后“黄梅雨”所带来的闷热与潮湿,是古人应对自然变化时的“未雨绸缪”。

老树画画笔下的二十四节气之芒种
与物候变化相对应的是古人在芒种节气的种种习俗。随着仲夏季节的到来,与螳螂孵化、鸟类繁殖相对应的,春季开放的各种鲜花会逐渐凋谢,所以祭祀花神、与之告别便是芒种的一个重要节俗。《红楼梦》第二十七回便记载了大观园内众人祭饯花神的场景:“凡交芒种节的这日,都要设摆各色礼物祭饯花神。言芒种一过便是夏日了,众花皆谢,花神退位,须要饯行。……那些女孩子们,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或用绫锦纱罗,叠成干旄旌幢的;都用彩线系了。每一棵树头,每一枝花上,都系了这些物事。满园里绣带飘颻,花枝招展。”女孩们用花瓣柳枝编制成花神的轿子和车马、用绫罗绸缎来制作花神的旗杆和仪仗,并用五彩的丝线将这些饰物捆绑在花草树木上,为仲夏时节赋予了夺目的灿烂芳华,也为少男少女寄托了别样的欢乐哀愁。这些庭院闺阁中的尽态极妍应该是古代一道靓丽风景线,但对于普罗大众而言,平安开启夏季的繁忙农事、保障一年的粮食收成才是真正的当务之急,所以更多的芒种节俗仍旧是与农事直接相关的。例如流行于浙江省云和县梅源山区的“芒种开犁节”,作为已经有着500余年历史的民俗,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当地18个村的村民会在每年芒种节前迎接赐福之神在各村巡游,芒种当天则会举行由鸣喇苇、吼开山号子、祭神田、犒牛、开犁、分红肉等环节组成的芒种开犁仪式,仪式结束后还会演酬神戏、吃仙娘饭,在其乐融融的氛围中济济一堂,共同憧憬稻田的丰收。与之类似的,在安徽省绩溪、歙县一带,每年芒种时节会举办安苗节,其间会有各村迎神巡游、褒贬稻田优劣、分享敬神供仪等环节;还有贵州省黎平县一带的侗族打泥巴仗节,是芒种前后男女青年在一起分插秧苗的同时,用互相投掷泥巴的方式娱乐消遣、互相祝福的民俗。总而言之,中华大地上的各种芒种节俗,大多是在播种粮食作物的同时播种生活的希望,其中既寄托着对自然最纯粹的敬畏和感恩,同时也饱含着对生活富足、家庭安康的美好憧憬。
生命萌发与孕育希望
无论从“芒种”的内涵变迁、还是从芒种的物候节俗来看,对于农耕文明主导的古代中国来说,芒种时节关系到许多家庭农事的成败、收入的多少、乃至家人的死活。从这些层面来说,“芒种”之“芒”就不仅仅是麦芒、稻芒,也不仅仅是忙碌、繁忙,而是一种希望、一种生命力的体现。事实上,“芒”字的本身就蕴含着生命萌发、蓬勃生长的意义。如《白虎通义·五行》:“其神勾芒者,物之始生,其精青龙,‘芒’之为言萌也”,在古代五行思想中对应东方、春季、青色的木神勾芒(又作“句芒”),名字中的“芒”字由来就是为了表现草木萌发时生命力;又如西晋文学家束皙的《补亡诗·华黍》中有“芒芒其稼,参参其穑”之句,便是用“芒芒”一词来形容广大、众多的样子。这些“芒种”之“芒”所发生的意蕴衍生,往往就承载着最真挚而炽热的情感表达。
《耕织图》中的“芒种”,就是对芒种时节的一种不完整、却又“直指人心”的表现。从上古岩画、先秦器具开始,中国自古便有用图像形式对农业劳作进行直观描述的传统,到宋代出现了按照时节顺序对农家的耕作及纺织劳动进行系统性描绘的图谱,楼璹于南宋初期绘制的45幅《耕织图》便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后的元、明、清各朝又有以楼璹《耕织图》为蓝本绘制的数十套类似图谱,并受到历代提倡重农思想的帝王所关注。而在这些《耕织图》中,“芒种”无一例外地与“插秧”对应在了一起。如明代《便民图纂》卷一的“农务之图”中,有描绘农民们在水田内插秧场景的“插莳”一图,图上又配有竹枝词曰:“芒种才交插莳完,何须劳动劝农官。今年觉似常年早,落得全家尽欢喜”;在清代雍正帝即位前所编的《耕织图》(又名《胤禛耕织图》)中,他为“插秧”一图题写的诗句也说:“物候当芒种,农人或插田。条成行整整,入望影草草。白柳花争陌,黄梅子熟天。一朝千顷遍,长日爱如年。”在《耕织图》中,原本与芒种息息相关的冬麦收割、豆蔬种植以及田间管理、物品收藏等事宜似乎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大江南北各不相同的芒种景象也被单一的江南水乡插秧景象取代了,这是不是文人墨客的无心之失或者帝王将相的不食烟火呢?其实,这恰恰是反映中国农业特点和中国农民愿景的艺术表达。正如许多学者曾经指出过的:作为唐宋以来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以水稻种植与蚕桑养殖为基础的“江南”成为了重农、劝农的示范之地,也成为了彰显政治安定、生活富足的重要隐喻与象征。所以芒种时节与插秧画面的对应,非但不是以偏概全的错误,反而真切体现了广大农民在历经了芒种时节的辛勤劳作后,对于“一朝千顷遍”“全家尽欢喜”的美好憧憬。正是“芒种”一词所象征的这种希望和生命力,赋予了芒种时节独特的魅力。

雍正帝即位前所编的《耕织图》册页之插秧
“芒种”是收获,“芒种”也是希望。金光灿灿的谷粒会让人联想到丰收的喜悦,又细又尖的麦芒则会让人联想到锋芒的锐利;潮湿泥泞的稻田会让人联想到劳动的汗水,整齐排列的秧苗则会让人联想到未来的幸福。经历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仍旧是中国各地开展农业生产、适应自然变化、调整生活状态的重要时间节点。通过对芒种节气丰富意蕴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农业文明的发展、南北文化的交融、经济中心的变迁,更能够看到中华民族无穷无尽的斗志以及永恒不灭的希望。
作者:刘捷(文学博士,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编辑:范昕
策划:范昕
责任编辑:邢晓芳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