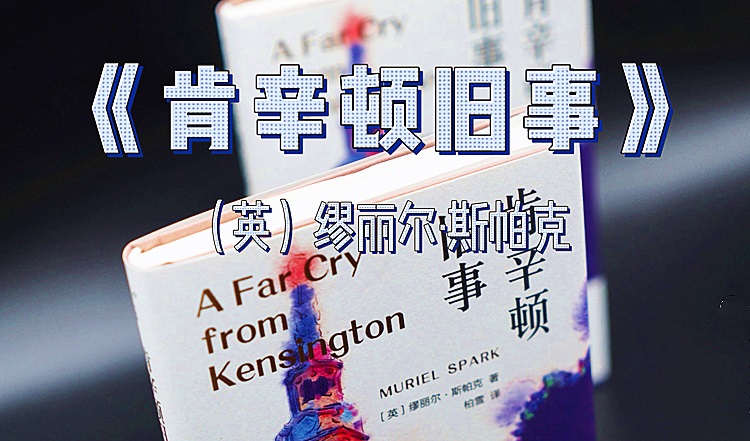
《肯辛顿旧事》讲述了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二战”后破败的英国伦敦的光怪陆离的出版界故事。书里那个独特的伦敦全是奇幻地想在出版行业找工作的人。资深编辑,胖嘟嘟、十分可靠的霍金斯太太,直呼阿谀逢迎的蹩脚文人为“尿稿人”——呕出了一堆文学材料,尿出了雇佣文人写的报章杂志,拉出了恶心的散文。
霍金斯太太的直言不讳,催生了一场刻意的、质量低下的文学表演。恶意滋生,如病毒般,感染了霍金斯太太生活的各个领域。
在这本书里,无端邪恶和权力滥用,与毫无真实性可言的糟糕写作,归根结底是一回事。
本书作者缪丽尔·斯帕克(Muriel Spark,1918-2006),苏格兰重量级女作家,在世界范围内亦享有盛誉,代表作有《布罗迪小姐的青春》《驾驶席》等。她分别于1967年、1993年获颁大英帝国官佐勋章与大英帝国爵级司令勋章。2004年,苏格兰艺术委员会创立以“缪丽尔·斯帕克”命名的文学基金。2008年,缪丽尔被评为“1945年以来50位伟大英国作家”之一。
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视频观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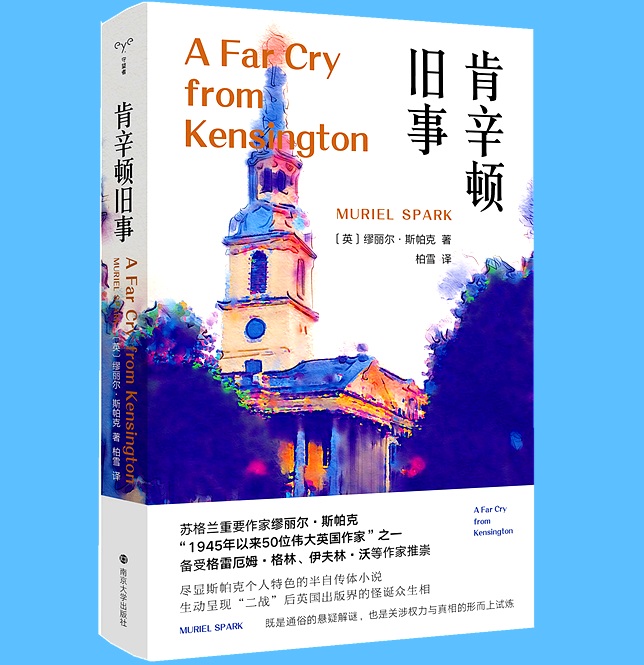
▲《肯辛顿旧事》, [英]缪丽尔·斯帕克著,柏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
>>内文选读:
白天实在太喧嚣,往往在夜里我都躺着不睡,聆听着寂静。最终,我在万籁俱寂中安心地睡去;但在我还清醒时,我享受着黑暗、思考、回忆,还有预料之中甜蜜的失眠带给我的感受。我听到了寂静。本世纪50年代初期,我养成了失眠的坏习惯。失眠本身并不坏。你可以在夜里躺着思考;失眠的质量完全取决于你决定思考些什么。你可以决定思考什么吗?——是的,你可以。大多数时候你可以下定决心去做任何事情。你可以安静地坐在空白的电视机前,什么都不看;你迟早能让你自己的节目比大众节目更精彩。很有趣的,你可以试一试。你可以把你喜欢的人单独或者一起放到屏幕上,说你想让他们说的,做你想让他们做的,如果你愿意,还可以把你自己放进去。
夜里,我清醒地躺着,凝视着黑暗,聆听着寂静,想象着未来,挑选着我过去忽略了的细枝末节,它们曾被弃如敝屣,此刻却涌上心头,显得举足轻重,于是命运的重量不再压在我当下生活的难题之上,无论是什么难题(人活着,哪一天不会遇到难题?为什么要把夜晚浪费在它们身上?)。
肯辛顿与20世纪50年代——我那些不眠之夜的背景——往往遥不可及。即使是现在,当我回到伦敦,回到肯辛顿,付了打车费,迎来了守候在那里的人们的问候,给朋友们打了电话,打开了邮件,当天夜里,我又找回了自己甜蜜的失眠时光,但我明白,往日的肯辛顿、老布朗普顿路、布朗普顿路,还有布朗普顿圣堂已经远去,遥不可及。我在夜里细细思考的往往还是过去在夜里思考的东西,正如我那时的日常生活对我现在做的事情仍有一定的影响。
那是1954年。我当时住在南肯辛顿一栋高层住房里,房间配有家具。几年前,一位朋友提及“你曾经在南肯辛顿地铁站附近住过一段时间的那个出租房”时,我吓了一跳。房东米莉应该会愤愤不平地否认那是个出租房,但我想事实确是如此。
米莉那时60岁,是个寡妇。她现在已经90多岁了,但还是当年的米莉。
房子是半独立式的,不相接的那一侧与隔壁房子的距离不超过三英尺。街道每一侧都有18间房子,样式相同。锻铁大门通向一条小路,路的两边各有一片碎石地和花坛,还散布着月桂树丛,小路通往房子的前门,门上带有两块印花玻璃窗。米莉·桑德斯的所有房客都有前门的钥匙,前门通向一个小门厅。米莉自己住在一楼。进来之后,右边是一个带镜子的衣帽架、几个挂外套的钩子和一个放伞的地方;其中一个平整的台子上放着台电话机。左边是米莉最好的房间,装了扇弓形窗,只用来招待访客。向前是楼梯,通往房客的楼梯平台,楼梯的左边有一条小走廊,通往米莉的客厅、厨房、卧室及隔壁的暖房,还有她家的后花园,这花园在伦敦的住房中算是相当宽敞、令人满意的了。这些街道是为上世纪的商人家族修建的。
二楼有一间浴室和几间配有家具的房间,分别租给了两个单独的房客和一对夫妇。正前方是一间客卧一体房,也装了扇弓形窗,旁边有一个小厨房;住在这里的是那对夫妇——巴兹尔·卡林和他的妻子伊娃,他们年近40,还没有孩子。伊娃是一个幼儿学校的兼职老师。而巴兹尔,他给自己的定义是一名工程会计师。卡林夫妇异常安静。一旦他们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就不会发出任何声音,即使是在午夜之后——房子白天的自然噪声已经结束。
卡林夫妇隔壁是一间大卧室,可以看到花园。房间里有一个洗手盆和一个煤气灶,旁边还放着个常见的深色钢制箱子,上面有便士和先令的投币口。在这个房间生活和工作的,是来自波兰的女裁缝旺达,她近乎贪婪地承受着苦难。尽管旺达·波多拉克永远无法承认她有过一刻的幸福,但她有一颗慷慨的心。她有许多客人来访,一部分是她的顾客——她的淑女们(她是这么称呼她们的),滔滔不绝地说着要怎么修改衣服的尺寸,一部分是她的波兰朋友——据她所说其中一部分是敌人。她的大多数访客都是晚上六点钟下班之后过来,对于顾客,她会给予优待,朋友和敌人则要在楼梯平台上等着,直到顾客试穿结束。旺达在招待客人的时候,并没有把工作撂在一边;她的缝纫机时不时地嗡嗡作响,其间还夹杂着男人说波兰语的洪亮声音、女人的吵嚷声和准备茶水时杯碟的撞击声。波兰语的对话听上去似乎是最响亮的,因为那些从旺达房门前经过的人都听不懂。
二楼平台的最里面是一间小一些的房间,住着25岁的片区护士凯特·帕克,个子小小的,皮肤很黑,胖嘟嘟的,眼睛像鸟一样又黑又圆,牙齿白得发光。她来自伦敦东区。她似乎散发出一种活力,经常能带动身边的人,当然,她也很有勇气。凯特经常晚上出去或者出远门工作,但是她在家的几个晚上都会打扫自己的房间。她对打扫这件事很仔细,也很热切,实际上她对每个人的房屋打扫都是如此。当她去别人的房间喝杯茶或者给他们量体温时,她常常会礼貌地说:“您的房间非常干净。”如果她没有这么说,那就意味着你的房间不干净。凯特讨厌细菌,那是魔鬼玩的把戏。因此,只要她晚上在家,她就会把房间里的家具拖到平台上,用滴露擦洗她的油地毡。要不是这些家具是房东所有,她早就用消毒剂擦洗它们了。米莉虽然长期以来都忍住了,但她反对凯特用沾满了消毒剂的抹布拼命擦拭她的桌子、椅子和床;够了,她说,经过凯特的大力清洁,整个房子闻着都是医院的味道。她给了凯特一些薰衣草做的花蜡,用来清洁她的家具。只要听到家具在平台上的撞击声和拖拽声,闻到薰衣草混合着消毒剂的臭味,就能知道凯特晚上一定在家。凯特发誓,等她攒够钱,有了自己的房子,一定要配耐洗的木质家具,还要涂成白色。对自己的积蓄,凯特严格地把控着,也很自豪;它们都被存在了邮局。她在房间的橱柜里放了一连串装着现金的小盒子,上面分别标着“电”“煤气”“车费”“午餐”“电话费”和“杂物”。等清洁和拖拽工作结束之后,凯特会在睡觉前十分仔细地修剪自己的指甲。她还会把第二天要穿的衣服摆放得格外整齐。有时在睡觉之前她会接过一杯饮料,雪利酒或者威士忌,但总会很严肃地叹一口气,似乎在传达她真不该拿走这杯东西,它可能会埋下祸根。
再上面一层有一间小阁楼,天花板是倾斜的,我就住在这里面。房间里安了炉子和洗碗槽;角落里是一个内置淋浴,倾斜的屋顶下面是一个又宽又矮的橱柜。
这层楼还有一间公用卫生间和另外两个房间。其中一间住着年轻的伊泽贝尔,房间里有她自己的电话机,这样她每天晚上都可以跟她在萨塞克斯郡的爸爸打电话;只有答应了这一条件,伊泽贝尔才能获准到伦敦做秘书的工作。有时,伊泽贝尔一晚上都在讲电话,除了和她爸爸,还和她的一帮熟人打电话,她那欢呼雀跃的声音,穿过薄薄的墙壁,抑扬顿挫地讲述着她那传奇般的每日经历。
阁楼这层的另一个房间更小一些,可以看到花园。这个房间住的是医学生威廉·托德。为了达到很好的听觉效果,他经常打开自己的无线电收音机收听第三套节目的古典音乐。他声称,这种方式能让他更好地学习。
有时我会办一次聚会,我想这能证明我租住在这里。除此之外,晚上在家的我相当安静。但是一般来说,在家的时候,我会下楼和米莉交谈。即使是楼下米莉住的一楼房间,也经常会有喧闹声,因为房子的维修和杂活需要特温尼先生晚上来完成,他就跟我们隔了几扇门。特温尼先生之所以要在白天完成自己的工作之后再来敲敲砸砸,是因为米莉的经济能力还没有达到能请承包商或者日间工人的地步。特温尼先生贴墙纸的时候,会把纸摊在架起来的工作台上;米莉准备好面粉和水调的糨糊,然后弄成胶状拿给特温尼先生,让他糊在纸上。或者他会用一堆工具通下水道,发出一连串哐当咣当的声音,周围回荡着米莉的电视放出来的声音,而我一边喝茶一边坐在那里看着。
米莉和这个房子里还有我办公室里的其他人一样,从来都只叫我的姓。尽管我是一名28岁的年轻女子,但大家通常都叫我霍金斯太太。这对我来说似乎很自然,对我周围的人来说明显也很自然,我当时都没想过坚持让他们换个叫法。我是一名战争遗孀,霍金斯太太。我这个人——霍金斯太太——身上有某种特质,能招来很多秘密。我太清楚不过,而且我给人的印象确实也是有点过,我体型庞大、肌肉发达、丰乳肥臀,两条腿又长又健硕,腹部隆起、背部宽厚;我身高5.6英尺,撑得起自己的重量,而且身体很健康。当然,这样的外貌或许是人们愿意向我吐露心事的部分原因。这种体型看上去让人很舒服。我当时的照片拍出来是圆脸、宽宽的双下巴和蒙眬的睡眼。这些是黑白照片。要是有了色彩,它们一定能展现出我那带有鲁本斯特征的肉体、眼睛和皮肤。而且我是霍金斯太太。直到后来我决定瘦下来时,我一下子注意到,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都不再向我吐露那么多自己的秘密。顺便说一句,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除了胖没有其他毛病,那你很容易就能瘦下来。吃喝跟以前一样,只要减半就行。如果有人递给你一盘吃的,就留一半;如果你要吃自助餐,就拿一半。如果你是个完美主义者,可以过一会儿再吃掉剩余的一半。关于意志力的问题,如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你就要把它想成当前时态下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只存在于过去和未来。在某一刻,你决定去做或者忍住不做某件事情,而在下一刻,你已经做了或者忍住没做这件事情;这是应对意志力的唯一方法。(只有在非常人能忍受的压力下,意志力才能即时存在,但那是另一种论述。)我免费给出这个建议;它已经包含在本书的价格里。
不管怎么说,在1954年,肥胖的我过得很安逸,大家都称我为“了不起的女人”,尽管我从未做过任何了不起的事情。大家都赞美我宽广的身材和洋溢着母性的外表。曾经有一位年轻的女性在公交车上给我让座,但我猜她比我岁数要大。我拒绝了。她很坚持。我意识到她认为我怀孕了,于是和气地接受了。大家都喜欢我,我很享受。我是霍金斯太太。
作者:[英]缪丽尔·斯帕克
编辑:薛伟平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