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精彩请观看视频
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的作者,“垮掉的一代”的代言人,无数人的灵感源泉:鲍勃·迪伦、披头士乐队、帕蒂·史密斯、乔布斯……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传记,《杰克之书》是多声部的访谈与回忆,拼凑出凯鲁亚克的肖像,还原了“垮掉的一代”众声喧哗的热闹场面。艾伦·金斯堡、威廉·巴勒斯、马尔科姆·考利等众多文艺界大咖齐聚一堂接受采访,《在路上》中的人物变身真人开口说话。他们的语言,重新创造了凯鲁亚克在马萨诸塞州洛厄尔度过的童年、在格林威治村的历险、跃升为文坛明星的经历,以及他47岁那年在佛罗里达的悲惨结局。
艾伦·金斯堡读过本书后惊呼:“这就像是《罗生门》——众人撒谎,真相毕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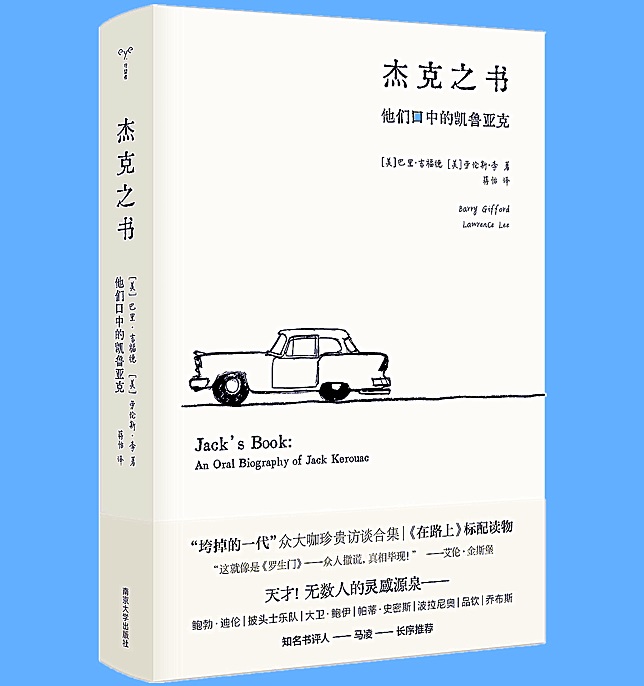
▲《杰克之书:他们口中的凯鲁亚克》,[美]巴里·吉福德、[美]劳伦斯·李著,蒋怡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
>>内文选读:
新版序
1936年5月30日,在一封给阿诺德·茨威格的信中,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写道:“为他人作传者,须投身于谎言、蔽障、伪善、错色中,乃至掩饰理解的缺失,实为传记之真相不可得,倘使偶有得之,亦不能挪而用之……真相不存在,人类不配拥有它……”
我和拉里·李谨记弗洛伊德的告诫,故选择了相当不正统(当时是1975年)的“口述史”来捕捉杰克·凯鲁亚克短暂一生的记录。拉里称之为“一种相当直接的作传方式”。我们的想法是,既然凯鲁亚克的亲朋好友中大部分人仍健在(他因长年酗酒而早早离世,终年47岁),那么,兴许我们能找到他们,然后说服他们坦率地聊一聊当事人,接下来就交由我们——还有读者——去爬梳种种不同的说法,决定谁的版本最贴近那无从躲藏的“真相”。杰克多年的好友、诗人艾伦·金斯堡在读完本书尚未编校的毛样后称:“我的天哪,这就像是《罗生门》——众人撒谎,真相毕现!”艾伦的话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这是他一字不差的原话。
艾伦真诚地希望,凯鲁亚克能被置于“最明亮”的聚光灯下,这无疑是因为在“垮掉的一代”最风光的时候,杰克——和艾伦,还有其他的同时代人——曾受到过批评家和新闻媒体的无礼相待与伤害。虽然《杰克之书》很可能暴露了凯鲁亚克的各种缺点,但我和拉里·李的意图是让人们沉浸到他那11本几乎遭人忘却的小说及其他作品中。当我们为了写这本传记展开调查时,市面上只有三本凯鲁亚克的书在售:《在路上》《达摩流浪者》和《梦之书》。到1980年,《杰克之书》出版两年后,他的书至少有八本能够买到。2012年,凯鲁亚克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推出了新版,小说《在路上》和《大瑟尔》被翻拍成了电影,他差不多成了一项产业。
我和拉里并没有打算把《杰克之书》写成一本“权威的”论著。我们相信,更精深的研究会紧随其来。“我死之后,”凯鲁亚克曾写道,“管它洪水滔天。”果不其然,那场雪崩立刻就爆发了,其实现在仍未结束。我们想要为此人的一生创造一场谈话式的、小说般(以对话的形式展开)的回顾。我们想要他认识的、爱过的、恨过的人和那些认识他、爱过他、恨过他的人畅所欲言,不给他们太多的时间、太多的岁月去思考说什么好。多数情况下,这些人还没有公开发表过关于杰克·凯鲁亚克的言论。他们的想法很新鲜——直到说给我们听,直到大声说出来,他们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有一个书评人称:“如果你有兴趣,想听一听50年代的谈话是什么样的,如果你相信文学跟生活多半有点儿关系,那么就读一读这本书吧。”谈话,这正是我们所追求的。
小说家兼记者丹·韦克菲尔德后来在他的回忆录《50年代的纽约》里记录了那段岁月,他慷慨地把我们的传记描述为“一份引人入胜的文学和历史文献,对‘垮掉的一代’最具有洞见的审视”。在我们看来,这里的关键词是文献。《杰克之书》的结构类似于纪录片,是一部凯鲁亚克在他的小说《萨克斯博士》中所说的“书式电影”。与韦克菲尔德先生年龄相仿的其他人则怪罪我们不该重新关注凯鲁亚克。他们当年就不喜欢他和/或他的作品,现在依旧讨厌他,也不乐意人们再关注他——连带着也不喜欢我和拉里。我们才不在乎哩,我们重视他的作品,以至于花人生的两年时间去推动凯鲁亚克之球再次滚动起来,这些完全在我们的意料之中。
我们知道,光是提到杰克·凯鲁亚克的名字,就足以激怒一些人。我们也知道,他的小说启发了千千万万的读者——尤其是年轻的读者——愤然离开他们身陷的抑或无趣抑或无望的处境去探索人生。我会一直敬重作家托马斯·麦瓜恩,因为他敢在一篇文章里公开表示,说他麦瓜恩永远也不想听到一句关于凯鲁亚克的坏话,因为杰克确实对不少人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他向我们灌输了一个大道理……你不必一辈子在俄亥俄州的迪普斯蒂克生活,”麦瓜恩写道,“凯鲁亚克鼓励我用自己的车钥匙,开上了高速公路。”姑且不谈凯鲁亚克的文学地位究竟如何,至少他拥有感化他人的力量。
杰克·凯鲁亚克并非神仙下凡,《杰克之书》也无意效仿圣徒传。本书(称它传记也好,报告文学也罢,再或是拼贴画、神圣的集锦、邪恶的乱麻,不管它是什么,会被人说成什么)包含一些极其感性和剖白的材料。它读起来一点儿也不枯燥。尽管有弗洛伊德医生的名言在前,读者在本书里还是多多少少会窥得些许真相。本书是属于那些跟我们敞开心扉谈论故去的朋友或劲敌的人的。因此,它也属于凯鲁亚克,这就是我帮它起名为《杰克之书》的原因。人们出于种种理由,在这位故人生前没有告诉他自己对他的真实想法,这些是他们写给他的书信。我和拉里很荣幸地为他们递上这迟来的机会。
我永远也忘不了,跟丹佛的桌球老手——驼背吉米·霍尔姆斯一起,坐在他年迈的阿姨家中那间闷热的客厅里,当时他住在那儿,我大声地朗诵了《科迪的幻象》中令人动情的一段,那是凯鲁亚克基于他曾经的生活写的。霍尔姆斯从来没有读过,听完后他对我说:“我不知道杰克那么在意我。他是真的在意,对吧?”我也忘不了在2月的一个严寒的凌晨,吕西安·卡尔喝醉了酒,跌跌撞撞地走在包厘街上,嘴里不停地重复着那几句话:“我爱过那个人,我爱过杰克,真该死,我居然从来没有告诉过他!”
第三章 路
6月,利特尔和布朗出版社拒绝了《在路上》。但过后的那个夏天,供职于维京的批评家兼编辑马尔科姆·考利写信给杰克,同意他从书里选一段文字给阿拉贝拉·波特看,后者是西涅图书发行的高质量平装本评论《新世界写作》的一位编辑。自从菲丽斯·杰克逊没能让这本书出版以来,杰克就愤怒地与MCA断绝了往来,但是考利被书的新奇感打动了,成了杰克的拥趸。他在1954年写的综述性作品《文坛现况》中如此赞扬书稿:
有一个相当大的群体,他们拒绝服从,发起了一场顽强的叛变——很难说他们反抗的是什么,因为这个群体并没有制定章程,但他们很有可能是在反抗同龄人接受的法律、习俗、恐惧、思维习惯和文学标准这一整套传统……他们经常谈论“地下人”,自称是“垮掉的一代”。发明这第二个称谓的是杰克·凯鲁亚克,他尚未出版的长篇叙事《在路上》是对他们生活的最佳记录。他们在两个层面上跟大多数传统的年轻人无异:他们不关心政治,即便是吸引观众的体育比赛也让他们提不起兴趣,他们在寻找某种信仰,一种会允许他们与世界和平相处的真正的宗教信仰。
马尔科姆·考利:
我第一次注意到凯鲁亚克,是因为他交到维京出版社的《在路上》的手稿,具体来说是交到在维京出版社工作的我手里。我不记得它是怎么来的了。有可能是艾伦·金斯堡带来的。那时,书稿已几经易手。在某个阶段,它已经修改过,重新打印出来,等交到维京出版社时,它是按传统的方式编页的。
我带着极大的兴趣和热情读完了手稿,我在维京的一次会议上说起它,让两三个编辑也去读了,但是不行,他们不肯出版。我很在意这件事,心里想:“这是全新的东西,应该要出版出来给读者们看看。我们得为它铺好路。”
当时的维京是一家相当保守的出版社,他们觉得我们的销售员不会愿意把这样的书摆在书店里,所以手稿就一直放在我的桌上。凯鲁亚克来找过我几次,我说:“你首先要做的,是找出其中的一些选段,先登在杂志上。”于是我就选了叫“墨西哥女郎”的那一段,给了《巴黎评论》,他们挺热情地接受了。然后我又看看还有哪些选段可以单独发表。那就是关于旧金山爵士乐的一段,阿拉贝拉·波特把它登在《新世界写作》上。
时间慢慢地过去。我跟杰克继续碰面,有时候,艾伦·金斯堡会跟他一起来。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和杰克去城外。我想让他带我去看看格林威治村的新型酒吧,对于那些我完全不熟悉,我已经二十年没怎么回过格林威治村了。他就带我去了。我记得他信誓旦旦地说,五十年后,世界上只会留下两种宗教。我好奇地问:“是哪两种呢?”他说:“伊斯兰教和佛教。”那让我相当惊讶,因为杰克是在天主教家庭长大的,这是他的本性里最固定的一部分。
所以,我时不时地会跟杰克和艾伦·金斯堡见面,给他们些建议。我觉得,艾伦想过也许我可以当垮掉派的类似于年迈祖父的角色,可我对这个主意不感兴趣。
……
维京雇了一位新编辑,叫基思·詹尼森,基思以极大的热情读完了手稿,他有能力和信念让他的策划获得成功。这一回,基思在我的帮助下,让《在路上》通过了维京的会议。最终,书稿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
威廉·巴勒斯:
杰克会坐着一连写上好几个小时。手写,全是手写。他会坐在一个角落里,说:“我不想有人打扰我。”我不会去在意他。他不停地写啊写。
凯鲁亚克的写作方法对他而言很管用。那并不意味着对其他人也管用,因为对我来说就完全行不通。我不以那样的方式写作。我会修改。他总是说第一个版本是最好的。我说:“也许对你来说是最好的,但对我而言不是。”我至少要改过三稿,稿子才能基本成形。当然,这是沃尔夫留下来的传统。创作的方法也非常相似,就是以极快的速度让语词流淌和写作。
在墨西哥那会儿,他的全套理论都运用得很好。也就是用语词来打草稿,注意语词的流淌,用第一稿——第一次想到的那些词。
作者:[美]巴里·吉福德、劳伦斯·李
编辑:薛伟平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