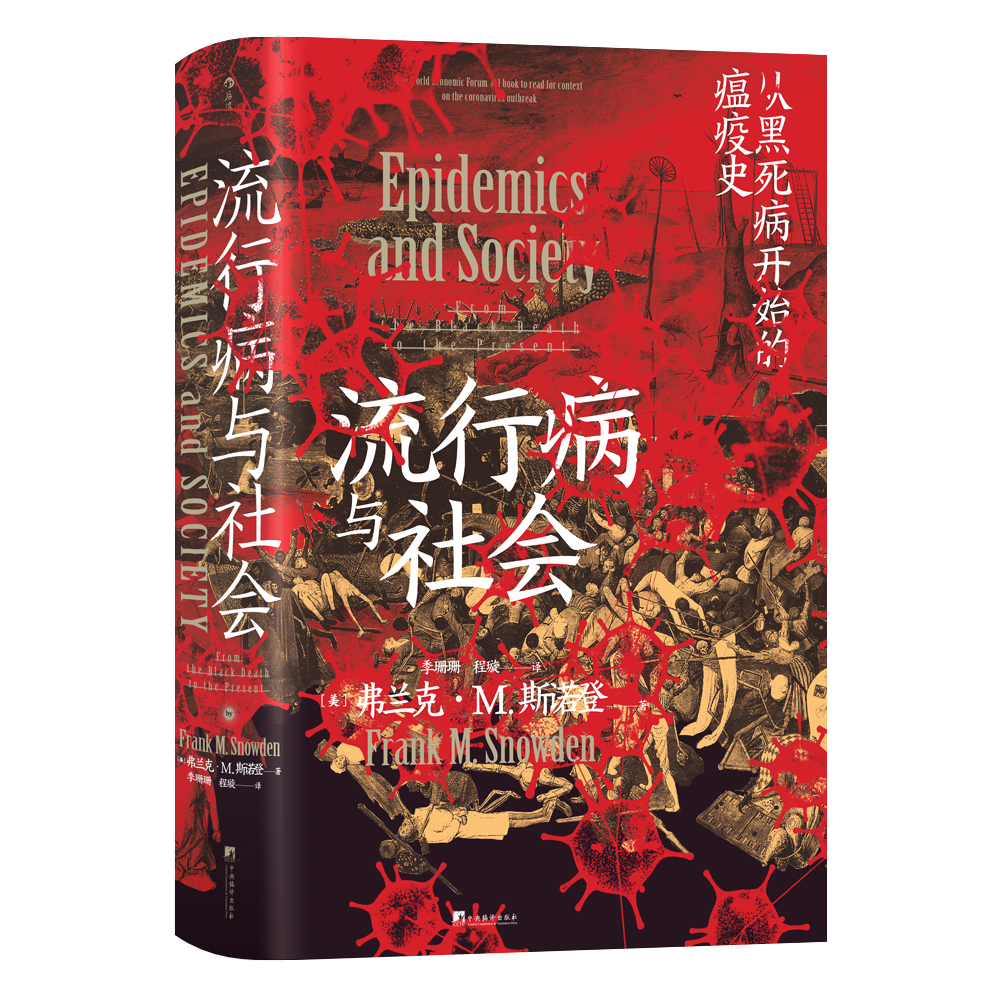
《流行病与社会》
[美]弗兰克·M. 斯诺登 著
季珊珊 程璇 译
后浪 |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流行病与社会》讲述了可怕而震撼人心的千年瘟疫史。微生物的致命威胁无数次逼近人类:鼠疫、天花、黄热病、痢疾、斑疹伤寒、霍乱、结核病、疟疾、脊髓灰质炎、艾滋病、SARS、埃博拉病毒……
针对这些深刻影响人类历史的流行病,斯诺登将专业权威的医学知识与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熔于一炉。
本书论述范围极广,跨越古今,遍及全球,深入展开医学与社会历史间的多学科比较研究,向我们揭示了流行病与社会的交互影响:一方面,疾病如何推动医学科学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如何塑造艺术、宗教、思想史和战争形态;另一方面,社会因素又如何让疾病获得适宜环境,迅速传播,肆虐人类。
>>内文选读:
在人类与微生物漫长的历史角逐中,20世纪中叶到1992年可以说是一个标志性时代,在这段令人欣喜若狂的岁月里,人类达成共识,认为与微生物一决胜负的时机已经到来,击退流行病、赢得最终胜利已经指日可待。1948年,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宣称,人类已经具备从地球上消除流行病的能力,新时代似乎已然来临。马歇尔的看法绝非特例。战后初期,一些人认为人类可能首先在一种疾病上面取得了胜利。疟疾学似乎实现了人类的这种夙愿,洛克菲勒基金会科学家弗雷德·索珀与保罗·罗素自认为发现了DDT这种强大的武器,就能帮助全人类彻底摆脱疟疾这种古老祸患。1955年,罗素抱着过于轻率的信心,出版了《人类对疟疾的掌控》一书。这本书设想了一场全球喷洒运动,致力于帮助人类迅速摆脱疟疾,代价低廉,简单易行。世卫组织受到罗素乐观主义的感染,以DDT为首选武器,发起了一项全球疟疾根除项目。项目的负责人埃米利奥·潘帕纳提出了一项通用的疟疾根除计划,包含四个示范步骤(“准备、攻击、巩固和维持”)。意大利战后抗疫运动的负责人阿尔贝托·密西罗里和定量流行病学创始人乔治·麦克唐纳德是罗素的拥护者,他们认为灭杀蚊子的成功如此振奋人心,应该很容易推广到所有由其他病媒传播的热带疾病,从而使人类迈入密西罗里所说的“没有传染病的伊甸园”——在那里,医学能保障人类的健康与幸福。
疟疾学家主导了国际公共卫生领域,他们提出的人类征服传染病的构想,迅速发展为一种流行的正统观念。胸科专家也开始坚信,结合卡介苗和“灵丹妙药”(如链霉素、异烟肼)两项技术创新能够根除结核病。这些专家甚至为美国和全球分别设定了2010年和2025年的根除期限。田纳西河谷管理局的首席疟疾学家兼世卫组织疟疾专家委员会成员辛曼,在1996年出版了《全球传染病的根除》。这是一本颇具影响力的著作,辛曼在其中将人类抗击疟疾的胜利推广到所有传染病方面。
艾丹·科伯恩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杰出的流行病学家,也是世卫组织的顾问。他在题为《进化与消灭传染病》(1963)的著作中详细解释了这一新信条。科伯恩指出:“人类追求‘根除’传染病的公共卫生理念,只有不过短短20年的历史,但它已经取代了‘控制’传染病的旧目标。”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科伯恩撰写该书时,人类尚未征服任何一种疾病,但他依然相信根除疾病的目标是“完全可行的”,该目标不仅针对个别疾病,还能够囊括所有传染病。事实上,他论证说:“这种预期似乎是合理的,在一定时间内,例如100年后,所有主要传染病都将会消失。”他继续写道,那时候流行病只会出现“在教科书里,或是作为标本”保留在博物馆中。“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他认为,“流行病的终结一定会到来,如今我们要关心的就是如何行动,以及何时开始采取必要的行动。”
在有些人看来,科伯恩所设想的2060年全面根除流行病的时间表还太过保守。仅仅十年后,1973年,澳大利亚病毒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与他的同事大卫·怀特一起声明,“至少富裕的西方国家”已经实现了这一宏伟目标。伯内特在报告中主张,“人类生存的古老危害之一已经消失”,因为“如今严重的流行病差不多已经销声匿迹”。世卫组织也认为全人类可以在20世纪末迈进一个新时代。1978年,世界卫生大会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举行,会议设立了“2000年,人人都能享有健康”的目标。

人类到底为什么对凭借科学、技术和文明的力量战胜流行病怀有如此盲目的信心呢?首先是历史原因。19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工业国家传染病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大幅下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进步”(薪酬提高、住房条件改善、饮食均衡,以及人民普遍受教育)的结果。同时,发达国家建造了各种坚固的卫生和公共卫生堡垒,包括修建下水道、污水管系统,采用泥沙过滤技术和水氯化处理,预防霍乱和伤寒;建立卫生警戒线,采取隔离措施,预防鼠疫;注射天花疫苗;首次使用奎宁对抗疟疾。同时,食品加工技术也不断提升,巴氏杀菌法、罐头消毒、海鲜生产的卫生措施等技术得到广泛应用,这些技术帮助人类在抵御牛结核、肉毒杆菌中毒和各种食源性疾病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因此,到20世纪初,过去许多可怕的流行病呈衰退趋势。究其原因,主要是人类抗疫经验的积累,而非科学技术的应用。但科学的进步很快就开始为人类提供强大的新武器。路易斯·巴斯德和罗伯特·科赫建立的疾病的生物医学模型,极大地促进了人类对疾病的了解,引发了一系列科学发现,并且催生了许多新的附属专业(微生物学、免疫学、寄生虫学和热带医学)。与此同时,人类迎来了抗生素时代的曙光,青霉素、链霉素的发现,为梅毒、葡萄球菌感染和结核病提供了治疗方法。疫苗接种也大大降低了天花、百日咳、白喉、破伤风、风疹、麻疹、腮腺炎和脊髓灰质炎的发病率。此外,DDT的研发,似乎提供了彻底消灭疟疾和其他昆虫传播疾病的病原体的可能方法。所以到了20世纪50年代,科学的进步已经为人类抗击肆虐的流行病提供了许多有效工具。面对如此巨大的技术飞跃,许多人自然会认为,人类可以逐一攻克所有的传染病,直到取得最终的胜利。的确,全球抗击天花运动就是很好的案例,世卫组织在1979年宣布,天花已成为有史以来人类战胜的第一种传染病。
在那些主张根除传染病的人看来,微生物世界基本是静止不变的,或者顶多是在缓慢进化。因此,几乎没有人担心,人类在消灭流行疾病时,会因缺乏准备、免疫不足而感染新型流行病。很不幸,这些人遗忘了沉痛的历史教训:在过去的500年中,西方国家经常遭受灾难性的新流行病的侵扰,如1347年的鼠疫、14世纪90年代的梅毒、1830年的霍乱和1918—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
伯内特就是其中典型。作为进化医学的奠基人,他在理论上承认病毒或细菌突变可能产生新的疾病。但实际上,他认为这种情况几乎不会出现,根本不需要担心。伯内特写道:“也许会有某种危险的传染病突然出现,但50年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事会发生。”“微生物种群固定性”这一概念认为,人类只会被已知的细菌和病毒感染。1969年,《国际卫生条例》(IHR)以它为理论基础,明确规定19世纪三大致死流行病(鼠疫、黄热病和霍乱)是唯一需要“通报”的疾病。按照法律要求,当有人被确诊为这三种疾病时,有关机构应通报给国家与国际公共卫生组织。这种以三种已知疾病列表为根据的通报制度,没有考虑如有未知的致命微生物传播需要以怎样的措施应对。
如果说微生物世界相对稳定的理论是根除主义者的信念源泉之一,那么进化理论也发挥着强烈的误导作用。进化理论认为,自然界本质上是良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传染性疾病会因为自然选择而往低毒力方向发展,原则上来说,致死率高的传染病往往会过早杀死宿主,因而无法继续传播到其他宿主身上。因此,支持者断言,于长期而言病毒将朝着与人类共存、保持稳态的方向发展。新型流行病虽然最初毒力较强,但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后,它们将逐渐发展为轻症疾病,最终演变为轻而易举就可治愈的小疾,例如天花从大天花演化为如今的小天花,梅毒从16世纪的暴发型梅毒转变为如今的慢性病,古典型霍乱现在也转变为温和的埃尔托型霍乱。
同样地,进化理论还认为,在人类疟疾家族的四种常见类型中,最致命的恶性疟原虫疟疾是新产生的,其他三种致命性较弱的间日疟原虫疟疾、卵形疟原虫疟疾和三日疟原虫疟疾则已进化得更易与人类共存。在此背景下,1974年版的《哈里森内科学(第7版)》成为根除主义时代的标准内科教科书,该书称传染病的特点在于“比其他疾病更容易防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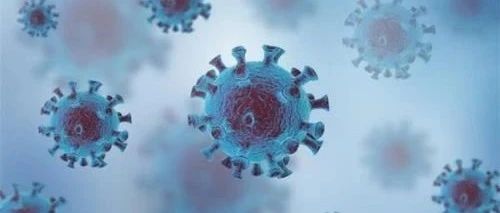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流行病学教授阿布德尔·欧姆兰提出了新时代最详尽、最广受引用的“流行病学转型”(或称“健康转型”)理论。欧姆兰与同事在1971年至1983年间出版了一系列富有影响力的著作,分析了人类社会在现代与疾病的遭遇。根据他们及期刊《健康转型评论》的说法,人类已经历了健康与疾病的三个现代纪元。尽管欧姆兰对于第一个纪元(“瘟疫与饥荒时代”)的精确时间范围尚无明确界定,但很明显,这一时代在西方一直持续到18世纪,以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中流行病、饥荒和战争的现实性抑制为标志。
随之而来的是“流行病消退时代”,在西方发达国家由18世纪中叶开始,直到20世纪早期,在非西方国家则持续得更久。在此期间,传染病死亡率逐渐下降,典型例子就是结核病。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终于迈入“退行性与人为疾病时代”。在病程早期,社会经济地位在健康与感染风险方面起着主导作用,而到了病程后期,医疗科技水平则更为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传染病死亡率与发病率降低,其他死亡原因变得更加常见,如退行性疾病(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代谢性疾病)、人为疾病(职业病和环境性疾病)和意外事故。美国卫生局局长朱利叶斯·里士满在1979年采用“健康转型”理论说明,传染病只是退行性疾病的“前辈”,最终会被形式简单、单向发展的退行性疾病取代。
公共卫生与科学的力量使过渡理论的支持者陷入盲目的自信,而这种自信又因遗忘历史而愈加膨胀。卫生局局长威廉·斯图尔德在1969年曾宣称,人类已经到了“抛开传染病书籍”的时候,这一观念显然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尽管欧洲和北美的医学专家纷纷鼓吹人类的胜利,传染病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最贫穷、医疗体系最脆弱的国家,仍然是最主要的死亡原因。结核病给人类敲响了警钟。虽然结核疗养院在发达的北半球纷纷关闭,但结核病却在南半球持续肆虐,也徘徊在北半球的边缘化地区,不断荼毒着无家可归者、囚犯、静脉注射吸毒者、移民和少数族裔等人群。保罗·法默在2001年出版的《传染与不平等:现代瘟疫》一书中指出,结核病根本没有消失。人们所认为的结核病消失,仅仅是一种因为它影响的人群过于遥远而产生的幻觉。实际上,根据世卫组织的保守估计,2014年结核病确诊人数与历史上任何时期相差无几。世卫组织报告还指出,2016年的结核病患者有1040万人,其中死亡的有170万人,结核病依然是全球第九大主要死亡原因,也是致死人数最多的传染病,超过了艾滋病。
>>著者简介
弗兰克·M. 斯诺登(Frank M. Snowden),耶鲁大学安德鲁·唐尼·奥里克历史与医学史荣休教授。其著作包括《意大利南部的暴力和大庄园:1900—1922年的阿普利亚》(1984)、《1919—1922年托斯卡纳的法西斯革命》(1989)、《霍乱时期的那不勒斯》(1995)、《征服疟疾:1900—1962年的意大利》(2006),以及《流行病与社会:从黑死病开始的瘟疫史》(2019)。《征服疟疾:1900—1962年的意大利》曾被美国历史协会授予“海伦与霍华德·R.马拉罗奖”,并荣获美国医学史协会颁发的韦尔奇奖章。
作者:弗兰克·M. 斯诺登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