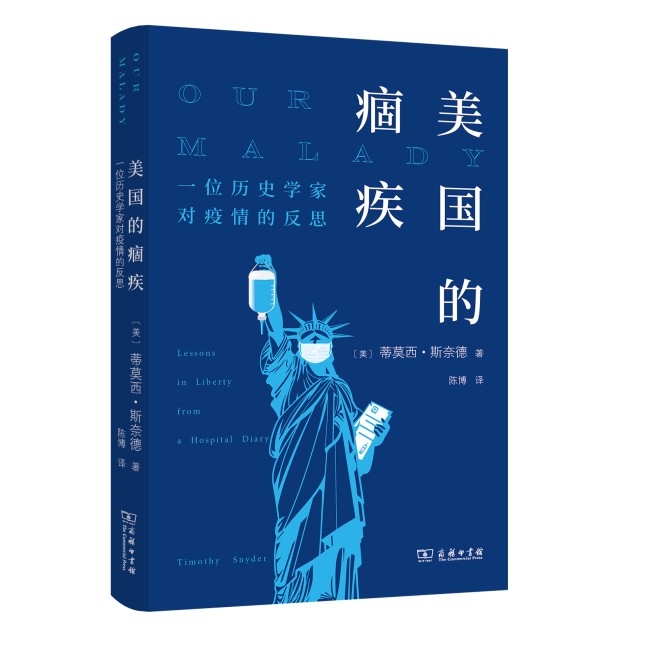
《美国的痼疾:一位历史学家对疫情的反思》
[美]蒂莫西·斯奈德 著
陈 博 译
商务印书馆2022年3月出版
《美国的痼疾》一书中,斯奈德将触动人心的个体经历与敏锐的历史和政治分析相结合,对美国利润至上、效率低下,专业意见被轻视,科学逻辑不断被政治左右的医疗体系,写下犀利而沉痛的呼吁。
>>内文选读:
序 言:孤独与团结
当我在午夜被送入急诊室,向医生描述自己的状况时,我用到了“萎靡不振”(malaise) 这个词。我的头很疼,手脚刺痛,一直咳嗽,几乎不能动。每隔一小会儿,我就止不住地颤栗。2019年12月29日,那一天才刚刚开始,却可能是我的终结之日。我的肝脏上有棒球大小的脓肿,感染已经破溃到血液。我当时并不了解这些,但知道情况一定很严重。萎靡不振,自然意味着虚弱和疲惫,一种周身无法运转却无能为力之感。
患病时,我们往往会觉得萎靡不振。萎靡(malaise)和痼疾(malady)都是古老的词汇,来自法语和拉丁语,在英语中也使用了几百年;在美国大革命时期,它们既表示疾病,也有暴政的意思。波士顿大屠杀后,有些波士顿名流写信呼吁结束“国家和殖民地的痼疾”。开国元勋在讨论他们自身以及他们建立的共和国的健康时,也曾用到“萎靡”和“痼疾/弊病”。
本书的主题便是某种疾患,这并非指我自身的病痛,尽管是病痛使我观察到了这一美国人共同面对的——借用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的说法——“我们的公患”。我们的病是身体上的疾患,更是与之密切相关的政治之恶 (political evil)。生病,使我们某种程度地失去自由(freedom);不自由(unfree),又不免有损我们的健康。美国政治中有太多痛苦的诅咒,太少自由(liberty)的护佑。
去年年底我生病时,脑子里总是想着自由。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20年来都在围绕20世纪的各种暴行来写作,如种族清洗、纳粹大屠杀等。我近年来所思考和演讲的主题是,历史如何抵御当下的暴政并保障未来的自由。我最近一次站在听众面前,是就“美国如何成为一个自由国家”做演讲。那天晚上我已觉得不适,但还是完成了工作,随后便去了医院。接下来的情况则让我对自由、对美国有了更深的思考。
2019年9月3日,当我站在慕尼黑的演讲台前,我的阑尾就在发炎。德国医生忽视了这一点。后来我的阑尾穿孔,肝脏被感染。对此,美国医生也未能发现。这最终导致12月29日我躺在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纽黑文市的急诊室里。当病菌在血液中奔走,我脑海中仍思考着自由。2019年12月到2020年3月,超过三个月的时间里,我辗转过五家医院,做了些笔记,画了些草图。当意志无法移动身体,或者当身体被束缚于各种袋子和管子当中时,自由与健康之间的紧密联系就很容易理解了。
当我翻看自己浸染着生理盐水、酒精和鲜血的医院日志,纽黑文医院的部分书写于那年的最后几天; 正是充溢于笔端的强烈情感,曾在我濒临死亡时拯救了我。是某种强烈的愤怒和某种温柔的共情支撑着我,也促使我重新思考自由。我在纽黑文写下的第一句话是“只有愤怒,孤独的愤怒”。我从未感受过比致死疾病中的愤怒更加纯粹、强烈的情绪。它在医院的夜晚向我走来,递给我一支火把,燃亮我此生的至暗时刻。
12月29日,在急诊室待了17个小时后,我接受了肝脏手术。12月30日清晨,我躺在病床上,手臂和胸口都插着管子;我无法握拳,但我想象自己正在握拳。我没办法用前臂在床上撑起身子,但我想象自己正在这么做。我只是又一间病房里的又一个病人,又一组衰竭的器官,又一条受感染的血管。但我的感受并非如此。我感受到的是一个动弹不得、怒火中烧的自我。
这种愤怒有种美妙的纯洁,没有被任何客体玷污。我并非对上帝生气,这不是他的错。我没有对医生和护士生气,他们也不过是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上不完美的人。我插着蜿蜒的管子,躺在病房里皱巴巴的床单上,病房外城市行人来去自由,送货员把门摔得巨响,卡车司机狂按喇叭,我也并非因这种种而愤然。我血液中的细菌正在庆祝丰收,对此我也并不愤怒。我的愤怒没有对象。令我愤怒的,是那个我并未置身其中的世界。
我怒故我在。愤怒的火把映照出我的轮廓。“孤独者的影子是独一无二的。”我在日记中晦涩地写道。我的神经元刚开始燃烧。第二天,12月31日,我的大脑开始从败血症和镇静剂中恢复。我终于能进行超过几秒钟的思考。第一段的延伸思考就与“独特性”有关。没有人曾经历我所经历的生活,做出和我同样的选择。没有人在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以相同的情绪度过新年夜。
我希望我的愤怒能带我离开病床,迈进新年。在脑海中,我看到自己的尸体,它正腐烂。腐烂的恐怖,可以预见。对每一个真正生活过的人来说,都是如此。而我想要的,是不可预见,我自己的不可预见,以及我与他人的不可预见之间的联结。
有几个晚上,我的怒火就是我的生命。就在此地,就在此刻,而我渴望着更多的此地,更久的此刻。我躺在床上,渴望再活几个星期,然后再多几个星期,我不知道那时自己的身体会发生什么,不知道那时自己会想些什么;但我至少知道,那个在感觉、在思考的人是我。死亡将终结我对世间万物“可能如何”和 “应该如何”的感受,终结我对可能性和美的感受。正如我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令我愤怒的是那种虚无,“那种特别的虚无”(that particular nothing)。
愤怒每次只出现几分钟,给我带来温暖和光明。尽管在发烧,我却一直都觉得冷。跨年夜的病床上,我渴望太阳升起,渴望阳光停驻在房间,洒在我的皮肤上。打了三天寒颤之后,我需要更多的温暖,单薄的铺盖却因胸口和手臂的插管而四面漏风。新英格兰的冬日晨曦透过厚厚的窗户已暖意无多;我活在象征和渴望里。
我不想自己心中的火把成为一盏孤灯。事实也并未如此。人们来探望我。妻子拉开窗帘,那一抹新年的气息也随之涌入。其他访客陆续到来,我会猜想他们在床边面对无助的我会作何反应,但我无法确知。我记得,一些来探望的老朋友相信,有人探望的病人会得到更好的治疗。他们当然是对的:归根到底,健康总是一件与“在一起”(being together) 有关的事,无论以何种方式。
探访有助于独处。团结在一起,可以让我们在宁静中回归孤独。朋友们哪怕只是出现,也会唤起记忆,令人回想起我们的过往。我想起有一次,有位朋友分享了“为什么要探望病人”的务实观点:多年前,是我在她的病床边探视,当时她生着病,又在孕中;而她当时就住在我正置身其中的这家医院。我想到了她的孩子,然后想到了我的孩子。另一种情绪正在凝聚:温柔的共情。
那愤怒纯然就是我自己:我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而非作为世界的回声;我想要创作,而非腐烂。除了整个宇宙和它的非生命法则,这愤怒不针对任何对象。有那么一两个晚上,我在自己的光芒中闪耀。
然而,第二种情绪慢慢地、轻柔地袭来,以另一种方式支撑着我:我感受到,只有当生命不仅仅与自己有关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生活。在我深陷孤独,对自己无能为力,甚至全部的动感都只能来自脑际想象时,这种情绪与愤怒一样,造访了我。在这种情绪中,我体味到自己和其他人簇拥着,滚过时间之流。我试图在日记中画出这种感觉,想到的是一个摆荡的、漂浮的载体。它看起来有点像一只木筏。
木筏可以由点滴材料逐渐搭造。我是木筏的一部分,其他人也是;我们在同一水面上漂浮、推搡,有时毫不费力,有时则可能撞到岩石。如果我那一条木板掉进深海,木筏可能会倾斜或覆没。筏子上的其他木板,有的离我的木板远些,有的则近些。我提醒自己,我的孩子们的生活如何与我的生活紧密相连。要紧的不是我的独一无二,而是我属于他们,是他们的父亲。他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期待着我的在场。他们从未与我切割。他们的木板一直与我的木板绑在一起。
我想象着,如果没有我,他们生活中那些让父母刻骨铭心的日常细节——足球训练,应对数学作业,高声朗读——会有怎样的不同。我痛苦地发现,想象中儿子、女儿没有我参与的生活的场景,竟然与我们过往共度的生活同样真实。我在脑海里看着他们的未来如何在没有我的情况下展开,随即抽离这样的思绪。
我的生命不只属于我自己,这种漂浮的思绪、温柔的共情,护佑我远离死亡。这种“生命被共享”的感觉从我的孩子开始,也向外延伸,参差的木材集合在一起组成木筏。我和我认识的、我爱的每一个人都在奋力踏浪前进,如果我现在倒下,所有人都会受到影响。在这种情绪下,我不再愤怒,而是在浮想、回 忆、沉思、共情。
愤怒帮助我看清了自己,帮助我的身体和心灵在受到冲击后重新振作。而共情将我置于他人之中。在这种情绪中,我是否特殊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其他人之中,在他们的记忆和期望中,为他们的生活形态提供支持,在困难时期充当浮标。既然我的生活不仅仅是我自己的,那么我的死亡也不仅仅是我自己的。当我理解到这一点,我又开始愤怒。一切,不能任其如此。
共情尽管与愤怒截然不同,却一起发挥作用。每种情绪都揭示了一个与我有关的真相和面向。二者缺一不可,皆为我所必需。我需要火把和木筏,需要火种和水源,需要孤独和团结,才能赢得健康,获得自由。这些对我而言确凿无疑,我猜想,对其他人也应是如此。
作者:蒂莫西·斯奈德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