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小区微信群里上演的“我的团长我的团”,到公寓楼里被各类物品堆满的互助小推车,再到“00后”UP主将自己做楼长的经历拍成“VLOG”……很多人的一个亲身体会是,消失多年亲密的邻里关系,在疫情隔离期间重新建立起来了。年轻人对于那句小时候常常挂在父母长辈嘴边的“远亲不如近邻”,突然有了亲身的体会。
针对于此,人类学家项飙曾经的观察“附近的消失”被自媒体反复引用“刷屏”,借以阐释现代生活里的邻里互动。
那么,项飙的“附近的消失”到底指的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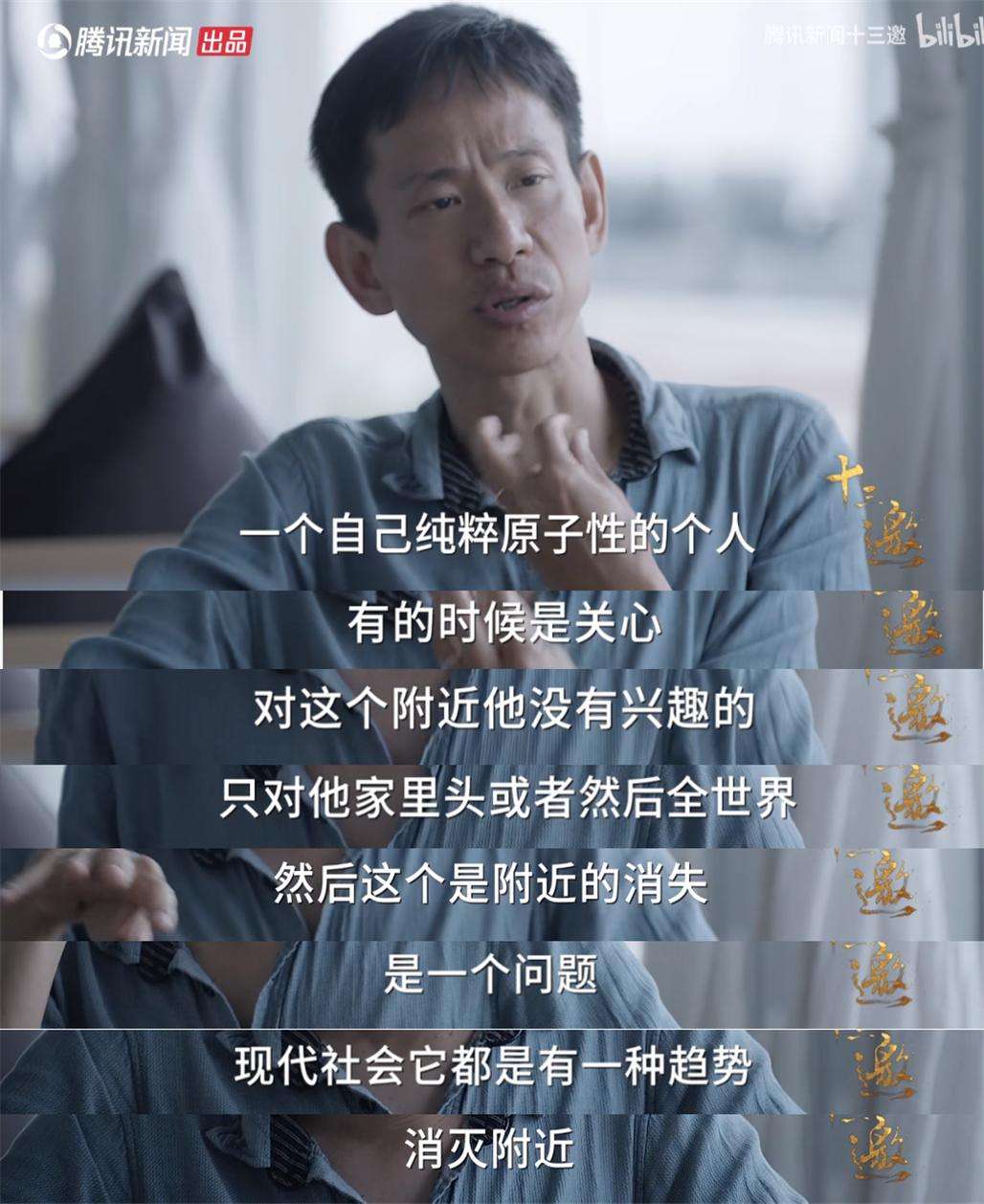
(一)
自媒体所引用的这一概念,引自项飙在节目《十三邀》的阐释。简单来说,即“对于自己周边世界,没有那种要浸淫进去,形成一个叙述的那种愿望或能力”。而这种“能力”的缺失,与另一种“超越”,形成了一组非常有意思的对照。他这样举例——
如果你问年轻学生,父母的工作是干什么?你居住的这个小区,当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这个小区在你的城市里面社会意义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周边的菜市场是什么关系?然后你的学校是怎么一个过程?
他们描述不清楚,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问题有点无聊、有点不重要。他们觉得更为重要的是“超越”这些,比如他们对要实现考好大学相关的世界排名、托福GRE怎么考这个系统很清楚。
这种“超越”不好吗?并不是。只是“超越”的意识原本应带来的,对于现实的“回观”不存在了。只有“超越”的结果是,回看自己身边的世界,变成了一个“要抛弃、要离开的东西”。
再换个角度看,是个体认知层次的断裂。即“家里头”与“全世界”两头之外,以附近为代表的的其他层次的退场。
在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项飙所观察到的“消灭附近”是带来效率与进步的——与其说是附近“蒸发”,不如理解为借由大数据和信息化承载而被“转化”掉了。
但这种效率与进步所带来的的生活转变,也在悄然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认知逻辑。
比如,我们依靠社交软件去认识婚恋对象,与其说是信任大数据匹配和海量注册增加的机会,不如说是失去在“附近”构建爱的关系的能力或信心,甚至于是消灭对于这种可能性的想象。
(二)
项飙又为什么提出这样一种观察?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项飙是谁。

项飙出生于1970年代的温州。上世纪90年代初,18岁的他考入北京大学。改革开放浪潮下,这座南方小城中的一批人,北上南下从商。身在北京求学的项飚,就关注到北京丰台区浙江商人的旅居社区“浙江村”。所谓村,并非自然村落或行政编制,而是聚居地。这些浙商在北京主要从事服装、五金电器、小商品、窗帘布艺等商品批发,因为比较强烈的同乡观念,聚居在一起。成为改革开放浪潮下,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发生转变的生动缩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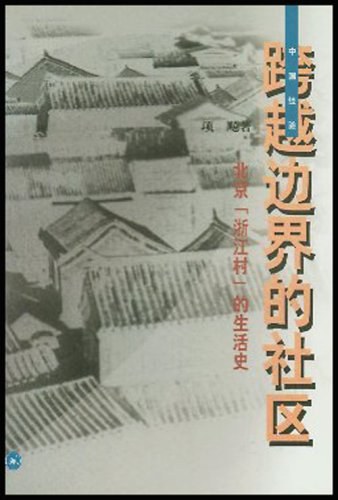
最初,项飙以同乡身份,将自己的观察,写成论文《北京有个“浙江村”》,参加1993年北京大学第3届“挑战杯”竞赛并获得北大一等奖,引发学界很大反响。此后,他持续深入,通过长达六年时间的参与式观察,最终完成了《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一书。本科完成如此独特、深入洞察的他,很快引发学界的广泛关注。在获得北大硕士学位同年,他受邀免考牛津大学博士。201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技术劳工》正是这一期间的研究成果。其所关注的,已经从国家内部人口流动带来的社会经济变迁,延伸为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劳动力流动中的种种现象和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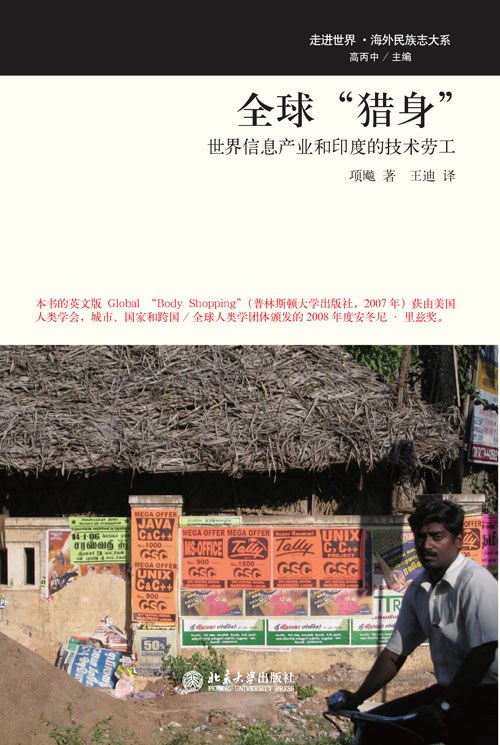
回溯其成长背景和研究脉络,我们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其所谓“附近的消失”的观察从何而来。
他所生长的浙江城市温州,对于亲族同乡有着较为强烈的归属感。而这种归属,即便在市场化浪潮下,在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依旧有着生动的延续。而进入新千年,在高速发展的互联网在改变生活方式与社会运转方式的同时,也在改变他过去研究对象那样依赖“附近”“多层次”的人际关系与经济结构。而这或许也就使得人类学家身份的项飙,有了更深刻的感知和思考。
他所主张的“附近的消失”,在人际往来方面,既能够解释因为疫情居家后连接更加紧密的邻里关系,同时也指向更多现象与变化。比如,对于层次感缺乏感知,其所感受到的世界是扁平化的。这种扁平化既指向邻里在个人生活里的“隐身”,同样对于社会生活认知中“小世界”构建的不完整。
项飙曾在采访里提到,在工作场景,倾向于把人打成“原子化”,与同事间的额外交流非常少,这就打碎了一层人的重要关系,使得人在职场失去了一个社会支持系统。“他们哪怕拿着几十万元的年薪,也觉得生活不好”,在项飙看来,这正是因为他们很难在现实中切身了解其他群体是怎样生存的,“只看到自己的某种特定生活方式,把生活过成了一个单线项目。”
在项飙看来,如果一个人有强大的“小世界”,会更从容。而“小世界”除了志同道合、互相扶持的朋友外,了解物理空间“附近”的人及构成,就会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比较客观,就会对自我有比较明确的界定,也就会比较从容。
而这种困在“原子化”与“世界化”的我的认知中的,其实不止年轻人。逐渐适应网络信息空间的部分中老年人,同样也在不知不觉中,“更愿意”接受并认可网络所传递的信息与观点。而这类信息通常又通过大数据筛选,强化他的既有认知,使之受困于“信息茧房”,更难去勾勒客观现实的全貌。
从传播学来看,“附近”所包含的人际传播,原本是意见观念、信息事实交流交换的缓冲空间,当这一层被抹去,撕裂与矛盾被更情绪化、更极端地呈现于互联网这一更为开放的公共空间,所带来的紧张焦虑都是每个个体所不能承受之重。
(三)
那么,重提“附近的人”与学者项飙,之于当下来说有什么价值?
项飙作为学者尤为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自本科针对“浙江村”研究开始所秉持的——“我相信长时期的观察是了解事实细微肌理的唯一可靠的办法”,一直被他坚守下来。
这种理念,使得他能够在20多年后,以个体经验为出发点,围绕议题,将习以为常的现象问题化,“再放回经验的抽屉”。吴琦将其总结为“把自己作为方法”,并以此来命名他与项飙的对谈录,试图凸显原本附着“自我”之上的历史脉络与社会关系。

而仔细追究,其实这是再朴实不过的、尤其是作为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基本素养——不是带着问题去观察,而是带着真诚与热情投身其中。只有当个体沉浸其中,方能以一种对“现实”的谦卑姿态,给出带有温度与关怀的思考。
回看自己本科时写就的、引发海内外学界轰动的《跨越边界的社区》,项飙不止一次表达过:“如果说《跨越边界的社区》有什么特别的优点,那就是我对调查对象的超乎寻常的熟悉亲密程度。这种熟悉,只有靠开放的、长时间的、不赶任务的‘浸泡’才能获得;没有这种熟悉,就不会有真正贴切和丰富的分析。”
他曾说,人类学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让你失望”。所谓“失望”,并非现实残酷与打击,而是很多时候“觉得自己很有道理,而且能和很多大的理论连在一起,但你一要问现实的人,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的一种“落空感”。
而作为学者、研究者,“那个落空感很重要,它就会逼着你去想新的现实背后的道理。”
这一套观念,之于普通人也一样适用。在撕裂冲突的舆论场与真假难辨的信息场,或许我们可以先放下这种赋予外在意义的强烈冲动,重新回到自己的附近,去全身心地投入现实,在实践中体察感悟,其并不一定通向最终答案或者终极意义,但却有助于更清醒、理性地看待问题。
作者:比由
编辑:陈熙涵
责任编辑:黄启哲
图:节目截图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