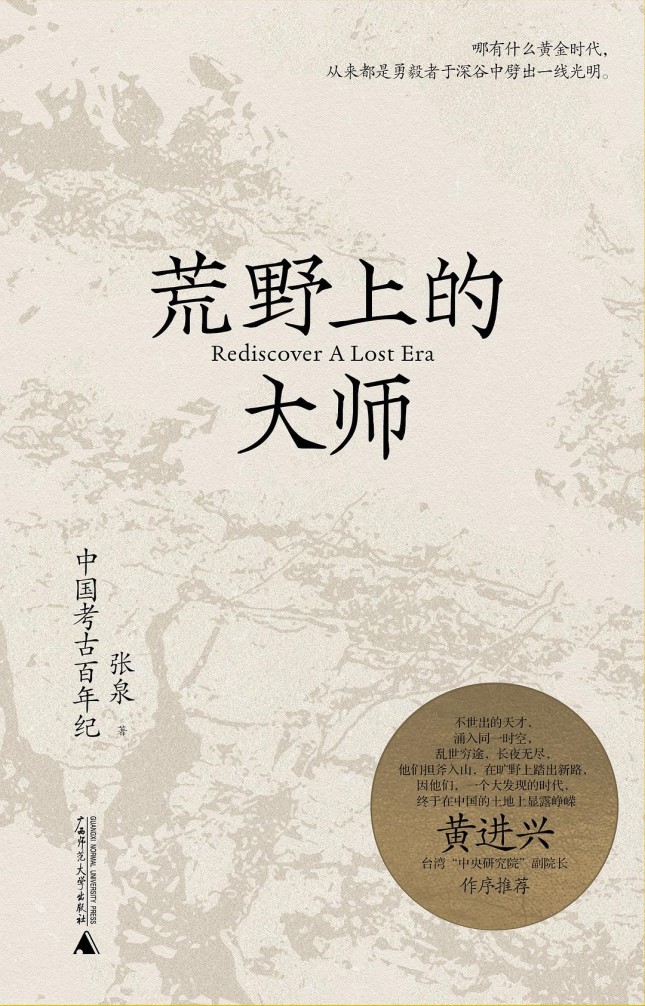
《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
张 泉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出版
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近代中国文化史上四座高峰,也是学人走出书斋、走向田野的先行者。本书发掘、重温以丁文江、翁文灏、袁复礼、杨钟健、傅斯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夏鼐、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为代表的一代大师的精神、思想与人生,他们以科学方法探索重建中国古史,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一个大发现的时代就此显露峥嵘。
>>内文选读:
李希霍芬的“偏见”
红皮肤的人
咳嗽声此起彼伏,海浪一般,从深夜直到清晨从未止歇。
丁文江和几十名矿工躺在一间用土墙围起来的草蓬里,整夜都没合眼。清晨起来,他发现,满地都是浓痰。
1914年,他用了大半个春天,深入云南,探访中国的锡都——个旧。白天待在矿洞里,几十步开外都能听见矿工们沉重的喘息声。他们早被生活的重负压弯了脊梁,矿石把皮肤染成红色,短暂的人生看不到丝毫希望。
但这还并非彻底的绝望。几个月后,丁文江从他们眼中读出了更加迷惘无助的神情。红皮肤的人衣衫褴褛,成群结队在山路上踟蹰而行,不知该何以为生。他们失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陷入战火,云南的锡矿顿时没了销路,许多矿场随之倒闭。20世纪初的世界,诸多隐秘的角落,就这样相隔万里却彼此关联。

丁文江
对于山外世界的变化,丁文江几乎一无所知。他辗转于云南、四川和贵州,这场孤独的旅途长达十个月,如同渔翁误入桃花源,早不知今夕何夕。
他随身带着帐篷、罗盘、经纬仪、空气高度计和照相机,沿着蜿蜒的金沙江,在荒山中穿行,踏勘地貌,考察矿藏。一路上要忍受酷暑、严寒与饥饿,昼夜温差动辄高达三十摄氏度,有时雨太大,帐篷都被淋透,能在乡间找块草垛睡一觉都值得庆幸。但他极为兴奋,不知疲倦地奔走。在个旧,他着迷于当地人摸索出来的采矿方法,开凿水渠,用流水冲出矿砂,这让在英国接受过现代地质学教育的丁文江大开眼界;然而,站在厂房里,他发现好几台从欧洲进口的采矿设备落满灰尘,竟然没有人会操作,又令他惋惜不已。
民间智慧与现代技术,就这样在深山中无声对峙,而中学与西潮的悄然角力,正是此刻中国社会的缩影。
轿子与帐篷
一路风尘仆仆,除了鼻梁上的眼镜,已经很难从丁文江身上发现读书人的影子。当地人尤其难以置信,一个从京城来的官员居然不坐轿子,却背着帐篷四处奔波。
轿子,却是丁文江最痛恨的东西。
“丝绸之路”的命名者、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曾把中国学者称为“斯文秀才”——他们留着长指甲,出门离不开轿子,还一定要带着书童随时伺候。他认为,中国很难开展地质调查,因为“中国的文人性情懒惰,历来不愿意很快行动。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既为自己的贪心而烦恼,又不能把自己从关于礼节和体面的固有成见中解脱出来。按照他的观点,步行就是降低身份,从事地质行当在人们心中就是“斯文扫地”。他的评价或许存在偏见,却无疑又揭示出某些真相:千年以降,中国的读书人始终对体力劳动心存芥蒂,他们寒窗苦读,就是为了逃离田野,登上庙堂。于是,像徐霞客那样不辞辛劳地探勘山水、孜孜记录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只是凤毛麟角,并且从未被主流接纳。即便进入民国以后,“赛先生”的名字即将在年轻人中间风靡,依然很少有人愿意学习地质学这样的专业。毕竟,地质考察需要风餐露宿,日晒雨淋,看起来不像个体面的职业;何况,那些冗长的术语、近乎离奇的发现与解释,听起来都匪夷所思,与人们熟知的“四书五经”格格不入。

李希霍芬
不过,李希霍芬的刻板印象并不适用于丁文江。
丁文江似乎是个天生的探险家。16岁时,这个极少出远门的泰州少年不顾家族反对,举债到日本留学。两年后,尽管他几乎不通英语,旅费也捉襟见肘,却还是说服了两个朋友,结伴前往欧洲。途经槟榔屿,他们礼节性地拜访了康有为,依靠康有为赠送的十个金镑,才终于完成了这场横跨半个地球的航程。到英国后,依然走投无路,丁文江险些去船坞打工,所幸,一位好心的医生帮助他留了下来,他才得以在剑桥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获得动物学和地质学双学士。经过专业的科学训练,冒险精神终于有了新的用武之地,回国后,他满怀憧憬准备探索崇山与疾流。他戴着眼镜,捏着雪茄,却以徐霞客自期。
1913年,在加入矿政司地质科第一天,他就问了一个古怪的问题——北京西郊的斋堂在哪里?听说那里出产煤矿。
没有人知道,更无人关心。地质科只是庞大的官僚机构下的一个小小科室,几个同僚对地质知识几乎一无所知,他们所想的,不过是按部就班地处理公文,上班下班,每月按时领取薪水。
踌躇满志的年轻人瞬间被抛进现实的旋涡,但他并没有被官僚系统吞噬,天真地试图依托地质科做些非比寻常的事。他深知,如果中国不进行地质勘探和科学研究,就只能依赖国外的学者和技术,无从发展,更无力自主;而想要改变现状,扭转李希霍芬式的“偏见”,必须从教育入手。
学不孤而闻不寡
丁文江的目标,是用三年造就一批地质人才,他们不仅要“学业优异”,更要“体力强健”。
推进地质教育,其实并非丁文江首创。地质科第一任科长章鸿钊也曾做过详细的规划。章鸿钊比丁文江大十岁,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地质学系,他之所以选择地质学专业,是因为中国地质人才匮乏,而矿业、工业、农业乃至商业,都与地质学息息相关,因此,他希望通过地质调查与研究,改变国家贫弱的状况。进入地质科之后,章鸿钊就草拟了《中华地质调查私议》,希望设立地质讲习所,培养专门人才,推进地质调查,但他未能如愿,随即转投了农林部。
所幸,继任者丁文江行动力出众,迅速与矿政司司长张轶欧达成一致。张轶欧同样从海外留学归来,先入读日本早稻田大学,后前往比利时,在海南工科大学获得路矿业硕士学位。他一直珍藏着章鸿钊留下的《中华地质调查私议》,希望能付诸实践。张轶欧和丁文江一拍即合,商定创办地质研究所,由26岁的丁文江担任所长。

1915年地质研究所教室
地质科资金有限,丁文江决定另辟蹊径。当时国立北京大学设有地质学门,但已经濒临终结,学生稀少,而且体格很弱,根本不适合田野工作;但是,北大地质学门拥有专业书籍、仪器和宿舍,这些宝贵的闲置资源正可以帮助地质研究所解燃眉之急。于是,丁文江与北京大学校长何燏时、理科学长夏元瑮商定,各取所长,合作培养学生。1913年夏,他主持了地质研究所的入学考试,选拔了30名学生。9月4日,工商部成立地质调查所和地质研究所,丁文江兼任两所所长。
“出走”的章鸿钊很钦佩年轻的丁文江,在丁文江的劝说下,欣然应允来到地质研究所,与丁文江一起指点这些年轻人。科学专业进入中国之初,面临重重阻力,前瞻精神与行动力都弥足珍贵,更难得的是,丁文江兼具了这两种特质。章鸿钊后来这样感叹:“丁先生是偏于实行的。往往鸿钊想到的还没有做到,丁先生便把这件事轻轻的做起了。这不单是鸿钊要感激他,在初办地质事业的时候,这样勇于任事的人,实在是少不得的。”
丁文江竭力想为学生们寻找更多优秀的老师,他还打算邀请任教于北京大学地质学门的德国教授梭尔格(Friedrich Solgar),尽管有些人认为这实在不是个明智的选择。他们觉得梭尔格非常傲慢,脾气很坏。不过,丁文江与梭尔格交谈了几次,又结伴外出考察,通过这些接触,他确信梭尔格很专业,而且可以合作。
他也并不一味地迷信外国专家。北大还有一个德国教授,带着一份井陉煤矿的地质图到地质研究所应聘,宣称是自己画的。不过,丁文江一眼就看出,他大概是把李希霍芬早年绘制的一张旧图放大了来冒充,于是断然拒绝了这个德国人。
又过了一年,丁文江终于等来第三个精通地质学的中国人,从比利时鲁汶大学留学归来的翁文灏,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主要研究地质、岩石和古生物。经章鸿钊引荐,丁文江与翁文灏一见如故,后者放弃了煤矿公司的聘书,加入地质研究所。“一战”爆发后,梭尔格应征入伍(后在青岛被俘),所幸,翁文灏的到来帮地质研究所缓解了教学压力,因此,章鸿钊把他誉为“本所最有功之教员”。
自此,丁文江、章鸿钊与翁文灏三驾马车并驾齐驱,为中国地质学界奠定了基础。

中国地质科学创始人,左起: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
在北洋政府臃肿的官僚系统中,丁文江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许多政府部门花费重金招募外国专家,可是,由于行政官员不学无术,根本不知道该怎样让这些外国专家发挥作用。农商部高薪聘请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就是其中之一。
安特生是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niversity of Uppsala)地质学教授兼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还曾担任世界地质学大会秘书长。他能被北洋政府任命为矿政顾问,不仅因为他的学术成就,更因为他的祖国属于“少数几个对中国没有野心的西方国家”之一。他也不负众望,接受聘书不久,就在河北宣化的龙关山和烟筒山等地发现了储量惊人的铁矿,因此受到时任大总统袁世凯接见,后来又被黎元洪授予“三等嘉禾章”。然而,勘察铁矿的过程中,他却对埋藏在大地深处的各种古生物化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当丁文江发出邀约,安特生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两人皆拥有广博的视野,对田野考察满怀热忱,彼此惺惺相惜。
几年过去,丁文江终于不再孤独,终于可以欣慰地感叹:“一所之中,有可为吾师者,有可为吾友者,有可为吾弟子者,学不孤而闻不寡矣。”
“十八罗汉”
学术领袖的视野,往往决定着一家研究机构乃至一个领域的格局与命运。
丁文江等人为地质研究所设置的课程,不仅仅局限于地质学、地理学、岩石学和矿物学,还涉及动物学、古生物学、冶金学、机械学、测量学,甚至照相术,他们试图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并着重培养实践能力。

翁文灏
强化田野考察是他们的共识。地质研究所规定,教师必须半年从事教学,半年外出考察,这样才能教学相长。丁文江坚持,“登山必到峰顶,调查不要代步”。翁文灏则强调,中国地质学界如果想要迎头赶上,“惟有担斧入山,劈荆棘斩榛莽”。丁文江、章鸿钊和翁文灏分头带领学生外出进行地质考察或测量实践,指导他们撰写考察报告,短则三四天,长则十余天,足迹从京郊蔓延到河北、山东一带。他们的背囊里一直携带着铁锥、指南针、倾斜仪、放大镜和小刀。气压计和望远镜也是必备的仪器,前者用来测定高度,后者用来观察环境。丁文江对学生还有更严格的要求,不仅要善于观察,认真采集标本,更要勤于记录,通过步速或步数来估算距离,每晚必须整理笔记,绘制地质图。如果学生爬山时赶不上他的脚步,他就会大声唱歌或者朗诵诗词来鼓舞他们。他希望大家在考察过程中学到的不只是技能,更是相互协调合作的精神。在他们的引导下,尽管这些学生只学了三年地质学,却都积累了丰富的田野经验。
这些年轻人依然用毛笔书写调查报告,誊抄在笺纸上,但在竖排的工整小楷中间不时会跳出英文术语和人名。他们还在调查报告里绘制了图片,小到标本,大到地貌,都如实地予以还原与分析。谢家荣和赵志新把各自采集的矿产标本放到显微镜下,再把观察到的形态描绘在纸上,并涂上颜色;赵志新甚至标注了石英、长石、绿泥石、磁铁矿和皓石在绿泥片麻岩中所处的位置;周赞衡手绘了杭州附近的地质剖面图;而李学清则用三维立体的形态绘制了山脉褶皱的方向图……尽管老师的评语和批注颇为严格,但他们对这些年轻人的成长显然很满意。

1916年,地质研究所教员和卒业生合影,前排为翁、章、丁三人
1916年,地质研究所有18人成绩合格,获得毕业证书——他们被戏称为中国地质学界的“十八罗汉”,地质研究所因此被视为“中国科学上第一次光彩”,却也就此完成了使命。此后,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的工作重心都转向了地质调查与研究,而以谢家荣、王竹泉、叶良辅、李学清等人为代表的“十八罗汉”也被悉数网罗进地质调查所,多年后,他们将成为中国地质界的中坚力量,主持着中国最重要的地质学机构,包括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的地质系。
丁文江兴奋地宣布:“我已经有了一班人能登山涉水,不怕吃苦。”作为中国地质界剧变的见证者,安特生也间接澄清了李希霍芬40年前的质疑:
一般的中国上流社会人士都不喜欢劳动,著者以曾和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士一同旅行的资格,敢在这证明,地质研究所的毕业生出门已完全不用轿子,而且十分明了野外地质学家的唯一行动工具只是两条结实的腿。

1919年丁文江、梁启超等人考察欧洲
地质研究所停办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却重新开张。1917年,蔡元培主持北大,成为中国教育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陈独秀被任命为文科学长,一大批明星学者、作家迭现,新旧思想激烈交锋,后人遂感慨于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称赞他对“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但事实上,获益的当然不只是人文学科,不只是环绕着《新青年》与《新潮》杂志的那一批文学闯将。
几年后,丁文江突然给蔡元培带来一张满是零分的成绩单。他原本期待着能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发现新的人才,于是给这批毕业生举行了一次考试,却失望地发现,许多学生甚至无法准确地鉴别出岩石的种类。他正告蔡元培,地质教育亟待改革。蔡元培立刻虚心地向丁文江请教,丁文江则向他举荐了两位人才。
一年前,丁文江曾陪同梁启超访问欧洲,顺路拜访了多位地质学家,一面向欧洲和美国的学术界介绍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工作,一面为中国地质学界招揽了两位杰出的学者,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研究采矿和地质学、获得自然科学硕士学位的李四光,以及美国著名古生物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葛利普,都将接受北大地质学系的聘书。
丁文江对李四光尤为关心。他担心李四光回国后生活清寒,先安排他到农商部矿政司第四科工作了一段时间,以便在北大开学前能领取薪水养家糊口,后来又帮他谋求了北京图书馆副馆长的兼职。这是丁文江的待人之道,一直无比热诚,无微不至。

中国地质博物馆中的一幅拼接照片,左起:高振西、李四光、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安特生、裴文中
随着葛利普和李四光的到来,北大地质学终于夯实了基础,从此脱胎换骨。四年后,丁文江已经敢于宣称,北大的地质学教育和西方大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在田野考察方面,甚至超越了除美国以外的绝大多数西方研究机构。毕十年之功,他终于可以自信地回应李希霍芬的“偏见”。
(本文摘选自书中《地质调查所:书生担斧入山》)
作者:张泉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