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别具一格的“有魅力的魏晋读本”。提起《世说新语》和其中以魏晋名士为代表的魏晋风流,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自由、个性、反抗等标签。《演而优则士——〈世说新语〉三十六计》一反老生常谈,认为魏晋名士的风流洒脱、放荡不羁并不是真性情,也不是所谓“个性的觉醒”,而更像是一场场经过精心谋划的“表演”,需要“观众”看到并广为传播,借助这条路径,以获得更佳的社会性利益,如声誉、地位、官阶等,所谓“风流”,只不过是一种精心且刻意的营造。这种基奠于《世说新语》文本的别样解读,令人耳目一新,鞭辟入里而又逻辑自洽,读来引人入胜。
读本书如同看剧,酣畅淋漓的同时而又别有会心。作者师从著名汉学家魏斐德,秉承西方历史写作传统,重叙事,以通俗悦读为目的,这样来聊《世说新语》和魏晋名士,除了讲述种种有趣、颇富韵致的故事外,更深一层,浑化故事背后蕴含的社会学动因于全书之中,并且加之以出色的心理分析。这样,专业读者能看到对经典的不同解读,而普通读者就仿佛看戏一般,看着这些魏晋之际的大名士上演一幕幕活剧,评判哪个的演技更为高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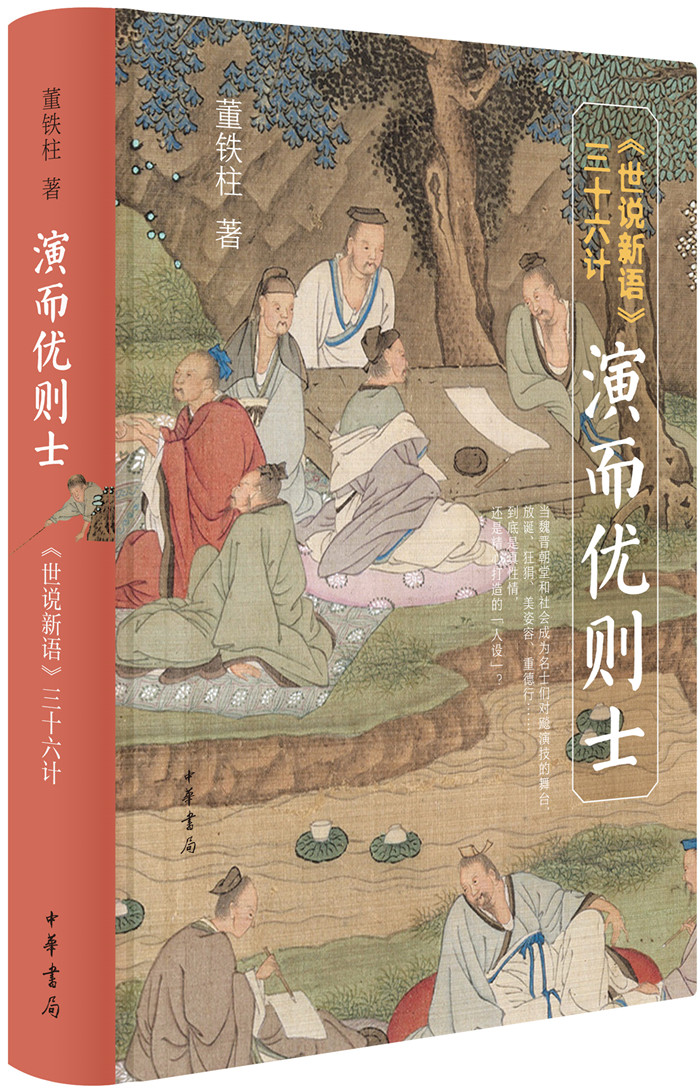
《演而优则士——〈世说新语〉三十六计》
董铁柱 著
中华书局2022年1月版
相关阅读:
第一章 人为什么要讲道理——清谈:聚会时的游戏
新婚后,女婿到了丈人家应该做什么?《世说新语·文学》篇中西晋裴遐的故事告诉了我们答案。《文学》篇第19则说:
裴散骑娶王太尉女。婚后三日,诸婿大会,当时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与裴谈。子玄才甚丰赡,始数交未快。郭陈张甚盛,裴徐理前语,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称快。王亦以为奇,谓诸人曰:“君辈勿为尔,将受困寡人女婿。”
裴遐与王太尉王衍的女儿成亲,婚后三日,王衍的几位女婿在王家聚会。王衍的女婿几乎各个都非常有地位,他的大女儿嫁的是贾皇后的亲戚贾谧,小女儿则嫁给了太子司马遹,当然裴遐也是出身名门,当时王、裴两家可谓望族,这一场婚姻也属于门当户对。这一天王、裴两家都来齐了人,在这样的场合大家要做的就是——清谈。
恰好当时在座的还有著名的哲学家郭象。郭象以善清谈而闻名,“口若悬河”这一成语,最初就是用来描绘他侃侃而谈的场面。郭象主动和裴遐展开辩论,郭象讲得气势磅礴,而裴遐则应对自如。在座的各位都极为佩服,王衍颇为得意地对大家说,你们就不要再挑战了,否则就要被我的女婿搞得狼狈不堪了。
这则故事可供玩味之处甚多。首先,在这样喜庆热闹的场合,大家不是玩樗蒲围棋,也不是比骑马射箭,而是喜欢看“主角”和人捉对清谈,然后众人旁观;其次,这样的清谈如果展现出高水平的话,可以获得他人的尊敬,浅白地来说就是可以让人有面子,故事中很显然王衍对自己女婿裴遐的表现很满意;再次,郭象在其中充当的角色也颇为有趣:到底他的故意挑衅是为了展现自己的才华让裴遐难堪,抑或是配合裴遐,为了凸显裴遐对玄学的理解和辩论之才从而获得老丈人的欢心,还是为给王衍做托,让大家知道他女婿的厉害……
《文学》篇中的另一则故事同样表明,清谈是名士们在一起时的不二选择。第55则说:
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诸人曰:“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
有一次支道林、许询、谢安等人一起聚在王濛家。谢安说,今天这样群贤毕至的集会机会难得,应当一起清谈。许询就问主人有没有《庄子》。刚好主人家有《庄子》的《渔父》篇。于是谢安就根据《渔父》选择了谈论的主题,让大家来谈论。支道林第一个谈,讲了七百多个字,词藻华丽,论述精致,大家都说好。然后大家一个一个接着谈论,最后是谢安出场,讲了一万多字,精妙绝伦,众人无不佩服。这则故事和上一则的相同之处,在于两个故事都告诉我们,在名士集会的时候大家喜欢清谈;不同之处则在于聚会的众人都参与了讨论。如果说上一则故事裴、郭二人是表演者而其他人是观众的话,那么在这里大家都是表演者而互为观众。当然,主角是很明确的,整个过程最重要的是突出了谢安高人一等的才华。
其最值得注意之处则在于一个细节:许询问主人家里有没有《庄子》。通常人们以为,魏晋时期玄学盛行,而玄学主要的探讨内容就是《老子》和《庄子》,那么当时的名士应该对《庄子》非常熟悉。但这则故事告诉我们,即使是支道林、谢安这样的清谈大家,对《庄子》似乎也不是全然熟稔的,至少不能烂熟于心;要找个大家都可以讨论的话题,还需要现找《庄子》的文本。在对《庄子》的文本并不非常熟悉的情况下,名士们对《庄子》哲学的阐发也许更多的是对自己固有思想的即兴表达。与其说这是对庄子哲学思想的探讨,不如说是一种文字游戏和表演。同时,许询问身为主人的王濛家里有没有《庄子》,而不是直接要王濛拿《庄子》出来,说明《庄子》并不是名士们家家必备的读物,而王濛家里只有《渔父》一篇,并没有《逍遥游》或是《齐物论》这样的核心篇章,也进一步让人思考:在那个号称对庄子思想非常推崇的年代,对《庄子》的重视程度究竟是怎样的,《庄子》又是以怎样的形式在魏晋时期传播的?
如果说这些名士对庄子哲学本身并没有足够的重视和了解,那么,他们又为何动辄在聚会的场合以庄子哲学为主题作清谈呢?庄子哲学对他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抑或我们也可以问,哲学——或者说是中国哲学——有着什么样的特质,可以成为他们在公共聚会时的谈资?
作者:董铁柱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