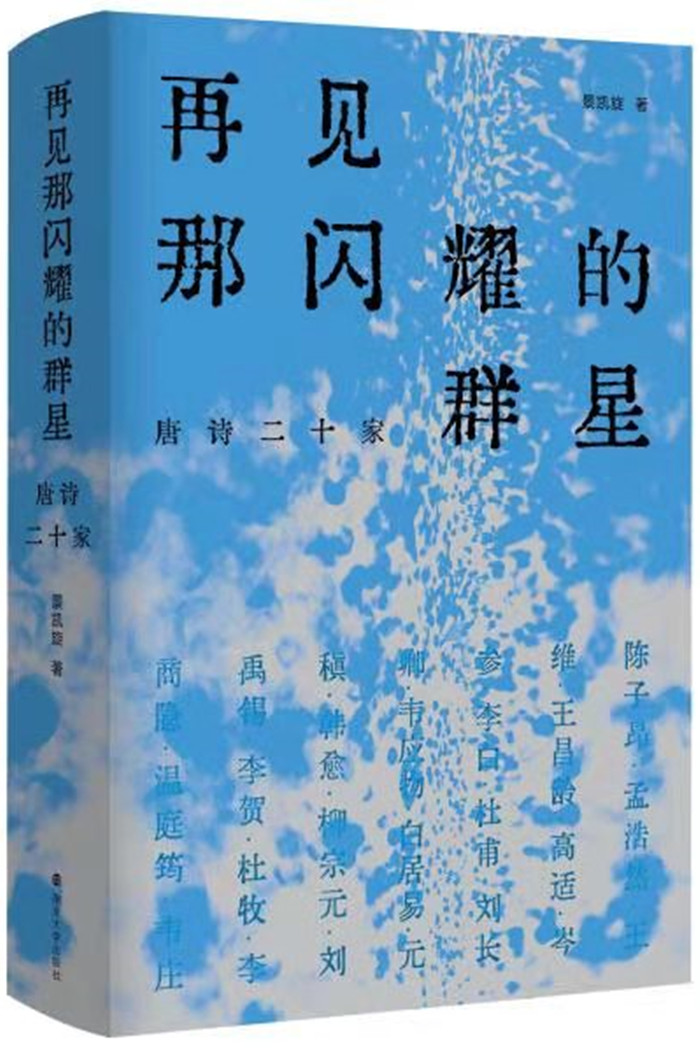
《再见那闪耀的群星:唐诗二十家》
景凯旋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再见那闪耀的群星:唐诗二十家》不是一部研究专著,而是一本诗歌随笔,是作者在唐诗中的一次游历。在谈及这二十位诗人时,尽量展示其最重要的作品,但并不做全面评价,而是对每位诗人采取不同的阐释角度。作者试图在唐诗的背后寻绎观念与价值的东西,比如中国人的天人之际、自我意识、时间观念和感觉方式,以及诗人的心路历程、审美情趣、人格品质和艺术技巧。此外,还收录了几篇附文,分别讨论唐代的僧人诗、女性诗、代言体,以及士人的角色处境。
正如作者所说:诗歌是唐代文人的事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诗歌,我们可以进入唐人的精神世界,从中寻觅到自己的知音。在精神层面,现代人并不比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柳宗元、李商隐高明多少,因为现代科学理性并不能解决生命意义的问题,而诗歌的作用正在于彰显意义。人生归根结蒂是不完美的,它需要不断地解释。
诗歌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痛苦而不是幸福联系在一起。古今中外那些伟大的诗人都有一种人生的悲剧意识,体验到个体生命与永恒事物之间的巨大鸿沟,即使在最快乐的时候,也对苦难的况味有一种迷恋。就诗歌所呈现的生命样式而言,王维渴望归去,李白憧憬远方,杜甫则始终行走在路上。
面对同样的夕阳,李商隐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歌德说:“西沉的永远是这同一个太阳。”李商隐感受到的是当下时间的短暂,歌德体验到的是超越时间的永恒。这似乎代表了中西文化在宇宙意识上的某种差异。
唐诗的价值是永恒的,它是人性悠长的回响。
相关阅读:各章精华
陈子昂(659—700)
遥远的过去来自黑暗深处,而未来更是沉没在无穷无尽的黑暗之中。这就是陈子昂眼中的世界图像。这是何其天荒地老的落寞!陈子昂是唐代第一个从群体意识中挣脱出来的诗人,他在旷野中呼喊的孤独具有文化史上的意义,那不是生命的感伤,而是自我意识的觉醒。
孟浩然(689—740)
孟浩然自己的人设始终是一个隐士,不是一个诗人。而与他同时代的诗人在面对功名利禄的巨大诱惑时,也需要捧出一个清高自由的隐士形象,以对抗自己身处的那个浮躁的盛世。
王维(701—761)
王维的诗是一种知性的美,不是一种伦理的美。他的“归去”没有远方的参照,因而他的诗缺少内在的人性冲突,缺乏附着于自由而不是自然的情感,总是引导读者进入无我的境界,对于存在意义的寻求也总是止于空无。“归去”于是成为他对生命有限性的一种妥协与回避。
王昌龄(698—756)
王昌龄的边塞诗和闺怨诗大都不是为自己而写,而是为时尚而写。如果说盛唐气象指的是一种青春的元气,那么王昌龄就是其最重要的代表。
高适(700—765)
今天的读者会发现,古人的价值世界还是比较单纯的,唐代的边塞诗书写着光荣与苦难、冲突与杀伐,却没有宣扬仇恨。族群仇恨的价值是现代人的发明,是在自然世界的价值消失后,人类进入历史世界才出现的情感。
岑参(约715—770)
许多唐朝文人其实从未到过西域或中亚,有的至多也就到过陇右。他们对西域和中亚的印象多来自前朝诗歌,然后借《从军行》《凉州词》《出塞》等乐府诗题来表现昂扬的书生意气。然而,岑参本人曾真正从军安西、北庭,他咏边塞之诗,句句从亲历中来,这使他成为与高适并称的盛唐边塞诗的代表。
李白(701—762)
自汉末至魏晋,士人中一直弥漫着“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悲剧意识。到了初唐,这个悲剧意识还在延续,人们不断被生命不居的瞻望所苦恼,继刘希夷“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张若虚“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之后,李白再一次举杯哀叹:“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杜甫(712—770)
杜甫被后人奉为“诗圣”是因为他的作品体现了儒家的社会关怀,但他的价值恰恰在于强烈的个体意识。自《诗经》以降,中国诗歌走过的是一条从整体意识向个体意识渐渐转变的道路,至杜甫终于达到了一个高峰。
刘长卿(约726—约790)
在一般人眼里,自然风景是没有情感的客观事物,只是供我们观赏,归根到底还是一种“我与他”的关系,而一个优秀的诗人具有移情的能力,能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变成“我与你”的关系。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懂得刘长卿山水诗的价值。
韦应物(737—791)
普通而平淡的人生写照是韦应物诗歌的独有魅力,这句诗看似恬淡潇洒,背后却有一种天涯沦落的情绪。人生的种种况味,似乎全在这十字之中了。我们仿佛看到,诗人一袭白袍,手持酒杯,从远处向我们走来,一直走到我们中间。
白居易(772—846)
白居易对隐逸作了一番新的阐释。他认为大隐隐于朝市,小隐隐于山林,但朝市过于喧嚣,山林又过于冷落,他的选择是中隐。白居易以自我保全作为基本价值标准,在个人与官场之间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界限,既不违背良知去迎合权贵,也不忤逆权贵而伤害自己。
元稹(779—831)
《行宫》的开放式结尾给人无尽的联想。唐代其他皇帝身后也留下了无数宫女,却都没有享受过此种追忆。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评道:“只四语,已抵一篇《长恨歌》矣。”让元稹伤感不已的不仅仅是过眼烟云的荣华富贵,更有春梦无痕的人间情爱。
韩愈(768—824)
当韩愈不再运用盛唐诗歌的“兴象”思维时,他就为诗歌开辟了另一条道路。这一转捩的原因之一是文人角色向士大夫角色的转换。强烈的主体意识导致诗歌观念的改变,人们不再愿意去追步盛唐那种对外在世界加以想象的诗歌,而是要从个体生活中去发现人的境遇,诗歌的人间性因此越来越多于超越性。
李贺(790—816)
李贺这位短命的天才诗人,就像流星一样划过璀璨的唐诗星空,让读者神迷目眩,又使我们超越了日常生活的平凡感觉,意识到生命的终极脆弱而无助。这样的诗人不可太多,但也不可缺少。
柳宗元(773—819)
柳宗元想要学陶渊明,放下仕途的“机心”,但他其实更像是在追寻屈原,那是一个清高贞洁的形象,在抒发着内心的孤愤。说到底,柳宗元从来都没有获得超然的自由,因为他的诗中始终有一个“我”在。
刘禹锡(772—842)
刘禹锡对天人关系的看法与司马迁接近,意义追求和价值期许都在人道之内,个体生命的圆满是通过群体生命的存在和延续实现的。这就是他屡遭政治打击却从不沮丧,反而更加积极对待人生的原因。对刘禹锡来说,自然的天道不足恃,人事的作用才最重要。
杜牧(803—852)
今天我们读杜牧的怀古诗,常常会感到主题上的重复。这也是唐代怀古诗的共同特点,总是在不断感叹朝代的兴亡,但终究不能在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上有所突破,看清历史循环的规律。这当然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时代的问题。更何况,在一个出身没落世家的诗人眼里,颓废从来都有一种无法抗拒的美。
李商隐(812-858)
李商隐渴望爱情,可又对爱的结局感到恐惧,他宁肯设想各种障碍,让女性永远像缥缈的女神一样神秘,而不愿跨过男女间的最后界限。李商隐将传统的艳情诗改造成爱情诗,完成了诗歌史上的一次飞跃。这些情诗无疑不属于传统的游子思妇,而是道出了男女情爱的本质:爱在终极意义上的不可实现性。
温庭筠(约812—866)
在温庭筠眼里,不但历史上那些追逐功名的文人到头来都成了一堆坟包,就连帝王的荣华富贵也如草木一般荣枯无常。当一个人在情感上开始与王朝政治保持距离,历史的正统叙事也就遭到了颠覆。
韦庄(约836—910)
唐末诗歌在艺术上或不及盛、中唐,但在认识上却很深刻。在一个大厦将倾的时代,大多数诗人已经无心锤炼字句,民不聊生的现实让他们感到惶惶不可终日,每一天都可能是迄今最坏的一天,却又可能是未来最好的一天。在韦庄的心里,有一种时日无多的紧迫感。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